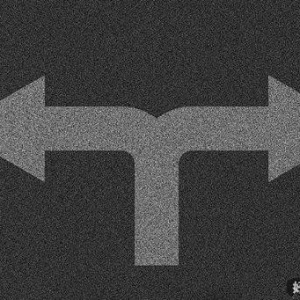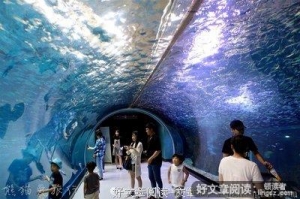在河沿村我众多的父辈当中,几乎没有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有头脑的做些生意谋个村干部,没头没脑的,大多赶着牛,终日与蔬菜为伍。
三舅本是那一代人中,最有可能由高考而改变命运的人。他始终秉承自己的信念,但却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妥协;他热爱生养他的运河滩,但又穷其小半生,想要跳出这片土地。
当庙宇和人们都不再信仰什么了的时候,三舅经历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天津西南边多是白蜡蜡的火碱地,地潮水汽多,据说1963年闹大水,南运河漾出支汊子,经年累月,倒淌成了一条五丈来宽的减河(人工开凿的泄洪水道),姥爷家所在的村子被当地人称作“河沿”,就傍在那减河边。
河水流来溯去,灌溉出片片红壤块子田,得天独厚的水土优势,叫畦里的菜长得格外健壮,方圆几十里,河沿村尤以盛产蔬菜出名。“五九的苗儿夏至的蒜,隆冬的白菜往家赶”,种菜的农户一年四季都闲不下来,女人在块子田里劳作,男人则骑车担菜走乡串镇地吆喝。
三舅从小就被姥爷视为家里翻身的希望,希望他能专心接下菜担子。可三舅不喜欢种菜,偏喜欢读书,高一就细读过整本《红楼梦》,还广泛涉猎其他中外着作。
可是,就在他高一那年,家里犁地拉车的青背老牛逐渐吃不下草料,所以,姥爷硬生生把三舅从学校拽回了家,让他辍学了。
三舅拒绝下地干活,整天蹲在炕头上抱着本书翻来翻去。姥爷本就看不惯三舅张口闭口谈学业,而今竟整日泡在“废纸”里,于是有一天,姥爷趁做饭的功夫,把三舅的书本一股脑扔进灶膛里烧了个精光。
焚书后,三舅像只受惊的驴驹一样,前后几次逃出家门,可终究因为饿肚子又跑了回来。用母亲的话说,家里孩子多,三舅又不是老小,闹来闹去谁管他死活?而从谷雨到霜降,长达几个月的抗议宣告失败后,三舅妥协了,但人也随之变得郁郁寡欢起来。
1996年,三舅时满20岁,村里一般大的小伙子们都相继结了婚,可保媒拉纤儿的婆子跑完东家跑西家,偏偏三舅好像被遗忘掉似的,守着泥筑的三间砖房无人问津。三舅之所以娶不到媳妇,一来是村里人都嚷嚷三舅神叨,怕是害了病;二来是这三间砖房还是当年赊账置办的,光秃秃的院子里仍扎着篱笆,在当时慢说礼钱三金,连置办酒席都成问题。
村里人私底下嚼舌头,说哪个女子嫁过去,怕是“炕上躺着木头墩子,炕下望着篱笆苇子”。
姥爷思来想去,决意把三舅托付给河北的亲戚,让他到黄骅港的标牌厂上班,三舅同意了,挒上包袱离开了家。临走之前姥爷还叮嘱:“书本是文化人的事情,咱农户家读完初中足顶呛,书念多了都是祸,好好赚钱才是正路子。”
那天清早,大舅担着行李,目送弟弟上了火车。可转眼一天两天,直到过去一个星期,始终没传来三舅平安到达的消息,姥爷连连打电话询问,亲戚只说压根没见到人。全家人出去找寻,一晃两个月过去,连个人影也没打听到。
20岁的男人被拐的可能性极小,黄骅那边又没有传来亡讯,家人都觉得三舅是逃了。数次找寻未果后,姥爷摆手长叹,说只当没有生过这个儿子。
2
后来三舅告诉我,当年,他半路在沧州站下了车,潜伏了一段时间后拿着仅有的钱换成车票,掉头奔向北京。
他在北京跑了好几家夜校,想读成人高中,但既不是应届生也没有正经工作,人生地不熟,最后抖抖手啥也没做成。
不久,又因为一本名叫《迷人的海》的小说,让三舅在立秋时节踏上开往关外的火车直赴大连,想去见见那个“让他产生共鸣”的作家。大连车站海风袭人,三舅举着书上的作者介绍四处问路的时候,一位“好心”的黑司机出现了。两个小时后,他从大连市区被拉到了丹东的大孤山,口袋里仅有的现金也全被骗走。
大孤山雾水飘飘,颓唐的三舅想寻份活做,可问来问去,饭店与油盐铺子的伙计都已招满,菜市口的壮劳力他又无法胜任,他只好在街上闲逛,溜达到棺材铺,木匠师傅活计忙,正好缺个帮工,三舅借着在老家担菜的那膀子力气赢得了师傅的认可。师傅夫妇盘问了一番,便收下三舅做了伙计。
刚开始,三舅还是抵触进棺材铺做活的。不是因为胆子小,而是一个正当年的小伙子整天混在棺材铺里,说出去不好听,旁人又说棺材铺多少有阴气,那玩意儿伤人。更主要的是,就这样不明不白踏进这个行当,心里还是不甘心。
可在饿肚子的现实面前,三舅只能想,落脚在铺子里,可以赚些钱,假如混上些时日,至少能学到几成手艺混饭吃,毕竟棺材这东西,那时人们总是要用的。
师傅的儿子早年到方坑里洗澡,一个猛子扎进去便再也没有浮上来,如果在世,应与三舅年龄相仿。因为这层缘故,师傅两口子对三舅很好,吃饭从不分桌,力气活也多共同分担,甚至偶尔还开导三舅要体谅父母的难处。三舅不止一次想过到大连另寻生计,但却始终割舍不下师傅,他认为那样不仁不义,况且在大连也不能保证找得到合适的活计。
很快,三舅在木匠活上便展示出超乎寻常的灵性,弯木取直这类活计全然不在话下。1997年,虽然师傅始终顾忌姥爷来找三舅,但“拙手易见千回,巧手难寻一面”,他不想错过一个如此伶俐的孩子,说要正式收三舅做徒弟,讲定“三年学徒、两年效力”的规矩,吃住全包。
做决定的那个晚上,三舅翻来覆去,他知道一旦应允,将预示他在未来几年内无法求学,甚至会关乎自己的后半生,但他还是答应了。他决定把自己的理想往后放一放。
自此之后,三舅的生活除了读书写作,还多了“一料二线三打眼”等木工常识。为了让三舅踏踏实实待在自己身边,师傅祭出了“风水”这项看家本领,成功把三舅引向了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道路,每当干完活的闲暇时光,两个木匠便会抱着一本《周易》,操着玄妙的言语谈来论去。
三年学艺,三月补艺,虽然三舅出师的速度较常人已经快了很多,可这一学还是走过了五个春秋,期间,一封信也没给家里寄过。
3
2002年,河沿村所属的镇子东南边,一家棺材铺悄然开业:两间低矮门市,手艺刘亲题“开市大吉”粘在门旁,鞭炮也没放,就这么安安静静的。
这是三舅的铺子。镇子上原有的棺材铺都是祖传的木工手艺,在人家地盘上挣口饭吃不容易,于是三舅除了做本行买卖,也打桌椅板凳,接些家具生意。由于三舅嘴巴灵快、手艺精湛,很快便名声渐显,镇子上还有传扬:三舅拜在关外大师傅的门下,能雕龙刻凤,好不了得。
三舅回乡的时候已经成了家,舅妈叫马兰花,因为小时候总唱“马兰开花”的歌谣,所以我多直呼其名。镇上和她相好的婆娘说,马兰花的家在黑龙江绥化,19岁之前她的生活就是脚踏青稞短草,在四野荒郊放羊,之后出来打工嫁给了三舅。婚后不久,孩子的降生,也意味着三舅的读书梦至此彻底结束,他要为这个家庭负责了。
河沿村的邻里到镇上赶集,把三舅回乡的消息带回了村。全家都是一愣,姥爷却没吭声,低着头顿了半晌,最后摆摆手说,不想再见三舅,姥姥哭着来劝:“他爷,难不成还要我给你跪下?”可姥爷心里就像结了块冰疙瘩,操着哑嗓子骂嚷:“没把家当家,老子也不求他回来!”
打断骨头连着筋,家里人希望三舅主动回家来认个错,可三舅随姥爷的脾气,跟驴一样倔,始终跨不过那道坎。
当时,这种“拒不认亲”的态度被许多人解读成无情,镇上的人们背地里都说三舅心太狠。无情之人是做生意的好手,却不易与其共事,一旦被扣上“不孝子”的帽子,生意也随之变得困难起来。
据母亲说,竞争对手抓住三舅“不孝”的口实,夹杂其他污蔑,大肆渲染。三舅常在闲暇之余沿着运河自南向北,捡拾没人要的破木头,或者到河湾子里刨些树墩。这些木头大小不一,即使碰上大块头也不能用来承重,只能拿机器切碎,取中间的干燥部分,来做些把手之类的零部件,以便节省木料。但就是这个习惯,却被这些人当成了把柄,说三舅到处搜集废料,然后嵌入拇指粗的钢筋串联起来,做成材板,以次充好赚取高价。当地风俗忌讳棺木里有金属,会破坏风水,不但逝者不安,对后代也不吉祥。一听三舅会这么做,连曾经从他铺子里买过木器的家户都人心惶惶起来。
更有甚者宣扬,三舅铺子里存着一本焦黄腐烂的“万民册”,书上用黑笔横七竖八勾勒出成堆的符号,记载着全镇上下各村各户一家几口、上下几辈、有无病史、健康状况、亲戚邻里等。这个谣言让妇人们极度恐惧,她们“联想”到三舅熟读中国哲学书籍,又兼习风水,就谣传说,三舅既能根据观察墓葬群来判断家族人口、运势人才,还能掐算入葬时间和墓穴选位,甚至可以通过栽一棵树、挖一锨土甚至下一根钉子来干预运势。
他的“不孝”,让这些玄之又玄的传闻在镇上纷纷扬扬,更加无解。
三舅身单影只,若想寻求家族的庇护,则需要姥爷点头,可姥爷那里僵持不下,族里的叔伯也不好开口,三舅只能任由大家议论。
生意上的挫折,激起了三舅“回家”的心愿。农历八月十五之前,三舅与家中通过气,家人劝三舅:“趁过节主动认错,毕竟是一家人。”
五盒月饼,五瓶剑南春,是三舅的礼物,他说自己出走五年,要把这五年缺的中秋寿礼都给家里补齐,以示赔罪。
但如此的破费开销,并没有换来谅解,对于三舅的突然造访,姥爷起初并没反感,反而是看完礼品后,似乎被戳中了痛点似的,嘱咐姥姥:“要他把东西带走。”随后便一头扎进屋里,直到天黑都没出来。
4
本镇的活计愈来愈少,三舅逐渐联系到了东乡二桥庙的生意。
二桥庙是座因庙得名的村子,因多产木材而得名,老穆就住在这村子里,他是三舅的木材来源。
在木头上面做手脚,是降低棺材成本的最便捷途径,这也是行里头见不得人的规矩。棺材铺的“材”也分三六九等,通常以当地通产的柳木材、椿木材居多,卖给普通人家赚头也比较小;南方的楠木材则因为质量高、不蛀虫,数“材”里的上品,售者多为富户,加工完余下的木料还能做小孩的童棺,所以往往捞钱都在这种生意上。
老穆的独门绝技就是炮制假楠木,如此以次充好,赚头能够翻倍。他曾不止一次撺掇过三舅,可都被三舅严词拒绝,三舅常引圣贤话来告诫自己,“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
虽然拒收假木头,但老穆给三舅谋了另一条路子。
民国的时候,逃荒死人多,二桥庙的老和尚梦见菩萨要他救济过往,所以打那起,庙里便开始“拾荒”:茫茫的碱滩上,碰见尚有口气的逃荒人就救济回来,遇到死掉的便收济到庙里,挖土往岗子上一埋,庙里给立个灵位。
生前都是可怜的游鬼,死后给他们一个安生——这是多少年来东乡墨守的规矩。直到后来,乡里每年也会拨经费安置死掉的流浪汉:人死后,会在二桥庙停放几天,一来先给公安局备案,二来再给土地爷报备,报备完,在岗子上拿半节糟棺材草草埋掉;还有些没家没业的流浪汉沦落到这里冻死饿死,也就被二桥庙的拾荒人顺脚埋了,身上的钱财多归了拾荒人。
日子久了,东乡地下处理死人的产业成为被默许的存在,乡里有明面上的人口管理,二桥庙有地下的“拾荒”产业,二者互有交织却并行不悖。
自90年代末以来,全国大力推行火葬,那些不舍得把亲人尸体烧掉的家户,只能先交给上面一份罚款或者伪造一份火化证明,再把人送到二桥庙来装棺超度。作为补偿,家家户户都要买庙里的棺木、寿衣,还要再送上份香火钱。久而久之,这套安置死人的办法便成了生意,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里仍屡禁不绝。
而当时,二桥庙所需的大量棺木基本都由三舅提供。棺材行业利润大,他给二桥庙的“材”质量属于下等,由于是大客户,发货还比一般散户要便宜不少,即便如此,走量不走质,收益依旧非常可观。
那阵子,三舅突然忙碌起来,经常开着双排座的卡车,从老穆手里拉来木头做棺材,加工完毕后再送到二桥庙。
除了生意上的来往,二桥庙对三舅还有另一种魔力:作为我们当地最大的庙宇,二桥庙的“经阁”一直保存着,虽然室中多数古籍已被烧毁,但三舅还是从中找到了一些关于木工、宅相、禅宗的存本。方丈热衷做“生意”,对书本毫无兴趣,所以每次送完货,三舅都可以任意借阅。
那时候,我正上小学,二桥庙的生意让三舅腰包渐鼓,没多久,他又买了一头青背小牛送到家中,说:“当初自己辍学本就是代替青牛劳动,而今青牛就像自己,希望为家庭出一份力。”
姥爷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为此重新开放了牛棚,麸糠草料,从未间断。
5
2008年还没“进九”,大雪就像催命鬼,一场赛一场厉害,大河结了厚厚的冰碴子,西北风格外戳人,十里八村挨不住寒,多有人走。三舅说,每年数九寒天是卖棺材的旺季,村镇上许多体弱多病的老人能扛过春夏深秋,可却会倒在入冬之后,铺子的生意随之又忙碌起来。
可能因为行当缘故,三舅不经常串门,到我升初中以后,借着青春期的猛劲,常偷着往三舅的铺子里跑。
棺材手艺作为一门“绝户活”,多是父传子,造棺的特有尺寸世代相传,造材的方法也口口相授。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导致了评判标准的独断,往往常人只能从表面大小来观察“材”的优劣,所以在制作的时候,考量的多是木工的良心。
三舅在屋子里写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从不糊弄人。例如,“材”俗称为“十页瓦”,一般由十页或十二页木料制成,其中盖、底、帮、档又分三三四、三四五等不同规格,三舅在制作中极少出现缺木短工的情况,其材大多满七尺三寸,能睡天下英雄好汉,而在送材的时间节点上,也踩得十分准确,不会耽搁时间上的讲究。
每做好一口,三舅都会在“材”里放卷刨花,说这是告诉孤魂野鬼,这口“材”已经有了主人。紧接着就要上漆,棺木成型如果不及时上漆,不久便会生蛀虫。其他棺材铺还在通用黑漆,大笔一刷覆盖性强,漆下木头的好坏难以分清,所以容易以次充好。但三舅却不顾同行的反对,使用透明漆,好坏一目了然,如此博得大家信任。
ldquo;材”做好后,便要“画材”。镇上“画材”的老先生逝去后,人们逐渐失去了精雕细琢的耐心,一般的棺材,材头材尾无外乎福寿二字与莲花图案,两侧则是左凤右龙。碑亭松鹤等全已消失不见,皆被大段云纹代替,出工快效率高,广为人用。
可三舅却重新在龙纹下启用了“暗八仙”等图案,此外还有琴器、桃榴寿果等。他坚持这样反趋势的做法,以此来显示尊重。“画材”除了继承老先生的笔法外,又借鉴水粉画的笔调,起承转合勾笔流墨,极富于书法的意蕴,先采用色彩的重叠来定调,后用小笔摩细处,细枝末节上的纹理会采用“书”字笔法——这个笔法由其自创,也是他绘制技法的来源。
那段时间,我常去铺子玩,三舅怕耽误我学习,便瞪着眼叫我少来几次,不然母亲发觉会责怪他。听了三舅的话,我冬至后就很少再去。
又过了些时日,年关将近,除了飞来横死的人,有病人的家户都会把丧事拖到年后,最好等到正月外,不然“新年丧兆”冲吉利。二桥庙的拾荒人也多回家过年,棺材铺的生意也暂时歇了下来。
年关前一场大雪足有五指厚,三舅决定赶在过年之前再回家一次。只不过,还没有等到新年到来,顶着小年夜的霜雪,三舅却被抓了。
6
据传,三舅出事头几天做工时,一斧子下去,木头四分五裂,大家都嚷这是坏兆头。
ldquo;小年”前,市北山区发生凶案,由于案情复杂,交接给了市局处理。市局锁定了一个失踪嫌犯,路况监视系统的线索显示,案发不久后嫌犯乘坐长途汽车南下,目的地便是我们县区边界处的镇子,可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嫌犯却人间蒸发似的,无影无踪。
一筹莫展之下,公安局只能采取最传统的笨方法,排查县区内外来人口与失踪人口的死亡状况,一路查到了东乡二桥庙。
在了解了二桥庙的地下产业后,干警突击审问,得知近日掩埋了两个死人,尸检后全不是要找到的目标。后来干警遍访周围村庄,才从孩子们的口中得知,土地庙背后的玉米地里还有一块乱葬岗,当晚,干警连夜突击,从土地庙挖出了多具尸体,翻来翻去,果真找到了失踪的嫌疑犯。
审讯时,老和尚只是承认了杀人者的帮凶角色,但随之却挖出了一条黑色产业链:就因为二桥庙的特殊性,周边有不少区县的死人也会冒充流浪汉,来私下处理掉,不用开具死亡证明,5000块处理一个人,只用买些庙里的棺木、寿衣与各种丧葬用具,土地庙背后的玉米地便是埋人的地方。二桥庙处理来源不明尸体的事实不可辩驳,而与二桥庙的生意往来也把三舅卷进漩涡。
东乡的埋人生意,镇上人都晓得。偷漏火葬、拾荒赚钱钻空子的事情常有,演化为带血的生意也并没多出乎预料,但如今出了这档子事情,镇子上还是唏嘘一片。
三舅在接触到二桥庙生意半年后,便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起初以为二桥庙靠土葬赚钱,人死后尊重乡俗把尸体保存,这是人之常情。但后来他却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疾病、天灾、冻饿,这些都是掩盖真相的借口,老和尚也常常半夜到土地庙,烧纸钱念经咒,蛛丝马迹告诉三舅,二桥庙可能真在参与处理一些来源不明的尸体。这个发现叫他终日惶惶难安,但当他在聊天中对拾荒人进一步试探时,对方总是矢口否认。
三舅熟读经史,自认为三观正确、绝不做有违道德的事,但在这个问题上却犹豫了。
如果揭发,自己的生意便会再次陷入低谷;如果包庇,则良心上过不去,同样也与他所读诗书之哲理相违背。
而就在纠结之中,老穆敏感地发觉了三舅的心事,他简洁地阐明了道理:“兄弟既然已经跳进了这个圈子,你要揭发,到时候和尚们反咬一口,你也得不到好果子吃。万一出事,那到时候老婆孩子去哪?这世上谁与钱过不去呢?况且,上面也不能叫二桥庙出事,就算真出事到时候装不知道,也无罪。老哥我这么多年不一样稳稳当当活得挺好嘛。”
老穆的威逼利诱很有效果,他成功地利用了三舅的知识盲区,同时又戳中了要害,这么多年,三舅始终也没有捅破这个秘密。
开庭时,法院认定三舅参与处理来源不明尸体,犯包庇罪,但鉴于审讯期间有自首情节,且并未直接参与销毁证据,处两年有期徒刑。
判罚即下,马兰花哭闹着当即提出上诉,姥爷也到处请人托窍,揣着“信封”去找镇派出所所长,可所长说,给你办事就得钻空子、冒险,凡事要讲究等价交换,你这个巴掌大的信封值得我冒那个风险吗?母亲说当晚姥爷回家后,流下了一滴浊浊的眼泪。
二审的律师是马兰花自己找的,可折腾了许久,几个月后宣布维持原判。二审宣判那天晚上,马兰花没再哭哭啼啼,只是屋里的灯亮了一夜。
● ● ●
三舅被关起来后,镇子上流言蜚语,人们有的说可惜了三舅的手艺;有的讲因为三舅不肯做假棺材,老穆故意拉他下水。
三舅不在后,铺子的生意也愈来愈不景气,不久镇北边又开了一家棺材铺,自夸祖上是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的御用木匠。
转年初秋,高粱熟透,山芋拉秧。马兰花销完铺子里半数的棺材,把未漆的用雨布盖住,带着孩子踏上公共汽车到邻县打工去了。
临走前,马兰花去狱里看过三舅一次。回家后,她依照三舅的叮嘱,把家里的书通通丢到院子里,引燃了一把火,只剩满院焦灰。随后,马兰花在棺材铺大门前撒下一圈白灰,接着便离开了家。三舅曾给我讲过,棺材铺每次卖完年轻人的“材”后都会这么干:撒白灰是为了防冤魂,因为中青年的死不比寿终,死后更为不舍不甘,白灰为界,怕魂魄不想超生,半夜回来走错了家门。
而马兰花在自家店铺门口撒白灰的用意,我至今也没有明白。
后记
2010年秋,三舅出狱的那天,姥爷早早套好牛车,天还没亮就上了路。他告诉姥姥:“当初我把三小子逼走的,如今我接他回来。”
牛蹄有节奏地向前踏去,又是一年秋晌,葵花大多收罢,三三两两,只剩秃杆子站在田野里,一牛一车两个人颠簸着,路上没有说话。
后来,三舅的铺子重新开张。东乡那边又新盖起了几座大庙,衰落的二桥庙隐没在其中,几乎没人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