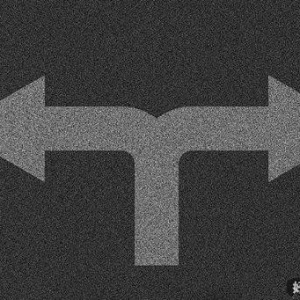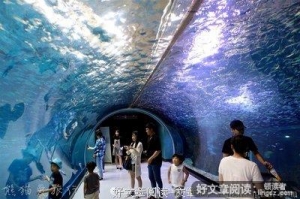东州城里出了个飞贼,起初还只是偶尔作案,几次得手后就开始张狂起来,三天两头地出手,再后来干脆不分昼夜,只要兴趣一起就来事儿,完了还在墙上留诗,把东州名捕赵之焕大大嘲笑一番。
赵之焕气啊,可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抓不住这个飞贼,因为他每次作案,现场都是干干净净的,不留一点痕迹。万般无奈之下,赵之焕只好去向自己年近八十的授业恩师、时下正在京城任总捕的欧阳华请教。
欧阳华听赵之焕述说了之后沉吟良久,问道:“你是说他最近白天也作案了?”
赵之焕点点头,说:“这正是令弟子困惑的地方,一般飞贼只要知道官府插手,至少会暂时收敛些,可此贼却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
欧阳华听罢又沉吟片刻,对赵之焕说:“那……我跟你去东州跑一趟吧!”
欧阳华任捕快几十年,还从来没有经他手破不了的案子,这个刑部总捕的位子他硬是凭自己真本事一步一步坐上去的,所以赵之焕一听说他要亲自到东州去,心里的石头就已经先放下了一半。
这边欧阳华跟着赵之焕刚出京城,那边东州城里就已经传开了欧阳总捕要来的消息。也许是惧怕的缘故,连着几日那飞贼都没有出来作案,赵之焕心里便有些得意起来,竖起拇指对欧阳华说:“到底是恩师威名震天下啊,终于把那贼给吓回去了!”
可欧阳华却朝赵之焕摇头:“以我的判断,他很快就会继续动手的。”
果然不出欧阳华所料,第二天天一亮,赵之焕就接到报案,说城中又有一富户昨晚家里遭窃。赵之焕请恩师一起去勘察现场,一到那里,就见庭院正中那雪白的墙上,又有那飞贼留下的一首打油诗:天地我独行,敢笑世间人;名捕与总捕,能奈我如何!现场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痕迹。
欧阳华站在庭院里,很仔细地看飞贼写的打油诗,一边看一边感叹:“有意思!有意思啊!”
赵之焕疑惑地问:“恩师,难道这字里有名堂?”
“你啊,真该好好看看这些字,”欧阳华朝赵之焕咂咂嘴,“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啊!”
赵之焕一听,愣住了,猜不透欧阳华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欧阳华的举动更让赵之焕感到莫名其妙,他原本以为欧阳华会下令四处搜捕飞贼,没想到竟成天呆在屋里,根本就不提捉贼之事。而那飞贼也好像知道总捕奈何不了他,为弥补前几天没有动手的损失,有时一天竟能作案四五起,而且每次作案后都留诗一首,把赵之焕骂得个一钱不值。
赵之焕觉得自己在恩师面前丢尽了脸面,一肚子气实在无处可发,只好跑去酒楼买醉。
他刚一坐下,就听到旁边有人在聊天。
一个大嗓门说:“我敢打赌,这飞贼是天上偷星下凡,要不,怎么赵捕头和欧阳老爷子都抓不到他?”
一个尖嗓子却反驳他:“话可不能这么说,欧阳老爷子是总捕,赵捕头也不差,相信一定可以抓到这个贼家伙。”
大嗓门听不进这话:“那欧阳老爷子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走路尚且费力,哪里还能动手抓人?再说赵捕头,这么久连飞贼是谁都不知道,他抓谁去啊?”
尖嗓门一听,立刻大叫起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看你八成是……”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引来很多围观的人;这些围观的人一边听一边忍不住插嘴,后来竟也跟着分成了两派。
吵到最后,一个瘦得像排骨似的的中年人竟宣称说:“我要是那飞贼,索性就到官府走一趟,什么总捕、名捕,哼,抓到我算他有本事!”
赵之焕一听,气得立刻从凳子上跳起来,他哪还喝得下什么酒,把酒杯一推就回衙门去了。
此时,欧阳华正和一个差人在下棋,左手执黑,右手执白,落子极快,见赵之焕进来,随口问了一声:“那贼有动静了?”
赵之焕便把欧阳华让他去作案现场临摹来的飞贼的诗拿出来,给欧阳华看。
欧阳华一张张仔仔细细地看起来,看到最后一张时,他笑着对赵之焕说:“差不多了!”
赵之焕不懂:“恩师,这‘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欧阳华朝赵之焕眨眨眼睛,说:“你按着先后临摹下来的顺序仔细看,这字前后有什么不同?”
赵之焕低头一看,没看出什么来呀?再看一遍,还是什么也没看出来。
欧阳华只好叹一声:“这都怪我,当初只教了你破案之法,没好好教教你书法啊!”他随即给赵之焕咬了一阵耳朵,又嘱咐一句,“记住,那些机关至少要比平时多布置上一倍。”
赵之焕挺困惑:“就这么块地方,要布置这么多?”
欧阳华笑笑,又跺跺脚,说:“不但屋里,屋外也要布置。”
赵之焕顿时吃惊不小:“飞贼当真会来这里?”
欧阳华肯定地点头:“不出意外的话,就在今天晚上。”
赵之焕虽然满腹疑问,但还是按照欧阳华的嘱咐,把所有一切都布置停当。
随后,欧阳华就叫赵之焕跟他下棋,一直到夜深人静时,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赵之焕这时候真是心急如焚,一来他担心欧阳华的判断是否准确,飞贼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来闯衙门?二来他也担心,万一飞贼真来了,自己预设的那些机关到时候是不是真能抓得住他……
赵之焕正在胡思乱想时,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衣袂飘动的声音,赵之焕心里猛一震:莫非被恩师说中,贼真来了?他“忽”地就要起身,没想欧阳华一把抓住了他,这时他才发现,欧阳华的手心是汗津津的,他感觉出来,其实恩师心里也很紧张。
只听外面响起几声奇怪的声音,显然是飞贼发现了赵之焕布置的那些机关,正在一一破解。不多时,就见一个人影从外面进来了,脸上还蒙着一块面巾。
欧阳华朝他拍拍手,说:“老朽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进来的果然就是那个飞贼,他愣住了,脱口道:“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来?”
不仅是飞贼,其实赵之焕也很想知道其中的道理。
欧阳华指指桌上赵之焕临摹来的飞贼那一叠打油诗,说:“原因很简单,是它们告诉我的。”
飞贼显然对欧阳华这个回答困惑不解:“这里面还会有什么讲究?”
欧阳华大笑:“难道你自己真没发觉?字迹变化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境变化,你每次下手之后都留下这玩意儿,上面的字越写越张扬,但同时又透出越来越深的寂寞味儿。是啊,一个人犯下这么多大案,又不能跟任何人说,当然就寂寞了。再看最后那首写的字,充满了想要向人诉说的欲望,可向谁说呢?说给普通人听吧,你不会获得多少满足感,如此看来,我就是最佳人选啦!”
没料飞贼听欧阳华说到这里,突然拍手大笑起来,:“不错,不错,你真不愧为天下第一神捕。”他一边说,一边就把蒙在头上的面巾掀了。
赵之焕看得真切,此人正是酒楼里那个瘦得像排骨的中年人。
飞贼对欧阳华道:“可是,你即使算准了,又能奈我几何?”
看飞贼气焰如此嚣张,赵之焕再也忍不住了,拔出刀来就是一招“泰山压顶”,挟风带雷般的向飞贼扑了过去。哪想赵之焕的刀刚砍下去,飞贼已经闪过身去,赵之焕见自己一招落空,紧接着又立刻使出第二招。但飞贼根本不和他正面交锋,只是用高超的轻功与他周旋,如此一来,赵之焕力气接不上,动作渐渐慢了下来。
没想飞贼的动作却依然那么轻快,最后“呼”一声落在屋梁上,朝赵之焕狂笑道:“如此笨拙,却要来抓我?”
他这话音刚落,突然就从梁上罩下一张大网来,眼看就能将飞贼罩住,不料这家伙却反应极快,在网罩落下的瞬间,他已经抽刀将网罩划破了,等网罩落到地上时,他已经跃至屋外。
赵之焕看在眼里,心里这是急得火烧火燎,又听飞贼得意地丢下一句“神捕也不过如此”的话来,更是气得捶胸顿足。
可让赵之焕万万没想到的是,明明那飞贼的人影已经飘到了屋外,没想眨眼间却又被丢进屋来。而且紧接着就是一声报告:“大人,飞贼抓住了!”
赵之焕惊讶地发现,进来报告的这两个人,竟然就是那天在酒楼里吵架的那两个汉子,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爷子早就在暗中安排好了一切,先故作低调,激起飞贼的狂妄之心,然后又安排高手故意争吵,以进一步刺激飞贼,使其落入陷阱,至于什么字迹变化、机关布置等等,那都是或要从心理上震慑飞贼,或要让飞贼生出轻视之意。
赵之焕心里顿时生出无限的感慨:当捕快并不是武功好就行,更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文/吴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