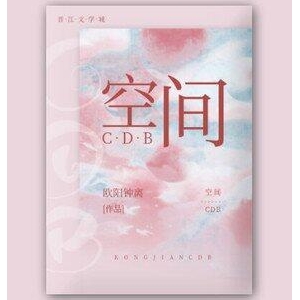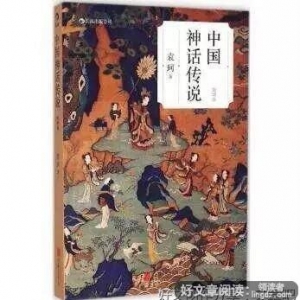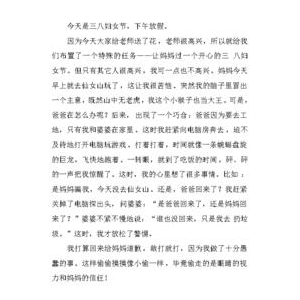每一朵花都在直奔绽放的主题
高穹

这一季我算是与月季、蔷薇较上了劲。从初春到初夏,不懈地迂回往复于它们之间,施肥喷药,修枝剪叶,期待它们会在春夏之交时给我呈上一片姹紫嫣红的生命高光。
这时偏偏又总能看到天南海北的文朋诗友们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产地的,正盛极一时的各种花卉,其中不乏月季和蔷薇花,有的花甚至开到荼蘼花事了,而我这里的花们各个闭花羞月的,像见到了绝代佳人杨贵妃般的一副不堪媲美,卑以自牧的姿态。
这让我不得不加快奔走往来于它们之间的频率。但它们似乎情怯于我这样的一片痴心躬迎。
我把自己这种像闺中待嫁般的焦虑心情说给姐姐听后,她笑我太闲了。说几个月的宅家生活,一定悄然改变了我什么。其实,姐姐不说,我也清楚自己确实有了变化。因从来都不躬亲农活,似乎置身红尘之外的我,在这个春夏时节,竟像染上一种瘾般一直都在慎独自律地莳花弄草,打理庭院的菜蔬花木。感受着王安石在《书湖阴先生壁》里的那句诗:茅屋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摘。
以往每年这个时候,我和家人都借故忙于工作,对庭院里的杂草视而不见。以致于后来晴翠接荒秽都习以为常了。
其实真的有那么忙吗?即便闲暇时,我们也懒得将庭院换妆易容。我想有三点可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一是,我和他都是家里老幺,自小所有的农活都被身上的姐姐们代劳了,无需劳动我们。二是,我和他都视农活为劲敌般,一见农活就四体发软,不想动弹,自甘投降。最主要的是最后一点,我们正值养家赚钱的年岁,做这些事觉得费事费时,认为何不在最好的岁月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其实喜欢侍弄花草菜蔬,对我来说并不突兀,在那些不断增长的年岁里清清浅浅已有了些许铺垫。但像这样如痴如醉恋上了花草,姐姐说我是闲出的病。我承认闲情逸致有时能明确乐事达观的态度,但它不会诱发闲人为一种付出而动力十足。就像块茎植物能上长叶子,亦能下产果实。而闲人只是一个根茎,人浮于事,只能闲出惊鸿照影般的花容月貌而已。
我在为花木修剪喷药,为菜蔬施肥刈杂时,忽然脑里就出现了身边那些曾经赶往在我这个岁龄的人们,每天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周而复始却乐而不疲的身影。那些身影里姐姐也在其中。不觉间我竟然也在重复着她的忙碌和快乐,不是吗?所以我否认了姐姐的说法。若说我闲出了满园春色夏景,就等同于说她也是这么闲出来的。
我是在等待月季花苞绽放时,看到了曾经那个努力包裹住琉璃脆般的初心,拒绝成长,羞涩开放,低垂着弯折的自信,又不得不向风雨如晦的现实撕裂而绽放的自己,谁在推动着我一步步脱离自我的窠臼,慢慢长成一棵树的姿态,扪天为近,窥地不远呢?
岁月不居,不觉间,我走向了生命的深处。我本不想重复他们已走过的路,但物来顺应,由不得自己,我已经是一棵落地为安的树,正在回收魂游四海的羽翼。我找到了一种生而可恋的活着的意义。
可我还是不能静下心来,就像手里拿着糖果,还在索要面包的孩子,在赶往岁月的路上急不可待要看到庭前花草争艳,院后植株繁茂,一切都是岁月峥嵘的样子。
那时姐姐忽然说道:今年是闰月年,不要妄自跟着时间跑,时令还没到,若到了花自然会开。
是啊,我怎么还照着孩子的想法,却忽视了世间万物一荣一损皆有时候呢?此刻那些摇曳在时光里的月季和蔷薇花,不蔓不枝,不牵不攀,仍羞答答地静悄悄地含苞待放,却明显地直奔绽放的主题而去。
一如此时的我,既然已敲定了生活的主题,又何忧落笔无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