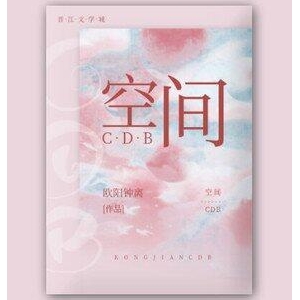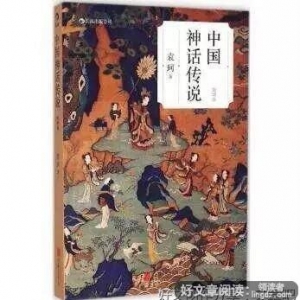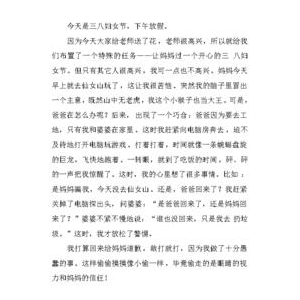很多人写传记,常常追述祖辈或者父辈对自己的影响,我当然也受到亲人的影响,但是倘若让我说说谁为我的精神涂抹了底色,我觉得就是我那个村子,那个特殊的小地方几乎上演了六七八十年代全中国政治戏的村子。那是个让我爱,更让我心痛的地方。
我降生69年,到了懵懵懂懂开始思考的时候,最惯常见到的情景给我的感觉是:做人不小心会挨整。父亲是会计,因了这个原因,我常常在晚饭过后被他带着去村里开会。但见小小的会议室里人头攒动,旱烟的烟气常常弥漫整个屋子,我只能看见黑压压的一屋子朦胧人头,具体是什么人,看不清。待到大家被一个年轻人领着齐喊口号的时候,我才看清楚他们都是本村里的“整劳力”(他们喊青壮年农民为整劳力,而妇女和少年少女被称为半劳力)。我常常被吓得不敢发出一声的,看着那个被批的人可怜巴巴的低着头,一声不则的样子,这样坚持两三个小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我不知道那个人究竟做了什么错事,竟然被这么多人齐呼着要打倒。也不敢问,因为父亲总是很严肃的,我记忆里他从未领头来喊,自己也不跟着喊,只是看着别人喊,现在想来父亲真是木讷的可以,他做会计,只是因为读了中专,有着一肚子迂腐的文化而已。而我们全村所有的人里,你打着灯笼来数,没有一个人有他那样儒雅的气质,他从不出语粗俗,也不会用自己比别人多出来的知识压人,当然他也没有管理人的办法,只是顺其自然而已。
后来知道那是村里整治偷鸡摸狗的村民的办法。其中当然就有我的叔叔。他从小不学无术,无论老祖宗们如何逼迫,就是不读书,竟然调皮到把家里黄牛的尾巴给拽下来,但是,因为家里颇为富足,没有人特别嫌恶他,反而常常拿他做笑谈。可是后来成年后,却常常做些不怎么光宗耀祖的坏事,所以就常常被打倒。自幼,大人们就常常这样为我树立学习的楷模:看你爸爸多好,可是你叔,哼!简直不是一母所生!
如果是纠正村民的行为,这样的批斗会倒也无可非议,我却常常听说某某村民因为不会说话而挨整的例子。比如有个村民对村里的领导说了几句闲话,立刻会在不久招来一个被整的培训班,只见那人站立在一群人围成的大圈子里,耷拉着头,脸色乌青,等待着人们一边高呼着打倒他的口号,一边用碎石子或者坷垃投掷他,他则老老实实任由人们“修理”。
很多农村题材的文字说文革在农村痕迹很轻,我不敢苟同。我幼时的记忆里,常常有这样一个镜头:我和弟弟因为不懂事口无遮拦说出了令大人忌讳的话时,正在做裁缝的母亲常常丢下手里的剪子,跑上前去一下堵住弟弟的小嘴。
二奶奶家里的二叔三叔都被“请进”过村里的学习班,那时村叫做大队。据说二叔三叔是说笑话时不慎被人告了,学习班(整人的班子名字)里的人来带他们走时,三叔机灵,马上说了几句认错的话,而老实的二叔却不会,只好被“收容”了一周。
爸爸是小队里的会计,母亲带着一组女人在大队里做裁缝,给全村所有的村民做衣服,所以他们平时接触领导较多。对于做百姓的苦楚,母亲是深知的,所以无论百姓们跟她说什么话,她总是宽容的理解,还好心的劝慰大家别出去乱说,她也不对我们讲述学习班里的情景,怕小孩子说出去惹祸。直到八十年代末,有位被大队学习班刑讯逼供差点儿致残的光棍儿叔叔晚上去我家里聊天,拿出奖状般大小的“平反书”让我们姊妹几个看,并跟我母亲交流当年所受的苦楚,告诉我们自己如何将自己忍受的冤屈一直告到北京,凭着中央领导的一纸证明天天坐不花钱的公交车,还露出被学习班里打手们用烟头烫伤的地方让我们相信他的陈述。
曾有这么一家,变卖所有的家产,外出告状数年,最终不了了之。我不知道他家怎么受了冤屈,也不敢问,因为母亲给我们定了一条家规:进门不谈别人事,外边随时有人听。
这个小地方不过是泰山东麓的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村子而已。方圆不过十几里地,且都处于狭长的山谷里。但是,正因为独特的地理,和独特的历史时代,她竟然成了闻名全国的学大寨先进单位。
现在你知道了吧,因为我们村的书记是全国名人,曾经在收音机里发表过讲话,在那个年代,成为一跺脚就令全村乱颤的人物就不足为奇了。
就是这个人物,号召全村人拆掉所有的民房,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号令自己的村民,铲平山脊,在山上建起了楼房。我记事的时候,村里已经盖起了五六座石楼。每天上学的路上,我都能看见浩浩荡荡的基建队伍,用光膀子拉着一车车(地排车)山上开采来的石头条子,吃力的爬上长长的山坡,他们脸上,除了用力拉车的肌肉扭曲,还有滴滴答答流个不停的汗水。还有十几个木工,天天将林场里运回来的大树桩绑在一根电线杆上,而后,他们两人一组站立于高高的木梯上,各执大锯一端,从早上一直拉到天黑,身体也由高高的梯顶下降到地上,每当走到他们拉锯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替他们难过的想法,看看他们的表情,总觉得这样的生活太残酷。
我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也都认识我,因为我母亲给每位村民做过衣服,而我家常常成为了他们肆意说笑的地方,他们知道我母亲的豁达,常常像在自家一样随便。
不要认为这样的工作劳苦,他们能够进入村里的“基建队”(给专门负责盖楼的青壮年男女取的名字),是每个家庭里最大的荣耀,就如当年去参加抗美援朝一样荣耀。
我没有见过他们有谁哭泣,倒是常常看见或者听见他们唱起高亢的歌。因为姐姐进入基建队劳作,我们家也有了一份荣耀,每逢晚上来临,进入家门的姐姐总是为我们谈论当天发生的故事:比如年轻的哥哥们说的笑话――
我要泥巴(你吧)。(男子建筑农民对干小工的妇女说的话,这时妇女一般是脸色羞红,嘴里骂几句。)
养上三万六千五百个女儿,每个女儿家呆一天,还没等亲热过来呢,就死了,这样多有福气!
唉,都说虱子是从肉里出的,怎么肉上没有窝儿呢!
——
我读到五年级时,我们家也住进了村里盖的楼房,因为住在楼头,于是每当放学的时候,我得以在家里的院子里目睹青壮年男子们拉着地排车由远而近飞跑着拉上长长的大坡。看见他们一个个脸色涨红脖子上青筋暴起,整个身子几乎倾倒在地上了,可是有些三人组里的哥哥们还在激烈着争论着什么,原来是休息时的牌局了。
我母亲遇上这个镜头的时候总是笑骂他们:娘的,这么累,还争这些!
他们可不管,膀子上丝毫不松劲,驾辕的死死抓住车辕,可是争论还是丝毫不放松:就是你孬了,刚才你小子藏起来一个司令!
看着他们,年幼的我总有一种震撼:生命真的让人畏惧,多么艰苦的条件啊,他们竟然乐观的这样!
我乐意亲近他们,没事的时候,就跑去跟他们说话,看着他们满布老茧的双手,常常震撼于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我在乡读书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是跟那些劳动者一起度过的。
七十年代初,我们庄就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目标。不过,容我做一下解释:自来水的引水实验没有成功,我倒是看见一个盛水的大皮罐,但是引水到楼上的实验没有完成,且水因受了太阳的暴晒而涩味浓重,故而中途搁浅。电话当然也没有安上。那个年代毕竟物质不太丰裕。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村自打我看懂简单的戏剧时,就有了彩电,每晚定时在村委的广场里(一个开阔的平地)演播,据说那台彩电是全国当时进口的三台中的一台,是跟爸爸同学的大叔到北京买回的,他是大队会计。
每晚有了看电视的机会,村里的娱乐就丰富了。有时还会同时演电影,让小伙伴们目不暇接。所以,在那个时代,我几乎看遍了所有的电视剧,现在想来,这些剧本比今天的深厚和耐看。
当时全村的经济状况相比较于邻村,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很多外存女孩子贪恋住楼房,吃白面(白棒子面儿)煎饼,要求嫁到我们村,可是当她们看到我们的村民劳作起来不要命的劲头时,都苦笑着说:看来,只闻名不见面是不行啊,被你们骗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杂乱的叙述能否让读者略微明白: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物质相对高于邻村,自由相对压抑,文化生活相对丰富的山坳里。
忘了提起,我读小学的时候,上海等大城市的摄影记者就不断的来到我们这里,为我们的楼房拍下了美丽的夜景。还有一个联合国六国联合考察的计划将在这里开始,因为某些原因临时搁浅。村上的有户人家,也上了电视,被作为先进农村的样板报道于很多媒体。我读二三年级开始,几乎天天看到盘山公路上来我们村考察的外地人,沿着盘山公路步行着一直到村林场里的一座养殖专业户的家,路上密密麻麻的人,沿着盘山公路,就像一条白绳上的蚂蚁。
我自豪过,多次。直到读了师范,有老师提起我的家时我还自豪过。
现在,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