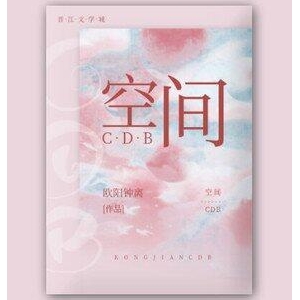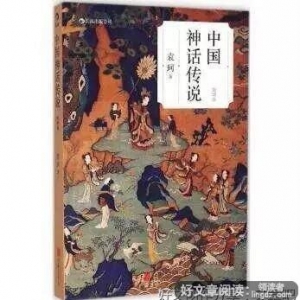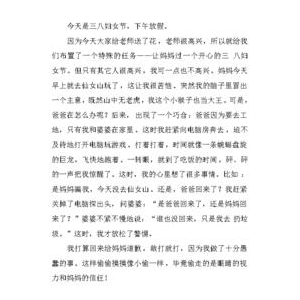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鸽灾》是一本由[美]路易丝·厄德里克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鸽灾》精选点评:
●憋文ing
●20180715——69;作者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方式讲述印第安人的故事,好处自不待言,副作用却也很明显——接下来不容易找到有相同阅读快感的书。所以,看过《爱药》《鸽灾》之后,更期待《圆屋》《拉罗斯》了。
●SAIC writing class
●可能是很不错的一本书,怀疑原文的语言应该是流畅而有韵律的,但译本应该叫翻译灾吧,有很多能想象出原文的翻译错误,语言的感觉特别不好,两个译者的水平大概不一样,偶尔还行,经常很差,而且把读者当傻子的译注也特别影响阅读节奏。
●印第安作家的作品我还是第一次看,真是孤陋寡闻,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就象被西方殖民者切开的血管,留下很多血腥悲苦的回忆,再加上他们不久前的祖先们与自然之间那种神秘的通灵感,说出来的故事自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引人嘘唏……
●很显然,鸽灾在叙述上比爱药更成熟——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小说在结尾处成功地将编织故事的网兜收拢了回来,手法沉稳老到,却也失之灵巧。生活历史成为贯穿始终的核心,爱恨纠葛、种族矛盾则是永恒的话题。然而,真相却不是救赎。鸽灾体现了厄德里克的野心,其内容涉猎之广泛,似乎连她所擅长的这种发散式的写作方式都难以将其把握,以至于技巧几乎被情节所淹没。最后,拜托简介思路清楚一点。
● 《鸽灾》出版后,印第安文化研究者按图索骥,从厄德里克的字里行间,翻出1897年一起真实发生过的灭门案,和小说中描述的基本一致,厄德里克甚至直接引用了“圣迹”这个真实案件中被滥用私刑的人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太具讽刺意味了! 到底是印第安人该感谢白人引领他们步入文明,还是永远将白人视为劫掠他们森林和土地的贼寇?答案只有印第安人自己心里有数。但明摆着的,是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仇恨、歧视和偏见长久以来依然存在。这难道不是贼喊捉贼的心理? 往事随风,往事匆匆。但往事并不如烟!有些事,绝不能当没发生过……我们还小时,破碎的语句四散在周围,故事还未形成。随着年岁渐长,曾经听过的故事,就渐渐变成我们的生活……
●手法很棒,就是记人名有点乱
●第一次读印第安文学 与众不同的视角和叙事 作者才华横溢 翻译流畅细腻
●“我们还小时,破碎的语句四散在我们周围,故事还未成形。随着年岁渐长,故事渐渐变成我们真实的生活。”
《鸽灾》读后感(一):一场印第安保留地的灾难
你永远没法以消灭肉体的方式消灭你的敌人,但你可以让你的敌人以认同你的方式被“消灭”掉,如今的美国如同熔炉,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黑人,都被重铸为美国人,哦,当然,墨西哥人可能要另当别论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在美国文化中体现最全面,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度,难免要为何种文化占主导地位而动一番脑筋,好在美国人为了所谓的自由研发出了很多制度,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为了促成双方团结以及保障白人领导地位,不得不将印第安人驱逐到人烟稀少之地,除了那些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的印第安人,仍有一部分尊重传统保留文化火种的印第安人活在保留地中,随着时代发展,留在故乡的人越来越少,而保留地也渐渐变成“三不管”地带,白人始终还是要把印第安人“消灭”的,文化的入侵谁也拦不住。
路易丝•厄德里克的作品《鸽灾》正阐述这个历史问题。从外公口中的鸽灾开始说起,一直说到那起谋杀案幸存的婴儿讲述慢慢拼凑出的真相,故事以三代人的爱恨情仇浓缩了印第安人与白人的近代史,恐怕故事会让冲着印第安文化而读的读者失望,但读罢此书,一定会让你震惊。故事中的故事,关系网中的网,剧情铺设巧妙,构思精细,尽管翻译过来的文字稍显没有力度,一段一段的十分有割裂感,但最后一节将所有独立故事穿起来之后,你只能赞叹路易丝•厄德里克的能力,简直太会玩了。
三代人,从不惜得罪老朋友也要诋毁基督教的外公,到婚前同居不以为耻的姑妈,再到就算不知未来在哪也敢对性关系无所谓的自己,从先辈与白人发生冲突,到晚辈渴望融入白人社会,尽管埃维莉娜对历史和家族产生浓厚兴趣,但也仅仅说说而已,法国、毒品、同性恋等等意识超脱的概念才是年轻人关注的点,真正保住文化或者愿意挖掘文化的印第安人越来越少,小镇的荒凉和闭塞将逼走一代又一代人, 这是必然趋势,无法阻拦,这也是美国现存少数部族的现状,在电影《追凶风河谷》中更是将如今印第安保留地缺少法律监管和政府重视的现状暴露无遗,很难说这里是否适合美国公民生存,但它确确实实养育了那些不愿放弃自己家园和文化的在夹缝中生存的印第安人,这本身就非常讽刺,这本书本身不就是一种讽刺吗?而作者本身也是一个德印混血,从白人到来,印第安的文化就再难纯净了。法国,多美好啊!
你不能融入美国社会,就会被时代淘汰,美国如愿以偿的把所有文化吸收,变成自己的再去释放,《美国众神》中对于文化趋同的恐慌要更甚,当我们集体崇拜金钱、媒体和网络的时候,又能指望什么保住我们纯净的文化历史呢?
《鸽灾》读后感(二):旅鸽的遗产
对于一本书来说,取一个贴切并且能够吸引眼球的书名总是很难的。不是每本书都能仅凭书名就再现出一种确切的意象,对小说而言尤其如此。而在短篇小说的集合里,如何使用一个简单的短语将经过编排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把原本破碎的叙述拼贴起来,则更是鲜少有人成功的尝试。但在路易斯·厄德里克这里,这种写作方式却是驾轻就熟的。譬如《鸽灾》一书中,书名虽取自首个短篇的篇名,却也是贯穿始终的钥匙,直指真相:鸽灾,即是历史的荒诞。
与成名作《爱药》有所不同的是,长篇小说《鸽灾》中的多个故事在结集出版前就已经作为短篇小说在《纽约客》等杂志上单独发表。虽然延续了厄德里克作品中既适合连贯阅读,分开阅读也毫无影响的特点,《鸽灾》中的故事却无疑显出更强的独立性。其中内容涉猎广泛,从家族传说到异教组织,从情窦初开到同性情结,从杀人案到绑架案,厄德里克在故事背景的构建上显然有着更为强大且复杂的野心,使得整本书成为一部有关虚构小镇普路托的百科全书。
鸽灾是北美洲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十九世纪初,自然学家亚历山大威尔逊曾如此描述他在肯塔基遭遇一群旅鸽的场景——“一场龙卷风,马上就要把房屋和地面上的一切都摧毁掉”。而这种昏天黑地如同末日降临的景象在体现大自然造化神奇的同时,却也反映出背后的因果逻辑:正是因为欧洲殖民者将原本与旅鸽和谐共存的原住民赶出了他们的土地,并且种植了大量旅鸽可以食用的农作物,才诱发了这样的鸽群大爆发。这种真实的荒诞建立在另一则荒诞的真实之上。彼时,北美这片等待发掘的土地上,种族矛盾正愈演愈烈,白人抢走了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却反过来将这些深肤色的原住民视作劫匪、强盗和杀人犯。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四个印第安人因为路过凶案现场就被认定为凶手并处以私刑的情节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小说中的凶杀案也的确借鉴了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即斯派瑟凶杀案),其中因果联系与书中细节相似之处极为明显。但厄德里克并未沉浸于对这一轰动性事件的经历描述,相反,在叙述者发出了应有的声音以后,她将视角转向故事发生地居民生活所受到的一连串影响。不止是当时、当地,在白人与印第安人不可避免地交往、通婚、冲突的过程中,伤害仍在继续。爱与被爱的困境之外,是仇恨,是偏见,是执念在发声。
小说采用了多角色的交叉叙述,将小镇普路托中上演的爱恨情仇向不同的方向延展开去,人物和情节如大树一般枝繁叶茂。而在小说的最后,同时身为幸存者和见证人的女医生将小镇的历史大事逐一梳理,收拢了故事的网兜,完成了求解与和解。在这错综复杂的有关血缘、种族、信仰与忠诚的故事迷宫中,印第安人所遭受的不公对待令人愤慨,每一个角色的成长和丰满也同样令人感动。而当一切都不复从前,当小镇从梦想走向荒废,历史终将在时间齿轮的摩擦中化为飞扬的尘土,所有的荒诞与真实,不过是已经灭绝的旅鸽在天空投下的一片阴影。“随着年岁渐长,故事渐渐变成我们真实的生活。”
《鸽灾》读后感(三):错版的美国邮票
你集过邮吗?美国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小说《鸽灾》中有人感慨:集邮也有阴暗面,所有的集邮爱好者都会有自己的喜好,这可能是个祸端!譬如小说中的奥克塔夫喜欢错版的邮票、加印的邮票,稀奇古怪的邮票,发展到后来,是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有缺陷的邮票。水渍、破损、血迹,这似乎是古怪的向往,然而这些元素同样构成了现代性的灾难,被有些人烙在记忆中,被更多的人轻描淡写。印第安人生活的土地,像一张错版的美国邮票。
厄德里克是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旗手,曾以小说《爱药》探讨印第安民族的现状和出路。而《鸽灾》触及了更细碎的情感:在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上,安定感渐失,必须与不友好的外部世界互动,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读者可能被简介中耸人听闻的凶杀案震惊。白人农场主一家被杀,路过的四个印第安人救出幸存的女婴,却被误为凶手,其中三人死于私刑。自此,这一案件不再受到追究。作者无意展开推理,案件的始末仅是贯穿全书的一根似有若无的线。许多人的命运被改变了,其中的血泪纠结最后却像一张错版的邮票,轻飘飘、冷冰冰地呈现出碎片般的线索。这并不奇怪,因为这起案件的见证者们大多不甚挂怀,此案仿佛已随时光而逝;同时,更多平凡的、不引人注目的故事,本质上与之相似,由来已久的渊源一次次调换了对象。
要挖掘最隐秘的情愫,作者让四个角色轮番自述。一个个琐屑、私密的片段,恰是这片土地的真实。小说的背景设定于20世纪,种族间的流血冲突已过去许久。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与白人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如错综渗透的枝蔓,殊难厘清出处或交集。他们可以恋爱通婚,可以结为莫逆,在危难关头也常有善良的人施以援手,但在心理上,仍有一条看不见的界限。最突出的,是信仰上的拒绝同化——神父与印第安家庭的言语交锋非常精彩,后者固守城池的态度颇有喜剧色彩,诸如奄奄一息的老人看到神父到来,犹如被打鸡血般瞬间起死回生,等等。我们以为是可以超越种族的爱情,也生出几分芥蒂,一起诡异的绑架案便是因此而起:一个白人男子有个印第安情妇,对方的弟弟前来索贿,白人男子提议对方绑架自己的妻子,以便他从妻子处取钱。事后,白人男子又决计离开妻子与情妇生活,未料始终感觉隔阂,遂向妻子自陈其罪。
至于印第安人被诬有罪,亦非个例。小说中的穆夏姆在搅和进凶杀案之前,就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某户的妻子被杀,人们不去怀疑连夜逃走的丈夫,却云集于穆夏姆的住所,向这位住得最近的印第安人兴师问罪。小说中滥施私刑的白人一直被公认是个和蔼的人,这样的人能毫无愧疚地罔顾法律、害死无辜的印第安少年,其中的偏见一言难蔽。同样的,凶杀案的幸存者明知真凶另有其人人,抵触的仍是印第安人。可她身不由己地爱上了一个印第安少年,每当他们的距离更近一步,她就迂回粗暴地把他远远推开。
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白人对印第安人怀有一种施恩的优越感,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倨傲,怀有一种不容置疑、不容侵犯的刚愎,似不在意故事是如何开始的。一切缓慢地变味,渐难以弭合。如同书名“鸽灾”,铺天盖地的鸽子以作物为食,人类用尽手段把它们变成口粮,谁会想到有朝一日,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会绝迹,又有谁缅怀它们的绝迹?
厄德里克埋下了“爱药”,一枚作用重于价格的“邮票”。疯癫老人穆夏姆分明很知道如何使用它——联络感情、追求不可得的爱情。而所谓的爱好者,看见的是价格,小心翼翼地珍藏,待价而沽,忘记了它们原本只是脆弱的小纸片,不易保存。有人问,集邮自何时始?老普林尼时代的邮票是真是伪?倘若它的价值是联结,定古已有之,应得永续。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文明,亦不会只是一枚被陈列却无用的错版邮票。
《鸽灾》读后感(四):随着年岁渐长,曾经听过的故事,渐渐变成自己的生活。
《鸽灾》,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印第安女作家露易丝·厄德里克2009年发表的最新小说,进入年度普利策小说奖最终竞逐名单,遗憾的败给伊丽莎白·施特劳特的《奥里芙·基特里奇》。小说面世十年来,没有一个导演敢接单翻拍成影视剧作,因为这本讲述印第安人故事的小说,太厚重,也太锥心刺骨了。 小说设定的时间在20世纪7.80年代,但会通过角色的回忆或亲口讲述,将时间和空间闪回到19世纪末。作者通过四个年龄、种族、文化程度和职业特点各不相同的角色,向我们徐徐铺开一张美国印第安人的“清明上河图”。《鸽灾》完全是一部关于印第安人的美国往事:在一个多世纪前,美国白人因为淘金梦,开始挺进西部。而加拿大的梅蒂人(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后裔),在加拿大政府的怂恿下,经当地印第安人引领,一路向南穿越国境进入美国最北的达科他州,开辟新天地。而这里也是美国政府给印第安人安排的保留地之一。 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表面看似和睦相处,但深存于美国白人内心的偏见,始终不能和印第安人完全平等以待。白人的潜意识里,对印第安人虽不像黑人那样毫无人道,但始终有一种“是我将你们从荒蛮带入文明”的居高自傲的态度。而生存环境恶劣的北部,没有黑人让他们发泄情绪,印第安人就成了白人们肆意泄愤的对象。 小说通过一位退休印第安酋长的回忆,揭露了近百年前一起耸人听闻的事件:白人农场主一家被灭门,路过的四个印第安人,进入犯罪现场,救了唯一幸存的母婴。但却被当地极端民族主义的白人们(还都没有前科)认为是杀人凶手。偏见不仅战胜理智,更凌驾于法律之上。未经任何司法介入,四名印第安人中的三人,被处以私刑绞死在今天成为旅游景点的一颗大树上。没被绞死的那个,就是讲述故事的老酋长,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有一半白人血统。 事件过去很多年,虽然大家都知道凶手依然逍遥法外,但作者并没有意图创作一部推理探案小说。她只是借这起事件,将整个自留地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 被人为割裂了历史,被历史强行拖入不被惦念的洪流。印第安人从来都是北美这片土地的主人,但从来都没有被人尊重过。他们以为通过抗争获得白人的尊敬,但更多的只是恐惧;他们以为通过妥协能够赢得白人的认可,但几百年来的水乳交融并没有将印第安人扶上台面。在今天的美国,印第安人的地位甚至不如黑人。 作者通过马尔克斯式的创作手法,将自留地印第安人与白人的“百年孤独”琐碎的、荒唐的、毫无仪式感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感觉篇幅至少能省去三分之一,因为到三分之二处,已经能够猜到凶手是谁。但毕竟,这真的不是一本推理探案小说,虽然那个惨绝人寰的杀人案和惨无人道的私刑,贯穿始终。作者更多的是表现案件和私刑百年来对自留地印第安人和白人生活的影响。那种破碎的、荒诞的、错位的生活。就如同故事中女孩父亲的癖好——收集特殊年份的邮票、印刷错误的邮票,甚至是灾难事故中染血的邮票。他认为邮票的价值是和血腥程度成正比的。而故事中所有的角色,都会或多或少地让人产生错乱的感觉:当年幸存的女婴,被嫌疑最大的家庭收养;而侥幸逃过私刑的人成了最后一任酋长;被处私刑的后代,自立门户传宗立派在当地是李洪志般的存在!不仅圈钱骗色还家暴妻子。而其妻子的叔叔,就是当年灭门惨案的真凶。这个真凶装疯卖傻,被收容在精神病康复中心,酋长的外孙女勤工俭学在病院打工,刚好照顾这个凶手。而凶手的主治大夫,就是被他灭门那家幸存的女婴。这个被救下来的女婴,长大后和当地印第安少年通奸,少年长大后成为自留地印第安人大法官,专为印第安人谋权……如此的自由、如此的混乱,却并不令人感到异常的唏嘘,对!因为很美国! 《鸽灾》出版后,印第安文化研究者按图索骥,从厄德里克的字里行间,翻出1897年一起真实发生过的灭门案,和小说中描述的基本一致,厄德里克甚至直接引用了“圣迹”这个真实案件中被滥用私刑的人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太具讽刺意味了! 到底是印第安人该感谢白人引领他们步入文明,还是永远将白人视为劫掠他们森林和土地的贼寇?答案只有印第安人自己心里有数。但明摆着的,是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仇恨、歧视和偏见长久以来依然存在。这难道不是贼喊捉贼的心理?这同样很美国。 往事随风,往事匆匆。但往事并不如烟!有些事,绝不能当没发生过……我们还小时,破碎的语句四散在周围,故事还未形成。随着年岁渐长,曾经听过的故事,就渐渐变成我们的生活……
《鸽灾》读后感(五):《鸽灾》:美国印第安人生活全息图(译者序)
《鸽灾》:美国印第安人生活全息图
(译者序)
《爱药》中文本问世后,路易丝•厄德里克对中国读者来说已不再陌生。厄德里克是当代最有才华的美国作家之一。1984年,长篇小说《爱药》获美国书评家协会奖,年仅三十岁的厄德里克由此蜚声文坛。1986年,厄德里克的第二部小说《甜菜女王》获美国书评家协会奖提名。2001年,《小无马地奇迹的最后报告》入围全国图书奖。2006年《沉默的游戏》获司各特•奥台尔历史小说奖。2009年,长篇小说《鸽灾》入围普利策文学奖。2012年,长篇小说《圆屋》获全国图书奖。2015年,厄德里克获得国会图书馆美国小说奖。2017年3月,幸运再次降临,长篇小说《拉罗斯》获美国书评家协会奖。迄今,同时获得过美国书评家协会奖和全国图书奖两个桂冠的均是声名显赫的文坛大家,他们是:约翰•奇弗(John Cheever)、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雪莉•哈扎德(Shirley Hazzard)和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
厄德里克不仅是成就卓著的长篇小说家、诗人,还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她自幼浸淫于齐佩瓦部落口头叙事传统,是讲故事的行家里手,可谓最会讲故事的美国作家。她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与印第安口头叙事对她的滋养、她从小养成的讲故事能力是分不开的。她曾获纳尔逊•阿尔格伦短篇小说奖(1982),七次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厄德里克是《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杂志短篇小说栏目的常客。长篇小说《鸽灾》中的多个故事在纳入长篇小说出版前就已在《纽约客》等杂志上作为短篇小说单独发表:《恶魔撒旦:星球劫匪》和《哥斯拉修女》分别在1997年和2001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夏门戈瓦》2002年发表于《纽约客》;《鸽灾》和《普路托的灾难邮票》2004年发表于《纽约客》;《城镇梦》2006年发表于《北达科他季刊》;《毁灭》和《请进》(发表时名为《格利森》)同年发表于《纽约客》;《爬虫园》2008年发表于《纽约客》。《恶魔撒旦:星球劫匪》和《鸽灾》分别于1998年和2006年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 ,《夏门戈瓦》和《普路托的灾难邮票》分别入选2003年和2005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
《鸽灾》(2008)一书除曾入围普利策文学奖,还获得了阿尼斯菲尔德•伍尔夫图书奖与2009年明尼苏达州图书最佳小说奖,入选《纽约时报》畅销书,被《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列为年度最佳图书。该小说与《圆屋》(2012)和《拉罗斯》(2016)构成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第一部和第三部的出版时间相隔八年。这三部小说每一部都获大奖,实属罕见。《鸽灾》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属于典型的地域小说,开辟了厄德里克作品中继小无马地保留地之后又一处虚构的故事发生地——普鲁托小镇和保留地。厄德里克沿用她钟爱的写作模式,用四个叙述者(埃维莉娜、安东•库茨、马恩•沃尔德和科迪莉亚•洛克伦)讲述二十个故事。相比她的其他长篇小说(如《爱药》),《鸽灾》的叙事者数量并不多。她串珠成链,将这二十个故事组织成长篇小说。《鸽灾》借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四个叙述者之口,讲述了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主要是小镇和保留地)近一百年中沃尔德(白人)、皮斯、哈普(白人)、穆夏姆、库茨、洛克伦(白人)等家族数十个人物间的枝节交错。“一些人身上既流淌着罪人的血液,也流淌着受害者的血液”,其中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白人约翰•怀尔德斯特兰德“身陷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同他爷爷如出一辙:他爷爷也有个私生女,也就是穆夏姆的妻子”。多个案件驱动着小说的情节发展:农场主白人洛克伦一家数人被杀,凶杀案扑朔迷离,穆夏姆等人被白人认定为凶手,伊莱克塔•霍格的弟弟疯狂地爱上了洛克伦家的一个女儿,他在凶杀案发生后连夜逃跑,也被误以为是此案的真凶;比利•皮斯绑架姐姐情夫的妻子;他的外甥科温•皮斯偷盗小提琴,后来神奇地成为一个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鸽灾》中,农场主白人洛克伦一家五口被杀案始终笼罩在小镇和保留地数代印第安人和白人心头,而这一凶杀案以历史上的斯派瑟凶杀案为原型。
小说《鸽灾》的凶杀案是血腥的。1911年,在虚构的北达科他州普路托镇上,洛克伦农场的一个白人家庭两代五口被枪杀,农场主背部中枪,现场血腥。印第安人穆夏姆、阿西吉纳克、卡斯伯特和圣迹路过该农场,救下了幸存的女婴,偷偷写信告知当地治安官农场还有一人幸存。治安官等人前去找到了女婴。一天,醉酒的穆夏姆说出以上事实,一群白人就此栽赃穆夏姆等四名印第安人,指责他们是凶手,还愤怒地骑马冲进保留地上的教堂,从神父手中抢走藏匿在那儿的穆夏姆等人。
白人要求杀人偿命,决定将穆夏姆等四人绞死。卡斯伯特被绑在马车后一路拖行,其他三人被押在马车上。半路遇到赶来阻止的治安官,白人便用枪威吓,赶走了治安官。白人想在一个白人屠夫家绞死这四个印第安人,但遭到屠夫拒绝,后在保留地上找到一棵大树,将阿西吉纳克、卡斯伯特和圣迹绞死在树上。穆夏姆的妻子是尤金•怀尔德斯特兰德(参与绞刑的白人)的私生女,他因此逃过一劫。在绞刑现场,有白人不赞成对印第人施以绞刑,但其他人毫不理会。参与绞刑的白人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在1911年的十四年之前,历史上发生过斯派瑟凶杀案。1897年2月14日,在北达科他州埃蒙斯县的威廉斯波特镇(现已不存在),印第安人弗兰克•布莱克•霍克、阿莱克•科多特、乔治•迪芬德、菲利普•艾尔兰和保罗•圣迹五人去奥特•布莱克(小说《鸽灾》中也有同名人物,即女农场主莫德•布莱克的丈夫奥特•布莱克)开的酒吧 买威士忌,奥特•布莱克说酒被一个叫佩博的车夫拉走了。五人于2月17日找到佩博,佩博谎称酒藏在白人斯派瑟家。佩博可能只是想开个玩笑,因为众人皆知斯派瑟是虔诚的信徒,并不喝酒。酩酊大醉的印第安人信以为真,赶往斯派瑟家的农场。当天,斯派瑟一家四代六口(男女主人托马斯•斯派瑟和玛丽•斯派瑟,女儿莉丽•斯派瑟•罗斯,女儿的两个双胞胎儿子阿尔弗雷德•罗斯和阿尔文•罗斯,以及女主人母亲艾伦•沃尔德伦)在自家农场被枪杀,斯派瑟在牲口棚背部中枪,女主人也在牲口棚中被枪杀,其余四人在农场住房中被杀,无人幸存。
五个印第安人很快被拘。阿莱克•科多特和乔治•迪芬德二人先行受审,其他三人待审。阿莱克•科多特有明确的在案发当天不在场证明,但仍被清一色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当场判处绞刑。一审判决后,科多特上诉至北达科他州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支持对科多特处以绞刑,要求有关方面搜集新证据并再审。乔治•迪芬德在庭审中否认杀人,陪审团经过六十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仍无法达成一致,庭审陷入僵局。在法庭上,菲利普•艾尔兰和保罗•圣迹对杀害白人斯派瑟一家的罪行供认不讳,并指认阿莱克•科多特也参与杀害了斯派瑟。
白人认为如果按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再审,没有新证据的支持,科多特肯定会无罪获释,因此决定在再审前劫狱。1897年11月13日晚,一群白人蒙面冲进监狱,持枪威胁治安官,要求放人,最终将关押在一起的科多特、圣迹和艾尔兰三人劫走。科多特等三个印第安人脖子上被套上绳索,被一路拖行至神智不清,根本没意识到会被处以绞刑。白人在屠夫迈尔•拉什家的绞盘上将三人绞死。科多特、圣迹和艾尔兰已死,无人指证迪芬德和霍克也参与了凶杀案,二人因此无罪获释。当地三十多个白人参与了这起绞刑,无一人有前科,绞刑后没有任何白人受到追究。
很明显,小说中的凶杀案借鉴了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二者之间的相似处甚多。第一,案发时间相近、地点背景相似。小说中的凶杀案发于1911年的一个农场,位于北达科他州保留地边缘的一个日渐衰落的虚构小镇普路托附近,对应现实中1897年北达科他州威廉斯波特镇。威廉斯波特镇在此后也逐渐没落,现已不存在。第二,小说与现实中的嫌疑犯都是印第安人,受害者则为住在农场的白人一家,且男主人的死状相同,均为背部中枪。第三,现实中的绞刑地最初都定于白人屠夫家里,不过小说中的白人屠夫不同意提供场地。第四,印第安人在被拖去绞死前都被治安官劝阻。洛克伦农场凶杀案中绞死印第安人的白人和斯派瑟凶杀案中劫狱的白人都有法不依,实施披着“维吉兰提正义” 外衣的私刑,使私人行为闯入本来由国家机关行使的公共权力空间。第五,也是最相似的一点,小说中出现了与现实事件中相重叠的人物——“圣迹”,小说中的圣迹年龄略小一些。第六,参与绞刑的白人都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
虚构与现实并非完全一致,而是保持了一定的张力。二者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小说中没有搜捕、收集证据、庭审等司法程序介入,而历史上的斯派瑟案有过庭审。这样的设定凸显出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印第安人是罪犯,仓促定罪,残忍地实施绞刑。第二,小说中的印第安人没有喝酒,完全清白,真凶是一个名叫沃伦的白人,而现实中斯派瑟案中的五个印第安人都均处于醉酒状态。小说中的圣迹年仅十三岁,无辜、虔诚、孝顺,深受保留地上天主教神父喜爱,绞刑时他因体重太轻,吊了很长时间后才断气;而斯派瑟案中的圣迹约十九岁,身上有受害者艾伦•沃尔德伦(斯派瑟家女主人的母亲)的戒指,戒指上刻有其名字的首字母,他与菲利普•艾尔兰承认杀害了斯派瑟一家。第三,小说中有一个女婴幸存,而现实中无人幸存,且连七个月大的双胞胎都被残忍杀害。小说中的真凶为白人疯子且有女婴幸存这一点可能借鉴了沃尔夫一家凶杀案(The Wolf Family Murder)。
厄德里克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直到小说接近结尾才点明白人沃伦是真凶。在《鸽灾》中,是印第安人发现了凶杀案唯一的幸存者科迪莉亚•洛克伦,告知当地治安官,说洛克伦家还有一人没被杀害,这个婴儿存因此得以活下来。而在毫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穆夏姆等四个印第安人被确认为凶手,其中三人被绞死,成为替罪羊,白人可谓恩将仇报;霍格离奇出走,也被误以为是此案的真凶;埃维莉娜在精神病院实习,看到病人沃伦疯疯癫癫,整天说“我要把他们都宰了”,猜疑沃伦可能是洛克伦农场凶杀案的真凶;科迪莉亚•洛克伦医生从小就收到神秘人送来的礼物,沃伦在临终前委托律师在他死后给她送去一沓钱,与她小时收到的钱的叠法一模一样,这些让她断定白人沃伦就是凶杀案的真凶。三个印第安人被无端夺去生命,蒙受不白之冤,实在是对美国法制的莫大讽刺。1890年的伤膝谷屠杀事件(Wounded Knee Massacre)标志着美国印第安战争的结束。不管是小说中的1911年印第安人被处以绞刑,还是事实中的1897年印第安人被处以绞刑,都发生在印第安战争之后,这说明虽然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结束了,但是仇恨、歧视难以消除,依然存在。小说中的科迪莉亚•洛克伦医生与库茨法官长期保持着婚外情,耽于肉体上的欢乐,但她不愿与库茨法官结婚,即使真相大白、沃伦被确认为凶手,也就是说确定凶杀案与印第安人毫不相关,她依然拒绝为印第安人诊疗。由此可见科迪莉亚•洛克伦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偏见、仇恨之深。
在美国官方文件和白人的书写中,是白人把印第安人从黑暗带入光明,从野蛮带入文明,从原始带入现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叙述比作漂亮的十字绣,那么厄德里克的小说则让我们看到了十字绣的反面。除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偏见、仇恨,小说里还可以读到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采取的一系列复杂多变的政策。“最近,我们去了一趟华盛顿,抗议一项意欲终止我们和美国政府关系的政策——这关系是受协定保护的。”在探险、测绘、建镇等一系列过程中,白人和印第安人不可避免地交往、通婚、冲突。尤其是实施《道斯法案》后,白人掠夺了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与印第安人的冲突更为频繁;专为印第安人开设的寄宿学校在印第安心中留下的伤口永远难以愈合;天主教传教士一心要改变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这些都在厄德里克笔下受到无情地揶揄、嘲讽。
小说里充满了野蛮、暴力、歧视和仇恨,但也揭示了人性美好的一面。年轻的白人约翰•沃格利富有同情心,他坚决阻止父亲等白人对穆夏姆等人实施绞刑。“他噌地跳下马,向他父亲的怀里猛扑过去,他父亲从马鞍的一边飞了出去。两人着地后滑行了一段距离,他仍压在他父亲身上——他父亲的背就像雪橇一样。约翰坐在父亲的胸口,抡起拳头,像锤桌子一样打他父亲的脸。他把整个手臂的力量都集中在拳头上,像是要把木头或是肉给打穿。他的另外一只手扼住他父亲的脖子。”善良的白人女性莫德•布莱克对穆夏姆和他的女朋友琼奈斯十分友好,收留他们六年,“教他们套索、骑马、射击,还有做美味的鸡肉面疙瘩羮”,为他们举办盛大的婚宴。莫德竟为一对印第安夫妇举办婚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印第安人救下了七个月大的科迪莉亚•洛克伦,随后奥利克•霍格和伊莱克塔•霍格夫妻收养了她,很宠爱她,不惜花很多钱送她去东部读大学。
在《鸽灾》中还可以看到埃维莉娜、安东•库茨、马恩•沃尔德、科迪莉亚•洛克伦等人心灵的成长。小说中的穆夏姆让人想起厄德里克其他小说中的纳纳普什,他酗酒、满口谎言、好色,调戏年轻的马恩•沃尔德,迷恋尼芙•哈普,是美国印第安文学传统中典型的恶作剧式人物(trickster)。“鼓在我们看来是有生命的,需要我们给它们食物和水分,庇护它们,关爱它们。鼓在主人睡着时会演奏乐曲给他听。”这些向读者展示了印第安人特有的文化。《鸽灾》呈现了美国印第安人生活全息图,不愧为一部文学名著。在阅读本书之后,再阅读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将会加深理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怀,体味作家对正义这一主题的深刻关注。
厄德里克的十五部长篇小说里人物众多,有大大小小数百个人物,时间跨度一百余年。厄德里克在她的文学世界里从容娴熟地驾驭、调度如此众多的人物,真让人佩服不已。《鸽灾》的人物在厄德里克此前十一部小说中大都没有出现过。阅读《鸽灾》这样多角度叙事的小说如同不断地拼魔方,也像不停地拼图,从支离破碎、看似毫不相关的片段中寻找内在逻辑和相互联系的线索。为方便读者阅读,译者在译本后附上了人物关系图。
多年来,我教授、研究、翻译美国印第安文学,先后翻译过莫马迪的《日诞之地》、厄德里克的《爱药》《鸽灾》和《圆屋》等美国印第安文学名著。目前正受邀翻译她的长篇小说《拉罗斯》和《甜菜女王》。要读懂厄德里克,读出她富有诗意的细腻笔触背后的深意,然后用中文中恰如其分地再现,都不是容易的事。在本书的翻译中我们得到了诸多帮助。美国印第安文学专家罗伯特•尼尔森(Robert Nelson)教授在我翻译《日诞之地》时曾给予无私的帮助。在《鸽灾》的翻译过程中,他同样耐心解释了所有难点。他广博的学识和谦逊的为人让我们感佩交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印第安文学与文化专家玛格丽特•安•努丁(Margaret Ann Noodin)教授热心解答了书中与齐佩瓦语相关的问题,她的帮助弥足珍贵。与年轻译者邹欢女士的合作非常愉快,相互间的讨论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她对原文的理解独具只眼,表达地道巧妙,译艺别有炉锤,不由让我心生感叹:后生可畏,优秀的译者大多是天生的。
张廷佺
2017年3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