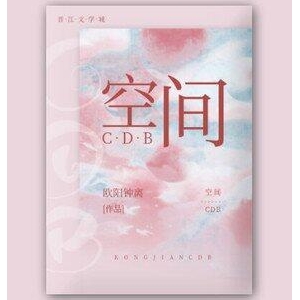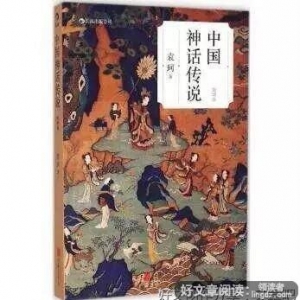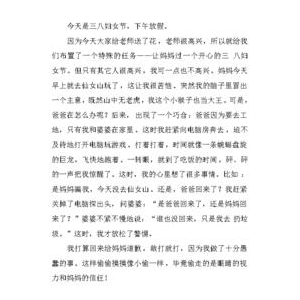炉 = 主持人
互联网与碎片化阅读
炉 | 在互联网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留给阅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因此,以微信文章为代表的碎片化阅读似乎已经成为当下流行的选择。关于这个问题,一方面,碎片化的短小文章更适合互联网的传播形式。但另一方面,碎片化阅读似乎难以触及深层次的话题与讨论。
请问您各位怎么看待碎片化阅读?你们作为文字工作者又是如何应对这种阅读形式产生的影响呢?
何珊珊 | 碎片化阅读大家都在提,但是也说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三个如果要聊这个话题,可不可以提出一些大家不常提到的问题。不如先说说什么才算碎片化阅读?
方瓶 | 首先肯定是不深入的,你可以把这种阅读看做一种(可供暂时停靠的)岛屿。公众号给你推荐的东西,一般都是作者写得最好的。有很多名家的非名作或者是非名家的名作,他们是不推荐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碎片的阅读,再去深入地了解和钻研这些东西。
宗城 | 很多人对一个以前的文学图景有一个幻想,觉得以前很多人读深度文学,即便是被后世知识分子推崇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卖得最好的小说也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能几十万册几百万册地卖。但是新文化干将们写小说,其实只有一万来个人读,只是读的人都是知识精英,所以可以更多地去解读。加上后来这些人占据了文化的解读权,所以现在大家解读新文化运动,解读的都是新文化干将们的小说,很少会去谈鸳鸯蝴蝶派。所以其实严肃小说遇冷,不只是今天的问题。 其实你说没有互联网,大家就不碎片化了吗?
鸳鸯蝴蝶派小说
那种古代的被压抑的民间阅读热情。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转移到了线上,转移到了比如公众号这样的平台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像大家读碎片化的文章成了主流。我个人的理解是它在前互联网时代也是存在的,只是当时书写的定义权不在民间,可能官方或者知识精英都会把它忽略掉,但是它一直存在。
何珊珊 | 我还挺赞成宗城说的。问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的是碎片化阅读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拿到一份杂志,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最先读的就是最后面的那些笑话,然后在有空的时候再去读前面的文章。但是因为现在有太多类似于以前笑话那样的东西在互联网上了。而且通过软件的设计,会让你对这些东西慢慢成瘾。所以碎片化现在就慢慢占据我们几乎所有的阅读体验。这就会导致以前能够通过比较深入的阅读而获取到那些阅读体验,那些系统性的思考,开始被逼到更小的角落了。
宗城 | 我个人觉得今天严肃读物的竞争扩大了,已经不只是文学在抢占我们的注意力了。更多的是比如综艺节目、直播节目、电影、电视,近年娱乐的媒介有一个爆炸性地增长。小说当年为什么会火,其实当年很多人读小说也是图个乐呵,当年王朔的小说很火,王朔的小说有很强的娱乐功能,但是后来大家发现短视频或者电影,更有直接的冲击力。所以一定程度上文学的娱乐媒介被其他东西所分流。我觉得其实文学的读者减少相对来说是个不可逆的问题。但是同时我觉得可以看到的是,还是有很多固定的读者并没有流失。因为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你去感慨碎片化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内心还是需求于有一个更严肃或者说更准确的东西,总会有那么一批人不满足于这种非常轻的阅读体验,他要去读更深的东西,所以今天仍然会有严肃读物存在。
王朔
我想到了前几天读一本书,它讲到米兰昆德拉也曾经说过,担心严肃小说会死,但那时候不是说严肃小说的销量会死,他担心的是严肃小说的精神,他说的严肃小说精神是什么呢?是提供一种我们对生活的复杂性跟开放性的理解。小说不只是一个迎合市场趣味的读物,它的模糊性跟复杂性给予了读者思考,不同于他们承建的东西。这个是严肃小说的精神。但是米兰昆德拉当时担心,在一个更加专制的年代,严肃小说的精神会消亡,因为统治者无法容纳那些模糊与多义的小说了。
当然这个是他自己的思考。其实我觉得他的话有部分确实是应验的,因为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一些比较严肃严酷的氛围中,文学的实验其实是受到压制的。比如在今天的华语地区,现代小说的潮流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被遏制的。
何珊珊 |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感觉我们小时候不是那么被鼓励阅读。特别是你上了高中以后,大家就已经开始跟你说读书是耽误你。我们当时语文老师还去跟其他老师争论,如果你不去读这些东西,孩子怎么写作文。当然他们还是有功利的目的,觉得要为高考的语文作文服务。我就记得我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时候,看到他们意大利的中学老师都是怎么样去引导学生去读书,思考他们读什么书,他们那时候就会读卢梭之类的书,而我高中的时候是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些书的,所以我是在想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样阅读氛围跟我们的教育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的天才女友》同名美剧
宗城 | 然后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像是个被赶着走的状态,有个鞭子在打,我们今天经常说那个词叫所谓的功利主义,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觉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氛围,其实就是在这种赶的过程中逼着自己。今天的舆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提倡大家要多努力,然后娱乐里面的代表都是怎样的人呢?是每天把自己努力得忙成狗的一种人,比如像薇娅、李佳琦他们都非常努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努力。这个时候你会感到非常焦虑,因为你觉得我不如他那么努力。
方瓶 | 而且我有一个观点是,只有你偷懒了,才能感受到一些不那么功利的东西的乐趣。比如说对我来说在窗子前坐着最大的享受是读一本没有用的书,只是在读。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成为一个诗人,更多的是不要去读太多的功利性强的书。
何珊珊 | 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到没有时间读书这一点。我前段时间正好读了唐诺老师的《阅读的故事》。他在书里就回答了:没有办法时间读书怎么办?好像会觉得是不是只有不工作不996了才可以去读书。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其实你不是真正的忙,而是进行了一个价值排序,把读书排到了后面,所以才会觉得你很忙,没有时间读书。而之所以大家会把读书这一个重要性往后排,其实也就是宗城刚才说的我们整个社会的逻辑,逻辑就是逐利的逻辑,所以会让人把这个东西往后排。
方瓶 | (这种逻辑)让人变成一个社会的螺丝钉,你在这里,就踏踏实实干你本分的东西,不要发挥你的个性,你就干涉及你螺丝的事情。把这个当好,剩下的不要管,让我们整个社会的大机器正常运转就行。
宗城 | 我想延伸一点的是历史层面的观点,其实今天的一个现象或者说灌输的价值观,和二三十年代前苏联建设的氛围是很像的,说得简单点就是牺牲这一代人的一部分的休闲,然后换了未来整个国家更好的一个体验。当然我不说这里是好是坏,我是说有时候历史会有一点相似。
5%与95%的的生活
炉 | 《十三邀》里面许知远和马东曾经进行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马东说“世界上只有5%的人有意愿积累知识了解过去,剩下的95%的人就是在生活。你(许知远)是那5%,你就关注你那5%就足够了。”请问您各位怎么看待这种95%与5%的论调?您认为文字工作者真的只用关注那5%就可以了吗?
方瓶 | 关于这个我刚好知道一首诗,是辛波斯卡写的。这首诗叫《对统计学的贡献》,我给大家读一读,
一百人当中
凡事皆聪明过人者
——五十二人;
步步踌躇者
——几乎其余所有的人;
如果不会费时过久,
乐于伸出援手者
——高达四十九人;
始终很佳,
别无例外者
——四,或许五人;
能够不带妒意欣赏他人者
——十八人;
对短暂青春
存有幻觉者
——六十人,容有些许误差;
不容小觑者
——四十四人;
生活在对某人或某事的
持久恐惧中者
——七十七人:
能快乐者
——二十来人;
个体无害,
群体中作恶者
——至少一半的人;
为情势所迫时
行径残酷者
——还是不要知道为妙
即便只是约略的数目;
事后学乖者
比事前明智者
——多不上几个人;
只重物质生活者
——四十人
(但愿我看法有误);
弯腰驼背喊痛,
黑暗中没有手电筒者
——八十三人
或迟或早;
公正不阿者
——三十五人,为数众多;
公正不阿
又通达情理者
——三人;
值得同情者
——九十九人;
终须一死者
——百分之一百的人。
此一数目迄今未曾改变。
我不多做评论,大家用这首诗来说话。我们到底是关注95%还是5%?
何珊珊 | 最开始我和我的同事还是认同了这个结论,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确实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去关注这些东西。
我认为跟阶级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历史上很长的时间,确实大概只有5%的人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的教育可以做得更好,让100%的人都能够受一样好的教育,会不会100%的人都是会在意这些东西的?
宗城 | 我觉得虽然教育是必要的,但是也要看到教育的局限性。这几年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哪怕是有高等学历的人,如果陷入到成见或者政治立场中,也会在发表判断的时候有局限性。教育可能是基础,但是如果说没有配套的价值观引导的话,有时候反而让人更加陷入成见中。
马东这句话,我觉得其实很油滑地遮蔽了政治因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只有5%的人愿意去了解,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教育里面缺少公民教育。一个公民本应就去关心他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就是公民组成的,公民才是社会的主人,无论是政策上的设计,还是选举,都是公民应当去关心的。我们做个历史上对比,你就会发现在08年乃至更早的时候,民间其实有很强烈的关注的热情。而现在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引导上的不同,因为引导的不同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去关心,或者说看不到这个东西。
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一种算法的区隔。这个算法的区隔是什么?比如经常会关心政治思想的人的社交媒体,还是会推送给他一些关于政治思想的内容。但是一个关注网络直播的人,这个算法每天推送给他的还是他感兴趣的东西。算法像一个中立的幌子,反而把不同的群体越来越区隔开了,这就导致5%跟95%之间的那条线越拉越开,大家都处在自己的信息解放里面,都认为自己世界才是更合理的。
我反而觉得今天更深刻的问题,不是说有一部分人愿意去了解,而是说每一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一方。到今天甚至发展成一个只能你死我活的问题。今天的舆论充斥着斗争的话语。从国与国的斗争到主义与主义的斗争,再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他会说你是一个某某的独派,就这样就把你定义出去,其实拒绝了跟你对话的窗口。所以今天一个更严峻的地方就是哪怕连对话都变得非常的不可能,它是一个撕裂的言论场地,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
何珊珊 | 我感觉你讲的像是所有的人都变成了1%,跟5%和95%好像不完全是一个事,他讲的是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分野,但现在连精英内部都会有一种非常可笑的对立,这就不是精英和大众这种对于知识兴趣的分野,而是大家都没有办法站在一起了,这好像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方瓶 |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引用这首诗,而不是用95%和5%这样一个简单的数据去分割人群。人不能被片面的一刀切,但人体部位可以,你说脖子上面是脑袋,脖子下面是身体,那是可以的。但是你说100个人,就不能横着一刀切了吧?
何珊珊 | 但还是有点不一样,你们说的是大家现在对一件事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其实当时他说的是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件事,就他们根本不觉得需要读书,而不是读了书以后会有一个很偏狭的观念。他们甚至都觉得我们这些读书人很奇怪。
宗城 | 同时,其实当时马东跟许志远说的话,是他认为许知远关心那5%就够了,他不需要再去理会那95%的人,但我觉得在生活实践里面不是那么分的。比如像我个人的例子,我小时候是一个生活在小城市的青年,我当时可能是95%的,如果没有这些著书立说的人去照亮我的生活,我又怎么会知道我的可能性呢?很多人他虽然现在没有去想象那种可能性,但是它可以通过书籍等精神食粮去打开这种可能性。如果真的像马东说的那样,许志远只关心那5%就够了,他们只做那种类似于精英式的一个教条的学术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永远只能生活在我的95%里面。所以我反而觉得即便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现在并没有很热情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深入其中,尝试建立一种连接,这种连接无法现在马上起作用, 而是可能成为日后的一颗颗种子。
方瓶 | 这是一种客观的变化,但他们两个人(马东和许知远)讨论的语境应该是创作者,创作者应不应该把他们的作品服务于大众,你写的东西是不是要对大众胃口?你是不是要去研究大众的喜好?
宗城 | 我觉得知识生产界已经有分工了,比如说学院内的学者,他就是做书斋式的学问。科普作者,比如说写《明朝那些事儿》的这种作者,他就是科普给民间,把学院做的知识通俗化,让更多人能知道,其实这个是并行不悖的。我一开始了解明代历史,也是从科普读物开始的。
问答摘录于五月围炉开讲
摘录 | 吴越
海报 | 杨若晴
图 | 图源网络
编辑 | 曹睿清
围炉 ()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菜单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