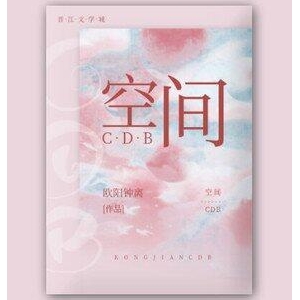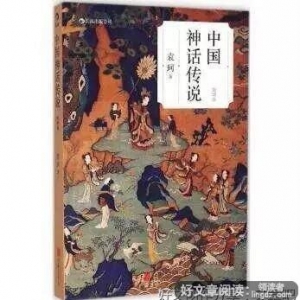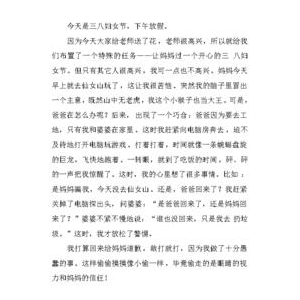幼时的记忆,因为隔了时间,想起来总是特别温馨。
现在想来最想温习的功课就是上山听松涛声了。我家住在泰山山系的东北方向的一个山坳里,幼时接触最多的,就是大山。
虽然住在山里,但是我自幼极少做过真正的农活,做的最多的,不过是在家里刷锅洗碗挑水洗衣做饭,再累些的是垫垫猪圈。那些田里劳作的农活,父母一般不让我沾边,一则我是家里身体最弱小的一个,再则,我也的确没有大的空闲可以帮助田间的劳作。
可是,每到六月天的时候,尤其是雨后,却特别爱跟着大些的孩子去山上拾蘑菇。说是拾蘑菇,其实现在想来我好像也从来没有拾到过几个。但我每次还是坚持跟着去,不为别的,只为去到目的地,坐在山石上静听松涛。
雨后空气特别清新,我跟着几个大些的姐姐们,手里提一只特别小的提篮儿,沿着一脚宽的羊肠小道开始向家门前的山上进发。脚下的土路沙质感特强,绝不会踩到烂泥,就是偶尔踩到沾着水汽的草颗,会不小心闹个趔趄,所以,一般爬到较陡峭的地方,我们都是提前抓住那些长长的韧性十足的草梢儿,记忆里没有人在攀爬过程中摔伤过的,即使是连人带篮子滚个个儿,身上也常常毛皮无损,那个时代的孩子,真似《红楼梦》中王熙凤所言的:我们家的孩子,胡打海摔惯了的。(她是矫情,俺说的倒是实情)。
当然了,路上不仅是风景特别美,带露的草叶儿,彩色的蝴蝶,绿的鲜嫩的蚱蜢,扑扑乱飞的蝈蝈,常常不经意间闯入眼帘,让我们不由自主停下来欣赏;更让我们欣喜的是,一路上不用担心饥渴,随时可以停下来摘酸枣,砸核桃,挖花生,刨草药,一路叽叽咕咕走上去,到达山顶的时候,身上的热汗往往开始流下来。我自幼就不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孩子,人家的孩子一般到达目的地就开始找寻一块合适的草地去四处寻觅着拾蘑菇了,专注的很,可是我,四处找寻的是干净的大石头,最好是俯瞰山下的位置最正的地方,踩上去,居高临下的俯瞰我们来的地方,从村里的第一户开始默数着,这冒烟儿的一家是谁谁的家,这门前大柱子上挂满大棒子串儿的是谁谁家,这老远处还能听见开合大门的吱纽声的是谁谁的家,这狗们狂吠的地方当是谁谁家附近了——
总是这么忘情的看上很久,猜测着哪家正在吃午饭,哪家正在压碾推磨,而哪家正在忙着结草绳,哪家正在把羊圈里的羊群往外赶。
拾蘑菇的姐姐们赶到我身边来的时候,总是自报成绩说;我已经拾了多少多少了,看,篮子底都盖住了!哎呀,你这个苦瓜妮子啊,怎么还在这里发呆啊?!我总是说:蘑菇不长在俺经过的地方,试过一百次了,俺总是找不到!
的确,我跟着她们,几乎每次都是空手而归的,尽管十分努力的去找寻,却总不见蘑菇长在我经过的地方。所以,我跟着拾蘑菇,其实就是为了玩儿,母亲父亲也知道我这方面是弱智,从来不阻挠,还是鼓励我跟着玩儿。
现在做了教育,总是这样想,如果以拾蘑菇来评价学生的优劣,恐怕这辈子我跟优等生无缘了。即使做了教师之后有次领着我那帮子个子比我高些的学生们去西山拾蘑菇,他们钻进树林不大会儿功夫就拾了很多,我呢,傻乎乎的跑了很远,愣是一个都没有看见。后来干脆找块干净石头傻傻的看山下,等学生们提着大大小小的方便袋满载围拢我的时候,他们诧异的说:老师,您一个也没有看见?我委屈的说,是的,真的没有看见,从小蘑菇就躲着俺呢。
俺自己觉得自己这方面建树不大,就自甘堕落,任由她们惊呼拾到了多少多少,俺从不羡慕,俺还有事情可做,就是坐在松树地下听松涛。母亲怕我拾不到蘑菇会难过,总是在出门前特别嘱咐,孩子,拾不到不要紧,回来打一篮儿猪草来,我也夸奖你的。我这人从小就小性儿,哪怕拾不到蘑菇,也喜欢让母亲夸奖,母亲特别聪明,总是想办法调动我的积极性,就引导我往别的特长上发展,比如打猪草啊,摘酸枣啊。只要我把透着红意的酸枣往母亲正在咔咔剪布的手里这么一塞,嘻嘻,不出几分钟,母亲就会停下活来夸我能干。其实,背后的姐姐正在撇嘴呢,她每次出去拾蘑菇,总是拾到满满的一大篮子。回来后可不得了了,她对蘑菇过敏,从来不能吃一个。
跑题了。俺最惬意的事情不是拾到蘑菇,而是坐在干净的大石头上静听松涛。山林里静寂无声,很有王维描写的那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感觉,不过不独夜里寂静,日里同样寂静的很,大家纷纷四处找寻蘑菇去了,当一阵阵山风吹来的时候,静静的听吧,稠密的松树林立只听到簌簌的声音,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像是海上的浪头无声的打过来,又涌向远方。那是细密的针叶间亲密的私语,是带着湿气的山风吻过针叶时发出的温柔的鼻音,还是松树们集体召开的演唱会,我常常这么揣测,树是有生命的,它们的快活的舞蹈和统一的让人感叹的语言,给人带来的感觉的美妙,那些没有听过松涛的人是无论如何难以体会到的。
听吧,没有半点杂音,没有一丝不和谐,任何美妙的音乐都无法模仿的出的。后来知道了一些词,所谓天籁大约就是指它了。怪不得诗人柯岩在悼念周总理的诗中这样写道:松涛阵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唯有松涛,是最能作为这样神圣使命的使者的。
坐着听累了,躺在石块上看着松林听,看它们如何快意的摆舞,看树隙间蓝天如何不杂一丝尘埃,看松针里流动的绿意如何在夏日的雨露里更加滋润;石块洁净,温厚,直到把爬山的疲劳全部驱净。
我常常这样想,现在的孩子,还有谁能有机会体会到这种来自自然的纯粹的宁静?他们没有这样的情致,即使有,他们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即使有了时间,恐怕也难以找寻这样的一片松林了吧。如果有这样的一对男女,能够携手踏上泰山,在松树密布的松林深处,静静的相守,什么也不要说,彼此能够听懂天籁的意旨,他们的生活就不会被无休止的喧嚣堵塞。
终老山林的魏晋风流人士,还有梅妻鹤子的林逋,我想,这些人一定会对美丽的松涛痴迷过。“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绝世独立的陶渊明,难道不是登上山巅听着松涛而由衷发此感言?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如果不是真正登高岗而观望,而思考,人生的真谛怎么会如此超前的定位在归于自然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