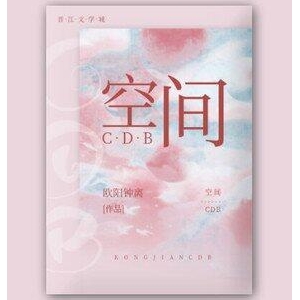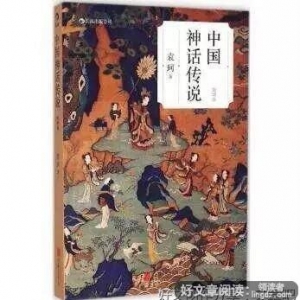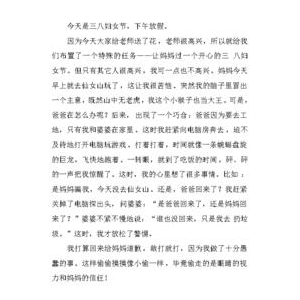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整理》是一本由阮元 校勘 / 劉玉才 整理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页数:54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整理》读后感(一):【轉】段玉裁: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
六經,猶日月星辰也。無日月星辰,則無寒暑昏明;無六經,則無人道。爲傳注以闡明六經,猶羲、和測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 孔子既没,七十子終,而經多岐或。漢初,儒者各述所聞,言之詳矣,而書不盡傳。迨鄭康成氏,囊括百家,折衷一是,其功冣鉅,而其要在發疑正讀,其所變易,其所彌縫,蓋善之善者也。顧鄭氏於六經不盡注,自是而後,南北學者,所主不一。唐人就所主爲《正義》焉,貞觀中,有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唐以前各家經本乖異,立説參磋,皆於是焉可考;又有顔師古奉勅考定《五經》,凡《正義》中所云“今定本”者是也。至宋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於是或合集爲《十三經注疏》。凡疏與經注本,各單行也,而北宋之季合之,維時《釋文》猶未合於經、注、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夫合之者,將以便人,而其爲經、注之害,則未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經本,存者尚多,故課士於定本外許用習本。習本流傳至宋,授受不同,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諸單行之疏,而未必爲孔頴達、賈公彦所守之經、注也。其字、其説,乃或齟齬不謀,淺者乃或改一就一。陸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自有《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同異,抑尠矣!有求宋本以爲正者,時代相歫稍遠而較善,此事勢之常,顧自唐以來積誤之甚者,宋本亦多沿舊,無以勝今本,況校經如毛居正、岳珂、張淳之徒,學識未至,醇疵錯出,胷中未有真古本、漢本,而徒沾沾於宋本,抑末也。 我國家列聖相承,尊崇經術,遠邁前古。恭逢皇上修明備至,其閒鴻生鉅儒,往往講明有過唐宋者。臣玉裁竊見臣阮元自諸生時校誤有年,病有明南、北雝及常熟毛晉《十三經注疏》本紕繆百出,前巡撫浙中,遂取在館時奉勅校石經《儀禮》之例,衡之羣經,廣搜江東故家所儲各善本,集諸名士,授簡西湖詁經精舍中,令詳其異同,鈔撮會萃之,而以官事之暇,乙夜㸐燭,定其是非,會家居讀《禮》,數年乃後卒業。分肌擘理,犂然悉當,其學贍,其識精,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坿《釋文校勘記》二十六卷,俾好古之士,以是鱗次櫛比,詳勘而丹黃之,家可具宋、元本,人可由是尋真古本、漢本,其在今茲有是書,較陸德明《釋文》之在唐初爲無讓矣。抑校讎經、注之書,亦猶步算之於日月星辰也,千百年而步算有差焉,則隨時修正之,千百年而經、注之譌又或滋蔓焉,亦隨時整飭之。又烏知今日之不譌者,異日不且譌哉?所望步算日月星辰者,有如此日而已矣。 嘉慶戊辰歲酉月,金壇貢士前巫山縣知縣臣段玉裁記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整理》读后感(二):【转】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平议
作者:刘玉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校勘之学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石,对于儒家经典文本的校勘,更是经学乃至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在写本时代,校订刊正经书文字,即已超越经师授经讲学需求,而承担起正定学术的职能。两汉经今、古文之争后,刊立《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及至唐《开成石经》,无不致力于通过文本校订刊正以确立权威定本。五代冯道据唐石经刻印九经,成为儒家经典刊本之祖。两宋以降,刻本渐繁,但经书文本歧异并未消弭。儒家经典相沿有“五经”、“九经三传”、“十三经”诸说,加之权威注释义疏,蔚为大观。诸经之经注与义疏,原本别行,南宋坊刻本为便利起见,汇合经注、义疏、释文于一书。南宋之后,十三经的组合方式,经、注、疏、释文的文本结构,逐渐形成固定搭配,并成为士人阅读的最基本文献,影响深远。然而由于经疏文字率而搭配,章节分合、长短无定,而且相互迁就改易,又人为造成经典文本的混淆。宋版诸经注疏在宋元明三朝不断刷印,但后印本多有补板、修板,字迹漶漫,明代又据之翻刻为闽本、监本、毛本诸本,文本讹误更甚。清康乾以降,考据之学兴起,校订经书文字渐成风尚,而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的校勘成果引进之后,亦颇为中土学人所推重。惠栋、卢文弨、浦镗诸儒可谓开风气之先,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踵行其后。阮元在此学术氛围影响之下,于嘉庆初年出任浙江学政、巡抚期间,邀集江浙学人编纂《经籍纂诂》,创建“诂经精舍”,并组织汇校《十三经注疏》,纂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世誉为清儒经典校勘集大成之作。
据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记载,阮元设立“十三经局”,延客校勘《十三经注疏》,约始于嘉庆六年。主其事者段玉裁,分任其事者有臧庸、顾广圻、徐养源、洪震煊、严杰、孙同元、李锐等人。各人因情况有别,实际参与的时间和程度并不一致。《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期的补校、审订,及至最后刊刻成书,当以严杰出力最多。今存《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的补校部分,多为严杰的手迹,足见一斑。此外,徐养源或参与其事较久,因迟至嘉庆二十一年印行《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进呈本,分校《仪礼注疏》尚有较多与之相关的内容增补。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纂修流程,文献记载无多,幸赖国家图书馆近年入藏李锐分校《周易注疏校勘记》的稿本和誊清本,据云得自阮氏后人家藏,可以略窥一二。李锐,嘉庆初年应阮元之聘,先从事《经籍纂诂》和《畴人传》的纂修编辑,后参与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分任《周易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及《孟子注疏》三书校勘之役。国家图书馆所存《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经与同馆藏李锐《观妙居日记》原稿本比对笔迹,当属李锐手稿。据《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誊清本和刻本提供的信息综合分析,其纂刊流程可作如下推测:(一)分任者李锐完成对校初稿并作自我修订;(二)严杰校补调整;(三)阮元批校;(四)誊清成稿;(五)孙同元复核,并有少量增补;(六)严杰校订(或与段玉裁同校);(七)刊刻成书(刊本校样仍有少量增补)。故诸经校勘虽未必如阮元所云“授经分校,复加亲勘”,但是校经、补校、审订、复核,存在相对严格的流程,有助于提高校勘水平。此外,从稿本到刻本,文字内容甚至文本结构都有更动,而这些变化背后寓含有丰富的学术信息。
阮元广罗善本,延纳学界精英,纂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堪称经典文本校订的典范之作,迄今恐尚无出其右者。阮元自矜为“我大清朝之《经典释文》也”。“校勘记”刊行之后,颇为学界所重。清焦循有评价曰:“群经之刻,讹缺不明。校以众本,审订独精。于说经者,馈以法程。”(《雕菰楼集》卷六)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亦云:“清儒校勘之书颇多,然其惠后学,无若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凡志儒学者,无不藏十三经;读注疏者,必并看校勘记,是学者不可一日无之书也。”阮校的优长之处,约略有三。
首先是广罗善本,备列异同。根据全书凡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宋版十行本为主,与其他宋版诸本以及明刊注疏本(闽、监、毛)进行对校,又以《经典释文》、唐宋石经以及各经注本作为经注文字的校勘材料。此外,《十三经注疏正字》《七经孟子考文》以及各种经解著作亦在参考文献之列。阮校之前,无论宋儒毛居正、岳珂、张淳校经,还是山井鼎《考文》、浦镗《正字》,不惟规模有限,参校版本亦屈指可数。而阮元借助地位之便,又有学界精英协力,得以博采唐石经、宋元善本、明刊旧钞,以及当代通行本,施以详尽对勘,备列诸本异同,在校勘规模和采纳文献数量方面,确可称前无古人。
其次,校勘理念先进,方法全面。山井鼎、卢文弨已经揭示“经注”、“义疏”、“释文”原本别行的文献实际。卢文弨指出,浦镗《正字》对于古书的层次构成缺乏基本区分,段玉裁则更进一步提出“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之说。“校勘记”正是遵此文献理念,在以注校经、以疏校经注的同时,不妄改文字,充分考虑并区分文本的历史层次。《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校诸本,不仅备列文本异文,还详细记录卷题形式、提行缩格以及文字磨改、剜挤、剜改、补刊之类版刻信息,这对辨析文本源流,鉴定版本,校订经、注、疏、释文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脱、衍、倒,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亦颇为全面。山井鼎《考文》多依赖对校,对于诸本皆误的情况缺少按断。浦镗《正字》则因所据版本无几,故校语多误作、当作、疑作之类,颇有疑所不当疑、以不误为误之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弥补了《考文》《正字》的缺陷,校勘方法虽仍以对校为主,但同时注重以注校经,以疏校经注,及注文前后互校,并旁取他书引据,广泛使用本校和他校之法。对于诸本皆误,且无他书可证者,则引证文献或援据注疏体例,加以考订,且多有不刊之论,堪称清儒理校成果之典范。
再次,学术考订成果丰硕。《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编纂正值乾嘉学术鼎盛之时,故得以广泛汲取汇辑汉唐古注、校订经书文字的成果,可谓取精用弘,博考详辨。以《周礼注疏校勘记》为例,总计罗列5821条校记,不仅征引历代文献遍及四部,还列述清儒惠士奇、惠栋、戴震、臧琳、段玉裁、孙志祖、卢文弨、程瑶田、沈彤、方苞等十余人的考订成果,并施以辨析取舍。“校勘记”参考清儒成果,意图集思广益令校勘工作更加详备,而其间辨析取舍则不仅体现校勘者的理念,同时亦透露出清儒成果的传播与影响幅度,可略窥当时学界样貌。校勘记引述的清儒校经成果,许多并未成书流传,故还有保存文献之功。
当然,诚如前贤批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局限与缺失,且与上述优长之处长短互现。“校勘记”以备列版本取胜,但实际参校版本仍颇有缺失。其中既有因存藏所限无缘利用者,也有因不明刊刻源流而忽视者。各经卷首所列引据各本目录,亦不乏与实际采用版本不符或转引他人校本者。以“校勘记”所用底本而论,凡例称《周易》等十经以宋版十行本为据,实际情况与此并不相符。阮元所谓宋版十行本,学界已倾向只是元刊补修本,且并非注疏萃刻之祖本。各经引据参校本多寡不一,缺失情况或与分校者文献功力相关。如《孟子注疏校勘记》引据14种校本,不惟遗漏了重要的宋本,且直接目验者仅有7种,另外7种则或据前人校勘学著作,或据他人校本,可靠程度自然大打折扣。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凡例”虽云“授经分校,复加亲勘”,校勘亦有相对严格的流程,但诸经参校采摭,实际是各自为政,故成品水平因分校者学术态度、文献功力而异,体例风格亦存在较大差别。总体而言,顾广圻、严杰、洪震煊分校诸经质量较好。“校勘记”采录前人成果,亦不甚严谨。如臧庸的校语多用前人校本,但往往不言出处,致使未列引据各本目录的校本出现在校语中,徒增困惑。《左传注疏校勘记》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存在明显承袭关系,陈书既为“校勘记”提供了基本思路,也提供了大量的校勘事例和他人成果,但只有部分被校勘记标记出来,更多的内容未加注明,需要比照二书才能发现。
正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自身存在缺失,故在其流传之后,不断有补订之作。其中如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周易单疏校勘记》,日本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吉川幸次郎《尚书正义定本附校勘记》、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常盘井贤十《宋本礼记疏校记》等都对阮校颇多补订增益。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整理》读后感(三):【轉】水上雅晴:《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以及段玉裁的參與
【作者简介】水上雅晴,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政法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琉球大学教育学部国语教育讲座教授,著名汉学家。
【摘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是阮元幕府的重要學術活動之一。阮元聘用七名幕友作爲分校者從事校勘工作。另外,段玉裁也參與了校勘工作。但是關於段玉裁的參與情況,有人認爲段氏在編纂《校勘記》時發揮了主導作用,亦有人對這種看法表示懷疑。爲了弄清這個問題,本文以“〇”即圈識爲綫索,不僅對圈識前後的校語之關係,而且對圈識前後的校語與分校者以及段玉裁之關係也加以考察。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整理》读后感(四):【转】王耐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版本考述
本文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第37辑。
学人简介:王耐刚,2005~201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明清学术史。
摘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是校勘學上的一部名著,其版本有文選樓單行本、南昌府學刻《十三經注疏》(通行所謂“阮刻本”)所附錄盧宣旬摘錄本和學海堂《清經解》諸本。這些版本之間,關係複雜。文選樓本有先印後印及挖改修版諸問題,摘錄本則有增刪改乙和底本轉換諸問題,而不爲人所重的《清經解》本在道光初刻本和咸豐補刊本之間也存在重要差別。本文即以上述諸本爲考察對象,略述諸本之特徵及關係。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以下簡稱“《校勘記》”)是清代嘉慶年間由阮元組織江浙學人編修的。在嘉慶二十一年阮元撰寫的《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中說:“昔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慮舊籍散失,撰《經典釋文》一書……臣撰是書(引者按,此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竊仿其意。”由此可見阮元編撰此書之初衷。
關於《校勘記》之版本,學者較爲關注的是阮氏文選樓刊印單行之本(以下統稱爲“文選樓本”)和嘉慶二十一年(1816)南昌府學刻《十三經注疏》所附盧宣旬摘錄之本(以下簡稱“南昌本”)的差別。如傅增湘先生在《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說:“嘉慶乙亥,阮文達太傅巡撫江西,重刊十行本於南昌府學,共四百十六卷,後附《校勘記》,然不若單本《校勘記》之詳備。學者但得阮氏《校勘記》全本,不論何本注疏,皆可據以校讀矣。”實際上據我們調查,文選樓先後印本之間,文選樓與南昌本、文選樓與後來學海堂所刻《清經解》本(以下稱爲“學海堂本”)之間,都有差別,本文試考述之。
張鑑《雷塘庵主弟子記》云:嘉慶十一年冬十月,“纂刊《十三經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成”。據此,《校勘記》之刊刻當在嘉慶十一年。但我們今天看到的多數文選樓本皆有段玉裁嘉慶十三年序,或有段玉裁序並嘉慶二十一年進書奏表,所以學者認爲文選樓本有先印、後印之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一套《校勘記》,既無段玉裁序亦無阮元進書奏表,所以被認爲是嘉慶十一年的初印本。
較早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是日本學者關口順先生,他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說略》一文中說:
文選樓刊本初刻之後,附載有嘉慶戊辰十三年(1808)日期的段玉裁之《序》而冠於全書之首,隨後又附有嘉慶二十一年(1816)十二月日期的《進表》,特爲敬裝十部將之進獻嘉慶帝。例如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文化研究所以及靜嘉堂文庫所藏各本均是附載《序》和《進表》的,這些版本中的校語基本上與初印本一致,與初印本不同之處幾乎僅在於卷首附加上列二文,以及《總目》末葉刻入的校字者名字從嚴杰改爲阮亨。上列版本顯然屬於後印本,大概是在嘉慶二十一年以後印行的。
關口氏認爲《校勘記》一書主體刊刻在嘉慶十一年完成,後來在十三年和二十一年又分別加刻了段玉裁序和阮元進表,同時將總目中的校字者由嚴杰改爲阮亨。但是,經過我們調查發現,不同時期的印本之間,在文字上有重要差別,並非如關口先生所言者。我們所調查并比勘過的文選樓本如下:
(1)《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南圖本”。此本有段玉裁序,無阮元奏表。
(2)上海圖書館藏揚州阮氏文選樓刻本(索書號:002871),以下簡稱“上圖本”,此本有段玉裁序,無阮元奏表。
(3)上海圖書館藏葉景葵舊藏本,以下簡稱“葉藏本”。此本上圖目錄著錄爲“嘉慶十一年刻本”,然卷首有段玉裁 嘉慶十三年序,故當是十三年以後印本。又封面有葉景葵題記,今錄之如下:“凡例內所夾一簽似唐鷦安手書。儀禮缺卷補抄極工整。丙子年以廉價得於上海城內書攤,己卯年重裝訖。揆初記。”其中《禮記注疏校勘記》卷一至卷四,《儀禮注疏校勘記》卷一至卷八皆係抄配。又此本無阮氏奏表。
(4)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盛宣懷愚齋圖書館舊藏本,以下簡稱“愚齋本”。此本有段玉裁序和阮元奏表,故華師大圖書館將其著錄爲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上述四個版本,從有無段玉裁序和阮元奏表這一點來看,以愚齋本刷印最晚,而其他三本印刷之先後則有賴于文字校對。下面我們以《尚書注疏校勘記》與《儀禮注疏校勘記》爲例,來討論上述諸版本印刷之先後次第。
南圖本與上圖本印刷之差異,主要在《儀禮注疏校勘記》中。如:
卷一215條:校語“浦鏜改从艸”,南圖本“从”誤“以”,上圖本、愚齋本皆改作“从”。
卷一315條:出文“賓醴不用柶者”,南圖本“柶”誤“栖”,上圖本、愚齋本皆改作‘柶’。
卷十五284條當爲注文校記,南圖本出文之前原空兩格,誤作疏文之校記,上圖本、愚齋本皆改爲出文前空一格。
又如:
卷七270條:出文“守故之辭”,校云:“浦鏜云‘有’誤‘守’。”南圖本如此,但上圖本、愚齋本皆剜改删去,故此行空闕。
又如:
卷十142條:出文“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校云:“若,《要義》作‘者’。按,‘若也’疑當作‘若然’。”南圖本如此,上圖本、愚齋本出文皆改作“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據文”,校語改作:“‘若’,《要義》作‘者’。許宗彦云‘若也據文’乃‘若據他文’之訛。”
除以上改正訛誤、更改校語、刪減條目外,上圖本、愚齋本還增加了一些南圖本沒有的條目,計二十條。其中卷六增兩條,卷七增一條,卷十一增四條,卷十二增三條,卷十三增一條,卷十四增兩條,卷十五增四條,卷十六增一條,卷十七增兩條。凡增加條目之處,爲遷就原刻行款,多將兩條併作一行,或減省前後條目文字,剜改增補之跡顯而易見。由此可知,南圖本之刷印要早於後來的上圖本、愚齋本。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七第049、050條,今錄之如下:
“楚語稱堯有重黎之後”,有,宋板、十行、監本俱作“育”,閩本亦誤作“有”。
“廢天地”,地,十行、閩本俱作“時”。按,“地”字非也。
南圖本與上圖本順序如此,而葉藏本與愚齋本兩條的順序互換。今按,宋越刊八行本《尚書正義》有兩‘廢天時’,一在‘楚語稱堯有重黎之後’前,一在其後。在前者,毛本作‘廢天地’,在後者毛本作‘廢天時’。出文既作‘廢天地’,則應在‘楚語稱堯有重黎之後’前。據此,則葉藏本與愚齋本爲是,經解諸本與葉藏本同,南昌本刪去這兩條。
又如《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第029條:
“官不至其言”,十行本“至”誤“全”。
南圖本與上圖本文字如此,而葉藏本與愚齋本出文皆作“官不至其賢”,改“言”字爲“賢”。核之毛本《注疏》,則葉藏本、愚齋本所改爲是。
又如《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四094條:
“常修己以敬哉”,常,閩本誤作“當”。
南圖本及上圖本文字如此,而葉藏本、愚齋本則作:
“當修己以敬哉”,當,閩本誤作“常”。
今按,閩本、毛本《尚書注疏》此句皆作“當修己以敬哉”,並無不同。核校《尚書注疏》諸本,惟明監本作“常修己以敬哉”。《尚書注疏校勘記》出文皆據毛本,故此條出文當作“當修己以敬哉”,校記部分則疑作“當,監本誤作‘常’”。若是如此,葉藏本及愚齋本近其實,惟校語中“監”誤作“閩”。
再如《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八第030條:
“吉禮之別十有三”,十有三,宋板作“有十二”,是也。
南圖本及上圖本文字如此,但葉藏本、愚齋本則作:
“吉禮之別十有二”,閩本作“十有三”,非也。
核校《尚書注疏》諸本,此條出文當以葉藏本及愚齋本爲是,校語則當以南圖本、上圖本爲是。
由上述諸例可知,葉藏本、愚齋本改正了南圖本、上圖本的諸多錯誤,因此我們認爲葉藏本及愚齋本的刷印時間要晚於南圖本和上圖本。我們再看下面的例子,《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六第015條:
“天爲過逸之行”,天,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大”。按,“天”字誤。
按,校語中之“大”字之橫畫,南圖本已經斷續不連,但尚可識讀,至上圖本、葉藏本、愚齋本該條“大”字之橫畫已不甚清晰,似作“人”字。至道光時,學海堂重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此條之“大”字遂誤作“人”字。由此亦可考知我們所調查的文選樓諸本刷印之先後。
另外,在上圖本和愚齋本《儀禮注疏校勘記》之間,也存在差異。如:
卷一337條:出文“謂賓客之贊冠者”,南圖本、上圖本文字如此,愚齋本刪去“客”字。
卷十四189條:出文“釋曰”至“於苴”,校云:“疏凡三十二字,今本脱,單疏、《通解》、《要義》俱有。”南圖本、上圖本文字如此,愚齋本校語則改作:“注疏本俱脱,此據單疏本及《通解》、《要義》補。”
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們所調查的四個文選樓本之先後印次爲:南圖本、上圖本、葉藏本、愚齋本。對於此結論,我們有以下幾點需要說明:
第一,我們沒有見到關口順先生所提到的初印本,所以初印本與上述四個版本的差別,有待他日續考。
第二,作出如上推論的前提是,我們所調查的每套《校勘記》內部十三種校記都是同時印刷的,即不存在將不同印次的各經校勘記補配成一整套的情形。但若這一前提不能成立,那麼問題將會更爲複雜,討論需要以每部經疏校勘記爲個案來進行。例如《尚書注疏校勘記》在初印之後至少進行了一次修改,《儀禮注疏校勘記》則至少進行了兩次修改。
第三,如上所述,南圖本、上圖本、葉藏本、愚齋本《儀禮注疏校勘記》皆有不同,而南圖本、上圖本《尚書注疏校勘記》則基本相同。據此,《校勘記》的修改並不是一次完成的,從南圖本到上圖本,主要對《儀禮注疏校勘記》進行了校改,而從上圖本到葉藏本,則主要對《尚書注疏校勘記》進行了校改,而從上圖本到愚齋本,則又修改了《儀禮注疏校勘記》的一部分。這種情況和阮元在《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中所說《校勘記》“連年校改方畢”一語正相吻合。
第四,我們的調查範圍非常有限,其他圖書館所存藏的文選樓本《校勘記》是否與我們上述版本之一相合,抑或與上述四個版本皆不同,我們無從得知。也就是說,我們的調查不能肯定文選樓本改版的次數,在上述各個印次之間,是否有其他印次的印本,亦有待續考。
南昌本因附於阮刻《十三經注疏》之後,故而在《校勘記》諸本中最爲通行,其大致是以文選樓本的後印本爲底本。但南昌本與文選樓本有重要差別,主要表現爲以下幾點:
第一,文選樓是全本,南昌本是摘錄本。南昌本刪去了文選樓本中的部分校記以及各經《釋文》或《音義》的校記。以《尚書注疏校勘記》爲例,文選樓本共有3037條校記,此外又有《釋文》校記388條,兩者合計3425條;南昌本則共有校記1727條,除未附《釋文校勘記》外,另刪去文選樓本校記1312條,又把文選樓卷二、三、四、六、八、九、十一、十二、十四、二十之001、002條,卷十六之101、102條,各自兩兩合爲一條。又如《孟子注疏校勘記》,文選樓本有校記2021條,又有《孟子音義》校記63條,二者合計2084條,南昌本則刪去了79條及《音義》校記63條,新增61條,總計2003條。
第二,部分校記底本之不同。《校勘記》卷首凡例云:
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孟子凡十經,以宋版十行本爲據。《孝經》以翻宋本爲據。……
《儀禮》、《爾雅》無十行本,而有北宋時所刊之單疏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
據此,《儀禮》、《爾雅》以單疏本爲校勘底本,《孝經》以翻宋本爲校勘底本,其他十經則以十行本爲校勘底本。但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尚書注疏校勘記》、《儀禮注疏校勘記》是以毛本爲校勘底本,而非凡例所云之十行本、單疏本。《論語注疏校勘記》則無固定之校勘底本。其他各經,則皆如凡例所云。需要補充的是,《爾雅》經注部分以明吳元恭仿宋刻本爲據,至於疏文部分則以單疏本爲據。
以上所述是文選樓本的情形,至於南昌本則與之稍有不同:《尚書注疏校勘記》、《論語注疏校勘記》之校勘底本均改爲十行本。《儀禮注疏校勘記》的底本則由毛本改換爲《凡例》中所說的單疏本,經注部分主要出於張敦仁所刻嚴州本。其他各經則與文選樓本卷首《凡例》一致。之所以會有底本的變化主要是因爲南昌本是附於所謂“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之後的,因此其出文須與“宋本”保持一致。
第三,南昌本增加、改寫了部分校記。南昌本增加校記不多,主要是利用明監本和毛本,加以“補”、“補校”等字。南昌本所增校記,各經比例不一。仍以《尚書注疏校勘記》爲例,南昌本新增校記11條,其中有6條錄自《釋文校勘記》,因此實際新增校記僅有5條。《孟子注疏校勘記》新增61條,主要是利用明監本和毛本補充文選樓本漏校的異文。至於改寫校記,主要是針對上述幾種存在校勘底本更換的校記而言。
對於南昌本摘錄增改《校勘記》,有學者深至不滿。如嚴杰在《清經解》本《校勘記》識語中說:“更可詫異,將宮保師《校勘記》原文顛倒其是非,加‘補校’等字。因編《經解》附正於此,俾後之讀是記者,知南昌本之悠繆有如是夫。”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錄阮福案語也說南昌本“《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但這些並未具體指出南昌本《校勘記》有何不妥。張文《南昌府學本〈儀禮注疏〉所附校勘記辨正》一文,將南昌本之問題概括爲:第一,忽略原校版本信息;第二,遺漏原校是非判斷;第三,混淆原校版本概念;第四,文字敘述出現錯誤。此文具體指明了南昌本何以“悠繆”。另外,我們在對校文選樓本、南昌本《尚書注疏校勘記》的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例如卷二074條:
“時言東作”,時,宋板、十行俱作“特”,非也。
南昌本相應之條目作:
“特言東作”,宋本同。岳本、閩本、毛本“特”作“時”。案,作“特”非也。
南昌本轉換了出文,并將校記中描述文字作了相應調整。《尚書注疏校勘記》在行文中一般只揭示與出文不同的版本,與出文相同的版本不再說明(僅徐養原如此,他經校勘記或同或否,如李銳所校,則不論與出文同否,一概詳細說明。由此可見《校勘記》的體例並不嚴整),所以文選樓本僅提及宋板、十行。南昌本在轉化過程中要補充版本,所以多了閩本。閩本而外,南昌本還增加了岳本。但是此條是校疏文,不應言及岳本,岳本疑是明監本之誤。
又如卷十071條:
“以紂自絕先王”,十行、閩、監俱脫“王”字。
南昌本相應之條目作:
“以紂自絕先”,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王”字,正與岳本同。
南昌本轉化的問題在於“正與岳本同”一語,此亦是疏文,而岳本並無疏文。孔傳中有“以紂自絕於先王”一語,各本皆同,此處也沒有必要單單引用岳本。又八行本《尚書正義》即《尚書注疏校勘記》所云“宋板”(或稱“宋本”)“先”下有“王”字,疑“岳本”當是“宋本”之誤。
道光九年(1829),《清經解》在學海堂刊刻,《校勘記》亦被收入。《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末有嚴傑跋語,今錄於下:
注疏之善册未有過於十行本者,若毛氏汲古閣本,缺佚錯訛,棼不可理。十行本初次修板在明正德時,即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所載“正德本”,非別有正德注疏本也。正德後遞有修改,誤書棘目,不若毛本多矣。近年南昌重刻十行本,每卷後附以校勘記,董其事者,不能辨別古書之真贋,時引毛本以訂十行本之訛字,不知所據者乃續修之册。更可詫異,將宮保師《校勘記》原文顛倒其是非,加“補校”等字。因編《經解》附正於此,俾後之讀是記者,知南昌本之悠繆有如是夫。錢塘弟子嚴杰謹識于廣州督糧道署,時道光六年八月朔日。
顯而易見,嚴杰主要是針對南昌本撰寫了此跋,以表示其對盧宣旬“摘錄”之不滿。咸豐七年(1857)年,道光時所刊《清經解》的部分書版毀於兵火。至咸豐十年庚申,時任兩廣總督勞崇光命鄭獻甫、譚瑩、陳澧和孔廣鏞主持補刊,故《經解》有道光初刻本與咸豐補刊本之別。
道光初刻本與文選樓本整體差異不大,我們將兩者比勘,認爲道光初刻本更接近嘉慶二十一年的印本,而與較早印本不同。我們在上文所舉文選樓諸印本之差別,道光初刻本之文字皆與葉藏本、愚齋本相同,而與較早刷印的南圖本、上圖本不同。關口順先生也說:“這本《校勘記》(引者按,指學海堂本)缺少《進表》和《序》,而有《凡例》,校語本文大概以後印本爲底本,管見所及,在收入《皇清經解》之時,內容沒有改動。”這和我們的對勘結論基本一致。
另外,道光初刻本也增加了一些錯誤,如前揭《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六第015條“大”字誤作“人”字,就始於道光初刻本。又如《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097條:
“而心傲狼”,狼,古本、岳本、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作“很”,是也。
記中兩“狼”字,道光初刻本皆誤作“很”,而他本皆不誤。又如《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四第111條出文“皇僕生差甫爲穆”,第113條出文“毀揄生公爲穆”兩條,道光初刻本皆將出文中“穆”字誤入校語中,他本皆不誤。
從整體上看,咸豐補刊本作爲道光本的補刊,所用的底本應該是道光初刻本,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各卷卷尾校勘銜名得到確認。如《尚書校勘記》卷十六(《清經解》卷八百三十三),道光初刻本卷末署名作“嘉應生員李恆春校”,到了咸豐補刊本,卷末的題名改作“嘉應李恆春舊校/南海 桂文烜、桂文燦新校”,可見補刊本仍然部分保留了校勘者銜名。第二,咸豐補刊本還保留了若干道光初刻本的版面,如《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七(《清經解》卷八百三十四)第七、八兩頁書版爲道光初刻本原版,卷二十(《清經解》卷八百三十七)的第五至七也是道光原版,並且保留了“嘉應生員李恆春校”的署名。
但咸豐補刊本也對道光初刻本作了相當程度的校改,這些校改使其與文選樓本、道光初刻本之間有了重要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集中在《尚書注疏校勘記》中。括而言之,表現爲以下幾點:
第一,校記或按語詳略不同。舉例如下:
卷一073條:“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浦鏜云:“及”當“乃”字誤。
文選樓本及道光初刻本文字如此,咸豐補刊本末增按語:“〇按,浦云是也。”又如:
卷三001條:“古文尚書舜典第二虞書孔氏傳”,古本如此。山井鼎曰:“古本分爲十三卷,卷內又數篇者,每篇篇題同此,以下不重出,可推知也。”
咸豐補刊本末增按語云:“〇按,唐石經、岳本俱無‘古文尚書’四字,餘與古本同,後放此。”多數情形是咸豐補刊本按語較爲詳細,而文選樓本或略或無。但亦有相反者。如:
卷三016條:“傳麓錄至於大”,大,十行、閩、監俱作“天”,是也。
卷四029條:“此以相尅爲次”,尅,宋板、十行、《纂傳》俱作“刻”,正、嘉、閩本俱作“克”,是也。
以上兩條,咸豐補刊本皆無結尾“是也”二字。
第二,校勘結論不同。例如:
卷二074條:“時言東作”,時,宋板、十行俱作“特”,非也。
咸豐補刊本相應條目作:
“時言東作”,時,宋板、十行俱作“特”。〇按,“時”字非也。
文選樓本以“時”字爲是,咸豐補刊本則以“時”字爲非,二本結論相反。
卷二135條:“故傳倒文以曉民”,浦鏜云“民”恐“明”誤,當屬下句,是也。
咸豐補刊本相應條目作:
“故傳倒文以曉民”,山井鼎曰“民”恐“明”誤,當屬下句。〇按,浦鏜云“明”誤,是也。
文選樓本以爲“民”字當作“明”,咸豐補刊本則認爲“明”是誤字。今按,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云:“‘民’當‘明’字誤。”據此則咸豐補刊本“明誤”上脫“民當”二字,違背浦鏜原意。又“當屬下句”,乃山井鼎說,浦鏜無此說。
第三,條目多寡不同。這涉及《尚書釋文校勘記》卷下142至145四條。今錄之如下:
“銳以稅反”〇按,《尚書撰異》云:治《尚書》者,自蔡仲默以來,皆謂“銳”當依說文作“鈗”矣,而未得其詳。考之《玉篇》,但有“銳”字與“鈒”、“鋋”等字,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是野王所據《尚書》作“執銳”也。
“瑁”〇十行本、毛本作“冒”,非。
“憑”〇段玉裁校本作“馮”。
“卞”〇段玉裁校本作“弁”。
咸豐補刊本四條變爲兩條:
“銳以稅反”〇毛居正曰,“銳,許氏《說文》音兌,廣韻徒外反,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其誤明矣。當從《說文》、《廣韻》音。”按,經文“銳”字若依《說文》則當作“鈗”,从金允聲,音允。今經既作“銳”,故《廣韻》於泰韻“兌”字鈕載之,《說文》初無此音,未知毛說何據。〇按,《尚書撰異》云:治《尚書》者,自蔡仲默以來,皆謂“銳”當依《說文》作“鈗”矣,而未得其詳。考之《玉篇》,但有“銳”字與“鈒”、“鋌”等字,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是野王所據《尚書》作“執銳”也。
“瑁”〇十行本、毛本作“冒”,非。
不難發現,咸豐補刊本在“銳以稅反”條增加了“毛居正曰”云云,這些文字在咸豐補刊本中剛好佔了兩行,因此補刊本刪去了“憑”、“卞”二條,從而使改動不會影響其他版片。又咸豐補刊本“鋋”字誤作“鋌”字,則沿襲自道光初刻本。
第四,兩本對於古本的態度有細微差別。我們先看下面的例子:
“古本”,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觀序以爲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間參俗體,多不足信。
咸豐補刊本末有:“是否真本殆不可知,其字句異同,可以正今本之誤者固多,亦時有舛譌,蓋展轉書寫,已失其真矣。”
卷三108條:“敬敷五教”,“敬”上,古本有“而”字。按,《列女傳》引此句亦有“而”字。又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令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蓋古本即據以增入。
此條末句“蓋古本據以增入”,咸豐補刊本作“是知古本不妄矣”。
卷十八062條:“惟孝友于兄弟”,“孝”下,古本有“于孝”二字。山井鼎曰……〇按,今皇疏本亦作“孝于惟孝”,山井鼎於《論語考文》亦衹言古本“乎”作“于”,不言作“惟孝于孝”,與此不合。……更無是理,古本之謬往往類此。
此條 “更無是理,古本之謬”,咸豐補刊本作“更無理矣,古本數經傳寫,漸失本真”。由以上三例可見,文選樓諸本對於古本不無批評,而咸豐補刊本之文字則與之不同。於古本是而諸本非者,則予以說明,於古本非者則以爲是傳寫之失。由此可見二本對於古本態度之差異。
以上四點差異,前兩點較主要,涉及條目較多。雖然咸豐補刊本有些校記詳於文選樓本,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並不是說咸豐補刊本優於文選樓本。咸豐補刊本有如下一些問題,如誤字較多,多是形近而誤。如卷一004條“怗”誤作“怙”,卷二131條“扞”誤作“扜”,“扜”又誤作“扞”,卷七068條“牗”誤作“牖”。前所舉卷二135條亦是咸豐補刊本不合浦鏜原意。由此可知,二本互有短長,可以互補。
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咸豐補刊本刊刻之依據主要仍是道光初刻本。但是其校改依據呢?咸豐補刊本之刻在道光初刻本及文選樓本之後,那麼咸豐補刊本的校改是否是針對道光初刻本或文選樓本的呢?
從有些條目來看,可以這樣說。例如《尚書釋文校勘記》卷下094條:
“不啻,徐本作翅音同”〇翅,葉本作“商”。按,“商”蓋“啇”之誤。
文選樓諸本及道光初刻本文字如此,咸豐補刊本此條作:
“不啻,徐本作翅音同”〇翅,葉本作“商”。按,“商”蓋“啇”之誤。〇按,葉本誤也,云[啇](商)之誤更非。
今按,咸豐補刊本云“云啇之誤更非”,顯然是針對原來“‘商’蓋‘啇’之誤”而言的。如果僅從此條來看,咸豐補刊本是在道光初刻本基礎上改動的。但是,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簡單。我們先看《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六028條(如下圖):
此條校記部分“法”字之左原有“作”字,文選樓諸本、道光初刻本皆如此。但“作”字似與文義無涉,且“非”字下文選樓本仍有空白。但咸豐補刊本此條與文選樓本不同:
“言我周亦法殷家”,法,古本、宋本據作“涉”。山井鼎曰,考疏意,作“涉”者非。
根據文選樓本的行款,“作涉者非”四字需要轉行,其中“作”字正合在“法”字之左。那麼我們可以推測,文選樓本此條原與咸豐補刊本一致,但後來作了修改,剜去“山井鼎曰考疏意作涉者非”十一字,又在“涉”刻“非”字。在剜改時,轉行處的“作”字剜改未盡,所以就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類似的情況還有《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八003、147兩條。這可以說明,我們所看到的文選樓本是經過剜改的本子。
如果我們的推測成立,那麼咸豐補刊本校改之依據,恐怕是要早於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有嘉慶十三年段玉裁序的本子。那麼咸豐補刊本根據的是否是我們在上文所提及的嘉慶十一年初印呢?因材料有限,姑且存疑。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集群經校勘之大成,梳理其版本對於研究《校勘記》本身以及清代校勘學史都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對於整理《校勘記》亦不無價值,因此我們略作考述,敬祈指正爲盼。
附識:本文寫作得到本所同事張文学兄指正並提供相關資料,書於此以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