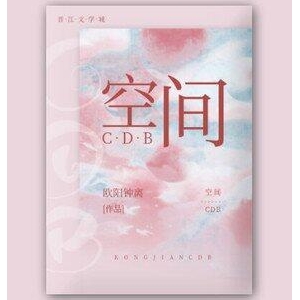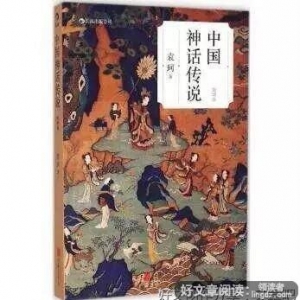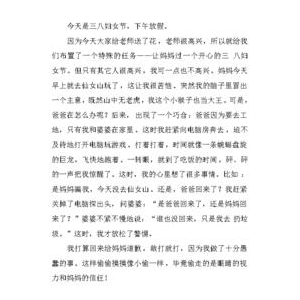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致父亲》是一本由弗兰茨·卡夫卡著作,华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5.00,页数:1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致父亲》读后感(一):《致父亲》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致父亲》前半部读起来很顺畅 后半部分和《他》《布雷奇亚关飞记》很难读。 《魏玛之行》有几个句子不错。 摘录: 话语印象深刻: 我还记得你的一些话,他们显然在我大脑中刻下了沟纹,如:“我七岁时就不得不推着小车走村串户了。”“有山芋吃我们就高兴死了。”换一种环境,这些叙述满可以成为出色的教育手段……P24 成年人面对咒骂的心理能力: 成年人有着多半很出色的神经,他们可以毫不费力的把咒骂从身上抖掉。P28 关于母亲在父子之间的斗争中无辜受伤: 我们双方都毫无顾忌地对她进行轰击…这是一种方向偏转,人们心中并不怀恶意,只想着同对方的斗争,但却在母亲的头上大吼狂叫。P31 丢掉苦恼: 两个人都不愉快。倘若能将苦恼从窗口泼出去多好。P103 某人以前常来,现在则不: 大公爵已有几年没到这里来了。他是个猎人而这里无猎可狩。P106
《致父亲》读后感(二):难念的经,难解的题
如何当爹果然是一道永恒的难题。
尽管与弗兰茨卡夫卡之间横亘着时代和国别的巨大差异,但书中作者以给父亲写信的形式所表现出的家庭环境却依然让我感同身受;甚至在内心深处很多方面,我也与卡夫卡有着惊人的(瞎估计一个数,大概在75%以上)相似度。我也自然而然地因此联系对照起六年前我和我爸之间短暂(却漫长得超出周围所有人的理解——将近三年的形同陌路)的决裂,以及今年清明节回家当晚(也就是一周前)彼此一触即发的、言辞异常激烈的相互辱骂。
我和卡夫卡是何其的相似。无论是身体上的孱弱、性格上的怯懦、敏感却常年受到打压的强烈自尊、灾难般的口头表达能力、人际关系问题上习惯性的有意逃避,还是对整个外界环境的漠不关心、对职业及职业选择的态度,以及父子关系里看似坚定的自我立场中挥散不去的道德负疚感......以上种种,都让我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不断强化出一种顾影自怜般的感觉。
而相比于我和卡夫卡的相似,或许我们的父亲之间更称得上是如出一辙(这样的父子关系模式简直就像科学实验般具有惊人的可追溯性和可重复性——有类似经历的父亲,因而形成了类似的性格,也造就了类似的父子关系)。两位父亲同样是从极端恶劣的低起点环境中崛起,同样携带着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样对周围人充满了不屑和不信任,有着同样待人处事的应对模式——甚至连自我吹嘘(通过奚落嘲讽他人得以实现)和自我开脱(独裁却对自己的专制毫不自知也缺乏自省所导致的无辜)时所用的语言和口气,都别无二致。
但可能我做的更好的部分,是我在一周前的那场大逆不道的骂战之后,(或许是出于强烈的关系修复之责任感的驱动,或许也夹杂着一丝反客为主地对权威进行主导所带来的快感)轻易地聚集起了生平前所未见的天量勇气,主动采取了与我爸直接面谈的方式(这对我的口头语言组织能力也是一场莫大的挑战)进行了沟通,避免了信件因无法实时感知对方情绪而导致的单方面控诉局面可能造成的表达内容可接受度上的缺陷——当然这个选择可能也让我错失了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一篇慷慨激昂的檄文之良机。
通过这种当面的对话仪式,我先是争取到了似是而非的原谅,并在这个过程中,再次列举了我人生前半段所受到的来自家长的种种精神上的迫害(简言之即翻旧账),同时我也充分传达出了自己对明显有违传统中国三纲五常精神的父子关系“平等“状态之渴望——这是一种对固有的父子之间权力结构彻底颠覆的大胆尝试,尽管是以一种看似和平友好的、光荣革命式的方式进行,但终究还是遭遇到了不大不小的反弹和抵抗。从全程双眼紧闭、不时从鼻孔里喷出充满讥诮意味之气息的我爸那里,我得到的仅有的、意思相对完整的那个反应,暗示了这位信息接收者内心充满了对这种沟通方式和关系诉求的强硬回绝——“你就当清明节这天来为父坟前自说自话吧”,他如是说。
但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至少通过勇敢的行动,为这段相爱相杀充满了各种复杂情绪(比如我爸在望子成龙的同时还无意识地提防着我在某些方面的青出于蓝可能导致的对他个人威严的微妙伤害)的父子关系,作出了几十年来未有之努力,也算是实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自我超越。
印象中有太多在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名人,都有着不太融洽的父子关系。或许严父的存在,是一个男人成长中最大的(却也是心怀最大善意的)敌人,是他迈向成熟之路必须要跨过去的槛。只不过每个人跨过去的方式,千差万别吧。
愿我们都能成为这场人生最重要的跨越运动中的刘翔,也愿世间所有关系紧张的父子,都能以某种最好的方式(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实现和解。
p.s.延伸来看,人和人的关系里,或许永远都存在着“我要的你没给而你给的我不要”的不知足感和“为谁辛苦为谁忙”的徒劳感之间的感受上的错位。
《致父亲》读后感(三):墓地里的寒鸦
卡夫卡的画
Franz·kafka,是与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齐名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英国诗人奥登曾这样评论kafka“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就像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作品不可忽视,他的悲剧就是现代人的悲剧。”为什么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卡夫卡的作品仍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他与我们的连接体现在哪里?卡夫卡,这位巨人神秘的外表下隐藏着怎样的灵魂?
先谈谈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与家庭背景吧。
社会环境
卡夫卡身处在一个奇异的时代下。文化冲突及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科技突破,对于世界的探索更进一步,与此同时也直接波及了教会的统治。上帝的存在从未如此受到重视。人们开始怀疑信仰的意义。
卡夫卡生活于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在笔记上写下:“布拉格是座温室,在这里,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意志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无的世界主义都在互相冲突。”
卡夫卡生长于一个微妙的环境里。作为一个捷克人,他从小接受德语教育。而身处波西米亚,他又是个犹太人。
家庭背景
卡夫卡的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母亲则是位家庭主妇。卡夫卡是家中的长子。
从小,卡夫卡的父亲就不赞同他进行文学创作。在卡夫卡看来,父亲是一个毫无温情可言的暴君,经常肆意的使唤和责备他的店员。即使是他自己的孩子,也每天都被他训斥。童年时的卡夫卡几乎是在被父亲责骂的阴影下长大的。因此卡夫卡极其畏惧自己的父亲。举个例子,成年后,卡夫卡本想学习文学,却被父亲勒令转修法律。父亲,是卡夫卡一生过不去的阴影。
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卡夫卡只得到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因为从小经历的家庭暴力,卡夫卡的情感被抑制,不被父亲尊重,且缺少安全感。因为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卡夫卡失去了归属感。他在日记里写下绝望的呐喊:“现在我在家中,身边是最亲近的人。但我坐在他们中间,就好像是个陌生人。”因此我们大概能理解,为什么卡夫卡的作品里充斥着窒息的绝望,压抑的孤独和恐慌。为什么“父亲”这个人物在他的作品里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正因为卡夫卡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或意识形态,他才能摆除局限和狭隘性,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卡夫卡。
一、《在流放地》
——卡夫卡式救赎
我认为《在流放地》这篇小说最能够体现卡夫卡的宗教观。这部作品故事情节极其简单:一位旅行家来到流放地,对流放地的残酷行刑提出质疑,并以行刑者的自决为结局。情节简单却离奇,行文流畅而晦涩。
一种普遍的理论:国家异化促使国家机器成为专制暴力统治的恐怖血腥工具是《在流放地》的思想主题。
但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又能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旅行家,军官,犯人,现任司令官以及存在于军官口中的“故去的司令官”都分别寓意着什么?流放地和机器都象征着什么?
流放地上生活着军官和犯人(被流放者)。犯人是有罪的人;军官则是司法者,是正义的代言人。然而犯人的罪过是什么呢?从头到尾,作者都没有提及。
(有罪却无知,联想到圣经中的“原罪”。人是生而有罪的,需要通过信仰上帝在死后获得救赎。)
旅行家替犯人感到不公,因为犯人要接受酷刑,也因为犯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是什么。然而犯人却没有替自己申辩,临死还沉溺于那碗难得的白粥中。
(犯人,指不仅受信仰所困,也受现实所困的人们。一些人盲信上帝,另一些人没有信仰却过着娱乐至死的生活。从众,盲目。)
(旅行家,指那些有着自省能力的人。意识到了宗教的局限性并选择放弃。却没有找到宗教的替代品,只能在各个学说流派间徘徊,成为永远的旅行家。)
旅行家向军官提出了质疑,而军官为了证明行刑机器的圣洁性选择自裁,死在了机器下。甚至“没有什么所谓罪恶得到赦免的痕迹。别人从机器中得到的,军官可没得到。”
(军官是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他热爱自己的信仰,然而最终却没有得到救赎。军官是什么?是个圣洁的替罪羊。他狂热的追随老司令官,甚至不惜通过自己的死亡来维持人们对于信仰的坚持。)
最终,现司令官取消了这项行刑,旅行家离开了这片流放地。而老司令官依然于地下长眠。
(现司令官,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老司令官,古老的信仰和宗教文化。随着新制度的崛起,宗教信仰逐渐被抛弃和质疑。然而流放地依然存在,犯人们即使不再被上帝统治,也会在现司令官的统治下生活。而旅行家虽然自己意识到了这个历史的循环,却无法帮助更多的人逃出这片流放地。)
也许这就是卡夫卡想表达的:现代人脱离了信仰的束缚,却又被各种其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人们要不浑浑噩噩,庸庸度日。要不迷茫漂泊,毫无归属。犯人或旅行家,我们失去了第三种出路。
二、《审判》
——在法的门前
在法的门前站着一名卫士。一天来了个乡下人,请求卫士放他进法的门里去。可是卫士回答说,他现在不能允许他这样做。乡下人考虑了一下又问:他等一等是否可以进去呢?
“有可能,”卫士回答,“但现在不成。”
由于法的大门始终都敞开着,这当儿卫士又退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弯着腰,往门里瞧。卫士发现了大笑道:“要是你很想进去,就不妨试试,把我的禁止当耳边风好了。不过得记住:我可是很厉害的。再说我还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卫士哩。从一座厅堂到另一座厅堂,每一道门前面都站着一个卫士,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就说第三座厅堂前的那位吧,连我都不敢正眼瞧他呐。”
乡下人没料到会碰见这么多困难;人家可是说法律之门人人都可以进,随时都可以进啊,他想。不过,当他现在仔细打量过那位穿皮大衣的卫士,看了看他那又大又尖的鼻子,又长又密又黑的鞑靼人似的胡须以后,他觉得还是等一等,到人家允许他进去时再进去好一些。卫士给他一只小矮凳,让他坐在大门旁边。他于是便坐在那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间他做过多次尝试,请求人家放他进去,搞得卫士也厌烦起来。时不时地,卫士也向他提出些简短的询问,问他的家乡和其他许多情况;不过,这些都是那类大人物提的不关痛痒的问题,临了卫士还是对他讲,他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为旅行到这儿来原本是准备了许多东西的,如今可全都花光了;为了讨好卫士,花再多也该啊。那位尽管什么都收了,却对他讲:“我收的目的,仅仅是使你别以为自己有什么礼数不周到。”
许多年来,乡下人差不多一直不停地在观察着这个卫士。他把其他卫士全给忘了;对于他来说,这第一个卫士似乎就是进入法律殿堂的惟一障碍。他诅咒自己机会碰得不巧,头一些年还骂得大声大气,毫无顾忌,到后来人老了,就只能再独自嘟嘟囔囔几句。他甚至变得孩子气起来;在对卫士的多年观察中,他发现这位老兄的大衣毛领里藏着跳蚤,于是也请跳蚤帮助他使那位卫士改变主意。终于,他老眼昏花了;但自己却闹不清楚究竟是周围真的变黑了呢,或者仅仅是眼睛在欺骗他。不过,这当儿在黑暗中,他却清清楚楚看见一道亮光,一道从法律之门中迸射出来的不灭的亮光。此刻他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在这整个过程中的经验一下子全涌进脑海,凝聚成了一个迄今他还不曾向卫士提过的问题。他向卫士招了招手;他的身体正在慢慢地僵硬,再也站不起来了。卫士不得不向他俯下身子,他俩的高矮差距已变得对他大大不利。
“事已至此,你还想知道什么?”卫士问。“你这个人真不知足。”
“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法律么,”乡下人说,“可怎么在这许多年间,除去我以外就没见有任何人来要求进去呢?”
卫士看出乡下人已死到临头,为了让他那听力渐渐消失的耳朵能听清楚,便冲他大声吼道:“这道门任何别的人都不得进入;因为它是专为你设下的。现在我可得去把它关起来了。
这是《审判》里最著名的一段。卡夫卡大学主修的就是法律。他将许多自己关于法律的见解容纳到了他的文学作品里。
乡下人被卫士阻挡在法的门前,临死也没进去。尽管在追求“法”的路上孜孜不倦,却对“法”没有深刻的认识。“法”是平等与公正,然而却被统治阶级扭曲成为自己服务的工具。
卡夫卡生活在正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捷克。在这里,新旧朝代更替,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剥削下层民众,新生的资产阶级压迫中产阶级。这个时代是没有公平与正义的。乡下人就是被统治者,一生追求平等幸福。然而却被卫士——资产阶级阻挡在了门外。他们阻挠无产阶级去追求平等和公正。法就在那里,平等公正就在那里,我们应怎么做呢?卡夫卡笔下乡下人应对的态度,其实是大多数人的态度:苦苦等待,听天由命。因此乡下人苦等一生也没有进入法的大门。在卡夫卡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也不见公平和正义。
对于社会和时代而言,卡夫卡是位记录者,却不是改变者。受个人经历影响,卡夫卡面对不公的社会现象的态度是消极的。
但在文学创作的层面上,这些作品的价值是巨大的。他的作品糅杂里存在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三、“耗子民族”的歌手
———卡夫卡的犹太情结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卡夫卡的最后一篇作品。但凡绝笔之作,都带有点作者自传的意思。这篇也是如此。
卡夫卡很少在自己的小说、书信、日记里谈论到“犹太”一词。他甚至极力否定自己与犹太民族的相似性。但他的作品却又时时刻刻围绕着这个民族进行思索与解惑。
文章标题《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什么是耗子民族?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漂泊不定,无依无靠,被西方基督徒排斥。“人人得而诛之”是犹太人那时的普遍处境。这样一个民族更需要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来抵御外侮。
约瑟芬却是一个独立于群体的个体。她热爱歌唱,却不知这种歌唱更加显示出自己的特立独行,使得自我与群体的距离越来越远。卡夫卡也是如此。他热爱写作,更想通过这种艺术来拯救犹太民族的民族局限性。然而犹太人,这个“孩子没有童年”的民族,一向认为物质追求是高于精神追求的。因此约瑟芬的艺术追求不被其他耗子认可,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也不被自己的父亲支持。
卡夫卡就是这个“耗子民族”的歌者。他看到了犹太民族的不幸未来,却无能为力。“我们民族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条路通向哪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而知道的人却无法让正在行进的人们停止或改变方向。他大喊大叫,其他人却对此无动于衷。
文章的结尾:
我们可能根本不会有多大损失,而约瑟芬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她认为,只有出类拔萃者才会承受烦恼——,跻身于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中,将会快乐地消失,由于我们不撰写历史,她很快就会像她的所有兄弟一样,在更高的解脱中被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