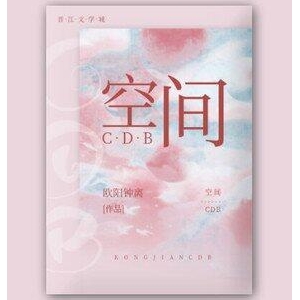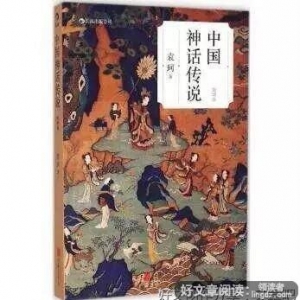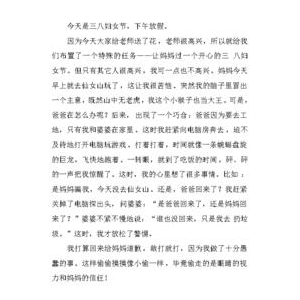滂沱大雨还在下,我的鞋袜早已湿透,凛冽的风拼命地吹过来,寒和冷一股脑袭来。
火车站外,因着大雨,阻隔了不少行人的脚步。的士司机在低矮的屋檐下不厌其烦地招揽客人。南昌,我又来了。
我又来了,南昌,在这一个早春大雨入注的清晨。火车站已变得面目全非,我踩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水洼里,大雨“噼里啪啦”的打在伞面,找不到要去的方向。
这情景就犹如当年刚从某校毕业,第一次到南昌的我,茫然失措,不知前方的路在何处。那时,我虽然年纪最小,但因为在学校表现优异,我是矿上十个女生的领队。毕业后,我们竟然没有如愿分到向往的国企,而是分回矿里,这对于一心想要跳出矿山的我无疑是一种打击。
矿上已经呈半停产状态,许多人都外出打工。我和另外九个女孩开了个小会,去冶金厅找领导把情况说明,要求重新分配。当然,我是有私心的,我可不想辛苦学习读的学校,换来一个一辈子打工的下场。
记得那也是一个下雨天,天像破了一个口子,总有源源不断的雨水流出来。我们七拐八拐,不知道问了多少人,走了多少路,终于来到冶金厅。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年人,他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
他热情的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然后询问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可能是年少气盛,加之那时我是领队,我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把读书的初衷,学习的努力以及对分回矿里的窘迫全都说了一边。窗外继续下着“哗啦啦”的大雨,他一边听一边拿支笔在小本本里记着什么。
陪我来的肖一声不吭,平时话多得不得了的她,在外面就像一个哑巴。我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完了,看了她一眼,我希望自己没有说全的地方她能帮我补充一二,但她佯装不知,扭头看向窗外。
中年人叫我们回去等消息,说会把情况如实反应给领导,叫我们不要着急,事情总会解决的。
就这样我们千恩万谢的离开了冶金厅。
因为实习要一年半,分配工作的事迟迟没有眉目。闲不住的我和几个矿里的女孩一起去到广东打工。
还没去到三个月,母亲托人打来电话,说冶金厅打了电话给矿里,我们十个女孩全部分配到了国企,叫我快回去。
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就买了车票,踏上回家的列车。
矿里在南昌有个转运站,天色已晚,我和另一个女孩在转运站暂时栖息。
我记得那时是六月,当我们准备出门逛街时,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静静地看着雨中的南昌,有一点朦胧,有一点心酸。
那些低矮的建筑是老城区独有的标志,街灯、树木、还有偶尔路过撑一把伞的行人,都汇进这蒙蒙的夜色中。
我对南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这感情,或许是心想事成的感慨,也或许是困顿路上的感悟。
但,南昌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太多了。那时年少天真的我,怎会知晓,若干年以后,兄长曾与这座城有过对话,后来长眠于这座城的红土地下。
大表哥小表哥他们把家从矿里搬到了南昌,可自小我和他们生疏早已没有了联系。
南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记忆的一个载体,是我前进路上的感情寄托,也是我心碎不可弥补的永远的伤痛地…
大雨一直下,一直下,张宇的那首《雨一直下》,一直萦绕在耳畔。
南昌,南昌,我又来了。再见你时,你已面目全非,而我也心性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