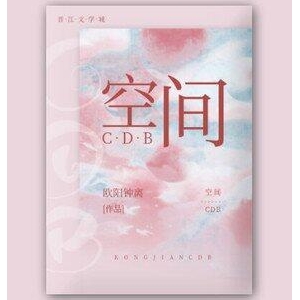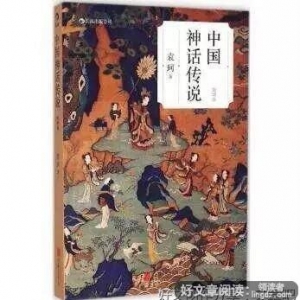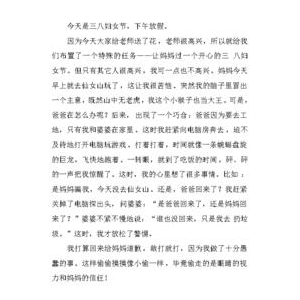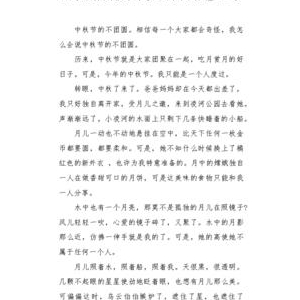《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是一本由[法]勒内·基拉尔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读后感(一):我该如何称呼浪漫?
本书的开始不是作者论述三角欲望结构如何建立并被小说天才反映至文本的前三章,而是作者写司汤达笔下的贵族们的那一章,神权和王权双双失落之后,人们就像自己那被赶出伊甸园的祖先,天真的童年幸福结束了,剩下的是向身边的每个人摹仿那不存在的、虚幻的永恒而带来的虚荣和痛苦。欲望的本质是摹仿欲望,就是对他人的羡慕,嫉妒和无力的仇恨,司汤达叫它虚荣因为把对不朽和上帝的追求投射到人身上是不可能的,而人又与生俱来的不满足。在现代已经深入人心的人人平等的概念上,缺少真正的大他者,上帝。作者不是在否定和嘲讽浪漫主义,而是希望读者能够拨开建立在人本中心的、傲慢的浪漫云雾之后,和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一起在作品的最后放下企图在人身上寻找神性的虚妄,在爱面前面前体察到谦恭,并且坦然于自己的谦恭。最后一章节的结论实在太打动我了,由皈依和治愈联系起来的那些伟大的小说结尾啊,忍不住又流着眼泪重读红与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局:一切汇聚于此又在这里结束,放弃欲望认识自我的可怕的一瞥也是新生的一瞥,瞥见所有伟大的文学巨匠都目睹过的愿景:那是包法利夫人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印上的有生以来最深沉的爱之吻,是于连在黑牢里和德雷纳尔夫人一起度过的最后的甜美时光,是查尔斯莱德多年后在brideshead庄园小教堂点起的蜡烛光,是拉斯科尼科夫跪倒在索菲亚面前亲吻她的双膝时流下的眼泪,是卡嘉最后握着米嘉的手痉挛般一遍遍说的“你要永远爱我”,是阿辽沙在小伊柳沙的葬礼上发出的对善良和新生的永志不忘的呼求。陀氏以他的天才给人类的摹仿欲望的荒谬与悲哀画下了句号,这确实是条漫长的路途,但也是迈向复活的唯一路途。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读后感(二):从铜脸盆到曼布里诺的头盔:欲望与真实的距离
勒内 · 基拉尔(René Girard,1923年12月25日-2015年11月4日),1950年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取得历史学位博士,毕业后留校教授文学。《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是基拉尔在196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在书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欲望的模仿理论”(Mimetic Desire/ Rivalry)。2005年获得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的称号。他研究兴趣广泛,在文学批评、批判理论、人类学、神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均有成就。(摘自维基百科)
黑格尔在逻辑与历史的思考中预见到了暴力时代终结后的和解,然而天才的小说家对我们说:“人类的互相理解,永远是同床异梦”。暴力确实无益,如今人们的欲望却是以“羡慕、嫉妒和软弱的仇恨”等等的幻象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真实的、自发的激情被愈发广泛的虚荣取代,后者正是自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竞争与障碍中汲取力量。在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差异愈小,这种平等(或者说是平均)愈是发展,愈是不可能带来应许的和谐,只会使竞争愈发激烈。这一种如今普遍存在的无意义的对立与斗争,与任何具体的分歧、实际的价值观都离得很远。欲望的客体萎缩了,并且被不断向我们逼近的介体消解――欲望的介体站在了最前面,成为竖在面前的唯一阻碍。
堂吉柯德透过铜脸盆看到了曼布里诺的头盔,是想要成为阿玛迪斯的欲望扭曲了客体在主体眼中的形象。这是一个结构完好的欲望三角形,介体阿玛迪斯高高的悬挂在堂吉柯德与他种种的欲望客体中间。通过崇敬、模仿和成为阿玛迪斯,他走向不存在的欲望的幻象。
"欲望模仿理论" Mimetic Rivalry
堂吉柯德的故事有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的欲望是否真实。不真实的欲望在这里被指向激情的一极——虚荣。作者指出,在某种条件下,这种虚荣可以得到迅速的繁殖和发展,也就是人人皆平庸,人人互相为敌,竞争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只是挑拨了人们心中的攀比和嫉恨,更使内心的自我与他者的外在世界之间竖起一面看不见的墙壁。傲慢的性格只会使人更加孤立,看似自由不受拘束的意志实际上既不坚强,也随时准备为了屈从内心的奴性而牺牲任何的自由。
如今人们各自为营。我们乐于从堂吉柯德的铜脸盆中看到欲望的变形,也可以从《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孤独的幻觉中辨识出现代人的痛苦――“我是一个,至于他们,他们是全体。”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很好地回应了斯丹达尔的提问:现代社会的人为什么不幸福?斯丹达尔说,我们不幸福,原因是我们虚荣。现在我们也应该看到了这一点。
从塞万提斯、福楼拜、斯丹达尔,到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天才的作家从不同的时代,就好像站在高低不同的台阶上,不约而同地观察到了现代世界“欲望”结构的不同的侧面,然而他们不总是能够觉察到自己的观察与前人的观察的联系。基拉尔向我们指出了欲望发展的历史。在天才的小说中,自发欲望的幻象得以重现,“自我”与“他者”既是对立的,又可以在反躬自省中得到和解。
假如我们致力于培养强韧的主观意志,在真实的情感至关重要的时刻不吝啬秘密的告白,是不是可以战胜现代人虚荣的热病,――人们还能够找回真实的激情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几乎没有伟大的精神可以抵抗大众文化的消费,民族和历史的矿藏也要面临枯竭,于是我们被输入更轻快、更大量生产,也更经济的新的流行文化。古老的美德被深深地掩埋,追随者们亦步亦趋地走进阴影里,却没再回到日光下面来。
英雄是有的,但是他们的纪念碑建得太匆忙,很快又被荒蛮的野草占领了。反叛的精神是人类的基因,但是如今又只是闪烁着零星的光芒——把我一个人留在了这里!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读后感(三):小说的真实——勒内•基拉尔的“三角欲望”
初读勒内•基拉尔在序言和导言式的第一章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包含主体、客体、介体的“三角欲望”理论,有点拉康欲望理论的影子,拉康认为我们的欲望是对他者欲望的欲望,这与作者说的“摹仿欲望”异曲同工,看似我们自发的欲望,其实是他者欲望被主体内化为自身所具。而此处的他者即所谓介体,主体的欲望并非直接指向客体,而是借助介体来选择客体。换言之,主体对客体的欲望其实是摹仿介体对客体的欲望。可以说,勒内•基拉尔的三角欲望理论与拉康的欲望观有共同也相互补充,比如主体与介体的摹仿竞争与拉康所说的主体为维护自身同一性对他者产生“侵凌性”(主体与异在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两种观点可以参照对比。
对于介体作者划分出外中介与内中介,划分的依据则是介体与主体的距离,介体与主体距离较远则形成外中介,当介体与主体不断接近则形成内中介。外中介对应着垂直超验(指上帝的超验性),内中介对应的则是偏斜超验(指介体的超验性),由于主体与外中介(如上帝)之间距离较远,即此岸之于彼岸的距离,所以主体摹仿的欲望形成的是一种对神的虔诚信仰。而主体与之距离较近的内中介,主体在摹仿介体欲望的同时也形成了与介体的竞争关系,即摹仿竞争,这种竞争带来了主体对介体的仇恨。但从根本上而言这种仇恨源自主体对介体的羡慕和崇敬。小说中,作者认为堂吉诃德、爱玛•包法利的欲望介体属于外中介。而内中介所带来的摹仿竞争则带来主体的羡慕嫉妒恨,典型的则是斯丹达尔小说中虚荣人、普鲁斯特小说中的攀附者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地下人。从虚荣人到攀附者,再到地下人,主体与介体之间的距离不断接近。斯丹达尔的虚荣人追求的并非欲望客体,而是出于虚荣才与介体进行竞争;普鲁斯特的攀附者缘自主体与介体的进一步接近,如果斯丹达尔的虚荣人的虚荣还出自对名利、地位、金钱等的追逐,攀附者则完全攀附与自己平等者甚至不如自己者,他/她完全被一种受虐狂的激情所支配,之所以攀附对方只是因为对方设置了重重阻碍。虚荣人对客体痴迷是因为那是介体的欲望对象,攀附者所追求的神性对象则仅仅是因为介体故弄玄虚、故布迷阵的阻拒,而且荒诞的是这种阻拒仅仅是因为麻木愚昧加机械迟钝;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他对身边蔑视、侮辱自己的介体又爱又恨,他认为仅仅自己一个人独自不幸,因此说:“我是一个,至于他们,他们是全体”,他人受到上帝的青睐、护佑,因此他既渴望投入他人中去,又嫉妒憎恨他人,同时还离不开他人,多少显得自轻自贱。从斯丹达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主体与介体不断缩小的过程,偏斜超验也早已取代垂直超验。
垂直超验的丧失意味着“上帝之死”后虚无主义,人甚至将原本垂直超验的上帝变为偏斜超验的竞争介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正是表现了人在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之后的迷茫空虚,《群魔》中基里洛夫正是企图通过一种自主性的自杀来取代上帝的位置,因为这能证明人可以为自己作主,然而上帝是无限的,自杀似乎具有自主性却始终是有限的,同时人只能通过自杀来宣示自主性本身就是一种彻底的无能。基里洛夫的思想无疑与尼采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即上帝之死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崩溃,人必然面临着虚无,在尼采看来,虚无并非坏事,正是在虚无之上人才能建立自身,建立一种主人的道德,肯定生命,热爱现世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尼采的超人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然而,勒内•基拉尔通过对基里洛夫的批判,也将矛盾指向了尼采,认为尼采、里基洛夫依然是以基督为介体(而且是内中介),妄想摹仿基督,与基督竞争,不过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负。因此,尼采的主人道德(包括里基洛夫的自己作主)在勒内•基拉尔眼里依然是奴隶的。况且实质上而言,由于主体与介体距离的缩短,上帝即使不被当作摹仿竞争的对象,也会被新的介体所替代,群众愈发怀疑那个远在天边的上帝,而渴望一个近在眼前的偶像,在《群魔》中贵族斯塔夫罗金就被众人当作新的偶像所崇拜,从而成为人间的新上帝。然而即使如此,斯塔夫罗金不可能成为上帝,他毕竟还是人,他有他自身的罪恶,最终也走向了自杀。
从欲望的谱系来看,至少到叔本华将意志提到了世界本体的地位,在康德的基础上,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体不是物自体,因为人之所以还能知道物自体说明它依然在根据律建构的表象世界之中。欲望、欲求同本体意志不可分,是意志的表现,它激发生命的创造,同时也带来痛苦。尼采在很多地方受到叔本华的影响,但是不满意其对意志的否定和摆脱,在这一点上尼采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即肯定意志、歌颂意志,认为否定、摆脱意志不过是生命衰弱、怯懦的表现。因此,尼采是对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者。勒内•基拉尔与叔本华共同之处或许在于,肯定欲望的本体地位,因此他从小说本体论的层面来讨论欲望,并将优秀小说的使命定位为:揭示三角欲望,否定介体,恢复垂直体验,与生命的欲望和解。认为这是小说的真实。欲望既然都是对介体欲望的欲望,那么浪漫主义前期的自发欲望还是后期的超越欲望都不过是一种谎言,是欲望的苦修(即为了掩饰对介体的欲望而压抑、抑制这种欲望)。因此,欲望作为本体,是无法超越的,那岂不令人绝望?勒内•基拉尔并不作如是观,他并非一味否定欲望,而是否定给人带来无尽争斗、矛盾的偏斜超验欲望,即内中介带来的摹仿竞争。他将希望寄托在垂直超验带来的宗教信仰,希望人们认清偏斜超验欲望,回归垂直超验欲望。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读后感(四):我们为什么不幸福?
“现代人为什么不幸福?”斯丹达尔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虚荣”。
基拉尔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摹仿他人的欲望。”
保罗与弗兰切斯卡
(一)谎言与真实
弗兰切斯卡嫁给了保罗的哥哥,因此也就成了保罗的嫂子。新婚之初,弗兰切斯卡与保罗之间并无杂念。直到有一天,他们一起阅读法国罗曼司《湖上的兰斯洛》,在读到桂妮薇儿王后与第一骑士兰斯洛初次互吻之际,保罗和弗兰切斯卡也转向对方,摹仿书中的这对情侣。由于犯下通奸的罪孽,他们后来被保罗的哥哥杀死,魂灵在地狱的狂飙中飘荡。面对诗人但丁的问询,弗兰切斯卡的鬼魂坦言:《湖上的兰斯洛》在她和保罗之间起到的作用,如同加勒奥托在王后和第一骑士之间所起的作用——在罗曼司里,加勒奥托本是王后桂妮薇儿的管家,是他将兰斯洛带入菜园与王后幽会,也是他怂恿王后主动与兰斯洛接吻,因此,“加勒奥托”在后世成为“淫媒”的代名词。
现代世界铺陈各种浪漫主义的赞誉,认为弗兰切斯卡与保罗的欲望“自发”而“真实”,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将此视为“浪漫的谎言”。浪漫主义的赞美者没有意识到,这与但丁的初衷背道而驰,仔细考察原著不难发现,在那个关键性时刻,弗兰切斯卡和保罗对彼此的关注,比不过他们对正在阅读的罗曼司的关注。但丁既是谴责这对情侣的神学家,也是抵达“小说的真实”的诗人,那种“真实”就是对“加勒奥托”或曰“中介”的揭示,就是对“摹仿的欲望”这一普遍心理机制的发掘。
弗兰切斯卡与保罗的激情,与堂吉诃德的疯狂、包法利夫人的梦想、于连的虚荣、马赛尔的攀附一样,皆源自“摹仿的欲望”。“摹仿的欲望”可以理解为“由他人产生的欲望”“借来的欲望”“中介化欲望”。传统理解,人的欲望都是自生自发的,从“主体(人)”到“客体(具体欲望)”只需一根直线予以图解。基拉尔则认为,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在社会与文化的作用下,个人欲望不是一种主动、本能、自然的产物,欲望永远源自“介体”——也就是“他者”。人只欲求他人所欲求的东西,所谓“最聪明的广告不对我们说某某产品质量精良,而是告诉我们‘他者’都跃跃欲试。”在这个意义上,该用三角形来表现欲望关系,主体与客体居于底边两端,他者高高在上。
穷乡绅阿隆索·吉哈诺痴迷于游侠小说,尤其崇拜小说中十全十美的骑士阿马迪斯·德·高拉,为此化名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效仿阿马迪斯,开始了自己的骑士冒险。堂吉诃德有了阿马迪斯,便抛弃了自我,换言之,他欲望着阿马迪斯的欲望。在欲望三角形中,堂吉诃德是欲望主体,骑士理想是欲望客体,凌驾其上的阿马迪斯是“楷模”、“他者”或“介体”。两方关系成为三角关系,主体也就成为三角欲望的牺牲品。临终前的堂吉诃德终于清醒,他高呼:“我是阿马迪斯·德·高拉和他绵延不绝的子孙的死敌……今天靠着仁慈的上帝,我付出了代价,吸取了教训,我痛恨他们。”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要通过整整两卷的辛酸经历,方才意识到欲望三角形的荒唐。唯有否定介体,才能寻回自我,这是堂吉诃德重新成为“善人吉哈诺”的唯一道路。至于后世评论家送给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高帽,在基拉尔看来,不过是“浪漫的谎言”又一种。
基拉尔用“浪漫的(romantique)”一词,指那些反映了介体的存在却没有揭示介体的作品,比如《湖上兰斯洛》。又用“小说的(romanesque)”一词形容那些揭示了介体的作品,比如《神曲》。他的名作《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关注后者,虽然只探讨了塞万提斯、斯丹达尔、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五位大家的作品,却圆满完成了“小说现象学”的任务,由文学而及史学、再及哲学、又及心理学,深刻剖析了现代社会因“他者”占位而形成的“本体病”。
(二)暴力与皈依
勒内·基拉尔是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以当代“摹仿论(Mimetic Theory)”而闻名于世。1923年,他出生于法国古城阿维尼翁,父亲是档案管理员,受其影响,他致力于研究家乡15世纪后半期的私人生活史,以此获得中世纪法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他在巴黎,目睹纳粹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孕育了反战、反对暴力的思想。战后他远渡重洋,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虽然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文学训练,基拉尔却直觉地发现了斯丹达尔、福楼拜、普鲁斯特不断重复的同一主题:摹仿的欲望。后来他去霍普金斯大学执教,系统阅读了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希腊戏剧和神话,在所有这些著作中,那个致命三角形依然清晰可辨。1961年,根据授课笔记完成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出版,基拉尔一举成名。此后,他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陆续出版《暴力和神圣》(1972)、《论世界初始以来被隐蔽的事物》(1978)和《替罪羊》(1982)等近三十部著作,成就斐然,2005年入选法兰西学士院。
基拉尔的学术生涯约略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欲望结构研究、社会暴力研究、基督教研究,看似零散,实则一以贯之。在他看来,人的自由只有两种模式,神的模式和人的模式,前者是宗教的模式,后者则是“他者”的模式。当现代社会宣布“上帝死了”,“他者”便接替了上帝的位置、接受主体的崇拜。更致命的是,“人人互为上帝”,因此促成“摹仿竞争”。竞争固然是可观的物质利益的源泉,却也是更为可观的精神痛苦的源泉。世界越是变得民主,个人自由越是扩散,竞争也就越来越多,个人也就越是感到不适。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的:“……他们摧毁了束缚人的少数人特权,却碰到了全体人的竞争。……平等产生的欲望与平等所能提供的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对立,使人们感到痛苦和疲惫。”
平等之发展,也就是欲望三角形中主体向介体的接近,并未带来和谐。在普遍的竞争、攀比、羡慕、嫉妒、仇恨中,无论是爱情、地位、财富、还是其它个人成就,都被毒化。人们对自己的境遇永远不满、对他人的欲望永远垂涎,每个人都活在他者的目光之下,一半人患了暴露癖,一半人患了窥视癖。那个“地狱般的三角”,解释了人与人之间持久的竞争,揭示了人际关系中永久的暴力,也描摹了人们内心世界的满目疮痍。基拉尔试图说明,社会暴力正是从此而来;更旨在呼吁,宗教拯救也正是由此开始。
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的结尾,他直接强调:“每一部伟大小说的结尾都是皈依,对此不可能有异议。”当人物否定了他的介体,于是谎言让位于真实、焦虑让位于回忆、不安让位于宁静、仇恨让位于爱情、屈辱让位于谦虚,由他者产生的欲望让位于由自我产生的欲望、偏斜超验让位于垂直超验,这就是皈依。不能不说,基拉尔的基督教神学家面目,是他在学术界颇受非议的地方。放下介体、走向上帝,这个“药方”分明是由“真实”的一边荡向“浪漫”的一边了,不得不查。
(三)“他者的暴政”与“他者的消失”
柏拉图提出过摹仿说,黑格尔论证过介体,拉康梳理过他者,尼采隐约看到“情感/怨恨”这一不断重复的循环,舍勒在《仇恨的人》中早就指出,人人都有相互比较的要求,“这种比较正是一切嫉妒和野心的根源。”那么,基拉尔的独到之处在哪里?
基拉尔首先是文本细读的大师,能够发前人之所未见。他留意到《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叙事者这样开头:“凡不是我自身的东西,土地、事物,在我看来都更宝贵,更重要,具有更真实的生命。”年轻的资产者马赛尔有两个艳羡对象,一个是大资产者的“斯万家那边”,一个是大贵族的“盖尔芒特家那边”。小马赛尔由保姆陪着去了斯万家,此行被定义为“朝圣”,这套房间先后被比喻为神殿、祭坛、教堂、大教堂、祈祷室,对于介体的狂热尽在其中。但是更令他心驰神往的,恰恰是他的财产、天赋、魅力都无济于事的地方——那个旧贵族的世界。谁不接待他,他就渴望拜访谁,于是“盖尔芒特家那边”压倒了“斯万家那边”。他不断神化盖尔芒特家的地位和魅力,并亦步亦趋地进行效仿。当他终于获得了盖尔芒特家的请柬,看到的是同其他沙龙一模一样的平庸,听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陈词滥调,这里的人政治上反动、艺术上倒退、文学上短见,圣日耳曼区的光环褪去,马赛尔大失所望。基拉尔犀利地指出:攀附者会匍匐在已经一文不值的贵族爵衔面前,匍匐在只有几十个老太太叫好的“社交场”面前。摹仿越是没有道理,就越显得人生荒诞。普鲁斯特关注的,不是客体可怜的真实性,甚至也不是变形的客体,而是客体变形的过程。他感兴趣的,是攀附者如何把圣日耳曼区当成人人梦想进入的神话王国,又如何在漫长的叙述中使读者惊觉这种个人欲望史的全部矛盾、纠结、自我欺骗。在这一意义上,小玛德莱娜点心是真正的圣餐,它具有圣物的一切品质:回忆化解了欲望中的所有对立因素,精神理解了介体的作用。
基拉尔还有意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复杂精致、富于解释力。他根据主体与介体间的距离,区分了外中介(external meditation)和内中介(internal meditation)。当主体与介体的距离过大,介体在主体眼中遥不可及时,是为外中介,比如阿马迪斯之于堂吉诃德,拿破仑之于于连。而当主体与介体的距离非常接近,甚至能够相互竞争,则为内中介,譬如马蒂尔德之于于连,老卡拉马佐夫之于长子德米特里。外中介的主人公景仰介体、步其后尘。内中介的主人公则怀有一种既崇敬又愤恨的混合感情,因为此时的介体是一个僭越者、一个竞争者、一个讨厌的第三者,因此带来的感受只能是羡慕、嫉妒、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所以是现代小说的最高峰,就因为他写出了内中介造成的激烈冲突,在他笔下,不再有无嫉妒的爱情、无嫉羡的友谊、无厌恶的向往。介体扮演着模式与障碍的双重角色,主人公们也趋于分裂,怀着崇敬仇恨,躺在泥淖里做梦,跪在鲜血里敬仰。不仅如此,基拉尔还提出了“双重中介(double mediation)”,即任何人在将他人视为介体的同时,自己可能也被他人视为介体,源自三角又派生三角,由此展开一张交错的欲望巨网,回噬着主体自身。
如果说基拉尔写出了“他者的暴政”,却没有预见到“他者的消失”。当代哲学家韩炳哲提出,他者的时代已经过去,那种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已经消失。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同质化的恐怖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个超级自恋的时代到来了。倘若基拉尔地下有知,他又该如何更新他的欲望结构图呢?
本文已发新京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