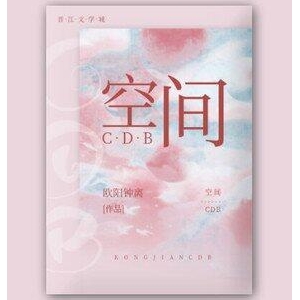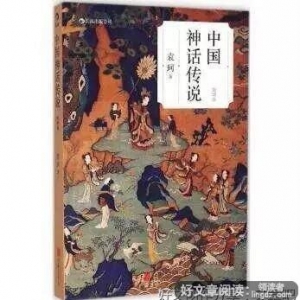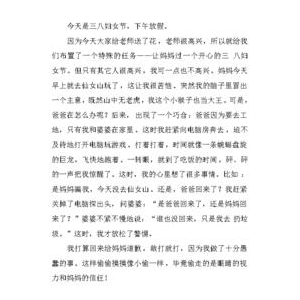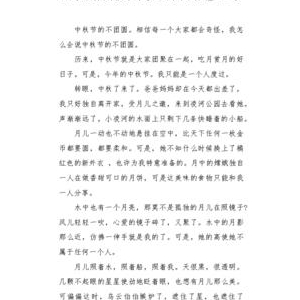《吠月》是一本由[日] 萩原朔太郎著作,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吠月》读后感(一):今天月色很冷
相较于带有特定意义的文章,诗歌似乎更看重氛围的营造。或者说个不恰当的比方,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武功招式清晰;但在古龙的小说里,武功招式化为无形,武功周遭的气息流动即烘托出招式本身。在文学创作领域,诗歌当属后者,因此读诗歌特别是现代诗歌时,往往先关注的不是它具体描述了什么,而是深吸一口气,妄图沉浸在诗歌所营造的氛围中。而一首诗歌打动人的,或许也就在只言片语所营造的氛围中。或许无法如同古诗般几下所有,但是那一两句诗歌能够让读者窥到作者内心的角落、作者所处世界的角落,便已足够打动人。《吠月》这个集子更是如此,它实际上是作者非常私人化情绪的体现,在缺少时代背景与时代共鸣的情形下,能够被读者接受甚至喜爱,大多是依赖于其词句中敞开的基于作者内心的一扇窗。
诗集中的作者是什么样的呢?《寂寞的人格》中,作者写道【自然总是处处令我受苦,而人情使我引物,我反而更细化在热闹的都市公园散步】。《害怕乡间》则正如其名直白表达自己对乡野的而延误。这一且在《走在路上,渴望置身人群》中得到了解答。在人群中被裹挟着流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这就是作者所渴盼的。诗人总被认为天性敏感,喜好独处和孤独。但是荻原朔太郎呈现的却并非如此。他同样喜好孤独,但是并不是空无一人的孤独。而是在人群环绕下的孤独。更与众不同的是,他喜好的孤独在主动和被动间犹疑。公园散步累了,觅得一方树荫享受孤独,是一种主动沉浸得孤独。但是相反被人群裹挟着向不知名的方向流动,因为对方向的无知也因为和知道方向的其他人不一致,因此孤独。这是一种被动的孤独。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在现代人造环境下的孤独。因此可以窥见,朔太郎更喜好于带有人工痕迹非天然环境下的生活。这种对于环境的选择、对于心态的把握,构成了其诗歌的一个基调。相较于歌咏山水,他更关注自我内心;相较于隐藏自己的情感,他更喜欢将炽烈的情感隐身在纷扰的现代人工背景下带过。
作为现代诗,朔太郎的诗歌中不乏对男女情感的描述,虽然本集子中专门有一部分收录了此类作品,但是或许因为本部分直接点题倒是显得这些诗歌直白多于含蓄,有损意境。集子对于这类情感描述的巅峰,我个人以为是收录在【腐烂的蛤蜊】部分的诗歌。这部分诗歌季总运用了触觉、嗅觉、感觉,但是视觉描述缺缺,最终依靠大量使用短小、细碎的意境搭配上基于嗅觉和触觉的描述,营造了不透明的昏暗环境。由此藉由看不见激发了感官,实际上写就了具有多重意义的作品,《春夜》当属其中佳作。虽然在本书收录的一篇自述性散文中,他提到自己的作品并非官能的。但是仔细品咂一些诗句,可以发现作者或许在创作时并无此意,但是成诗后却隐隐透出此类含义。这与作者上文所述,作者在暧昧背景下创作的细小涌动不无关系。
最后,诗集名为《吠月》,犬的形象自然不可少。数首诗均提到了犬。《陌生的狗》一诗中印象尤深。无论是“狗细长的尾巴拖在地上”还是“一边未遥远的、长长的悲哀而胆怯/一边对着寂寞天空长得月亮而高声吠叫”,这实际上并非狗的形象,更是作者自我刻画的内外两重自我。
《吠月》读后感(二):近代日本诗之父萩原朔太郎和他的诗
《吠月》。诗集。作者:近代日本诗之父萩原朔太郎。 “诗的目的不是讴歌真理和道德,是仅为了诗的表达。”这是波德莱尔的名言,也是萩原朔太郎特别认可的一句关于诗的原则。
作者把写作时的情绪当做密码放入诗中,我们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否与作者当初埋下的密码相同呢?其实我们真的不得而知,诗是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中最容易丢失的东西。 我在这诗集里看到了什么? 腐烂与生机,苍白与翠绿,音乐与绘画,男男与女女。 我们先来说一说腐烂与生机,在诗人的眼睛中,似乎特别容易看到那些腐烂的东西,或者说在诗人的鼻孔中,特别容易闻到那些腐烂的味道,有一些意象在传统的诗词中是绝对不会和腐烂纠缠在一起的,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它们就以那样的一种衰败的味道存在着。傲霜的菊花如此: “那菊花是腐烂的,那菊花滴下痛楚”(《腐烂的菊花》)肥美的蛤蜊如此:“一看那柔软变形的内脏似乎已经开始腐烂……嘶啦嘶啦嘶啦嘶啦吐着腐烂的气息”(《腐烂的蛤蜊》)人更是如此:“悲惨又饥饿的心,嗅着烂葱和烂肉的气味流泪”(《仰望绿树的树梢》)……
作者是一个名医的儿子,在他在诗坛上已经闯出名气之后,他带着自己的这本诗集回到家中,希望能以文字打动父亲,大概是诗集中的这些句子和里面随处可见的生与死触怒了父亲,父亲根本无法接受他的作品。作者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句子?我的理解是,作者在孤寂的时候感受到自身与世界的格格不入,这世间一切的美好在他那里都变成了腐烂的气息。 可惜他的父亲没有认真读他的诗集,在他的作品中,实际上也有很多昂扬向上的迹象,比如他著名的一首《竹》,里面就有竹子在坚硬的地面上生长,在地面上锐利地生长,迅猛地生长……感受是一种非常瞬间变化的东西,更何况是我们敏感的诗人,诗人抓住了自己感受的一瞬间,却因为这一瞬间得罪了自己古板的父亲。终他的一生,父亲没有成为理解他的读者,不过幸运的是他的诗慢慢的被大众所接受,他没有成为父亲成功的儿子,却成了引领一代诗坛的名家。把个体的感受写入诗作,这大概就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在他的《诗集》中,我还特别喜欢看他写爱情的作品。特别推荐一首:《那手,是点心》,我把全诗拍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情人的眼中,对方的手都是那样的可爱:扑簌簌像一条活动的鱼,引发情人的爱意与欲念。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化里,鱼都代表着女性和情欲,这一只温柔的小手,搅动着情人的心,撩拨着情人的魂,情人恨不得把它当点心吃掉,在他的想象中,这只手可以做一切美好的事情:弹琴、做针线、调情…… 读着这首诗,我想到了很多感人的爱情。读这首诗,我也仿佛被某种情绪“抱住渴求着爱的肩膀,在敏感的皮肤上,轻轻用指尖触摸,轻轻用指尖划过轻轻地紧紧地按压” 在我读过的写情人的诗作中,这般俏皮可爱又流露着满满爱意的诗作,我只想到了余光中的《小褐斑》。
《吠月》读后感(三):为了听见吠月之声,我们读诗
“在这春日来临的时候 非要凝视悲哀之物的我是多么不合时宜。”
如果从《吠月》里抽出一句诗概括读完的感受,没有比这句更能捕捉心绪的了。在这首名为《樱》的诗里,萩原朔太郎没有写樱花树的绚烂,也不知树下的人群在玩什么,他着眼于散落的花瓣,写道“可怜啊”。
另一首《海鸟》也很动人,悲伤被簌簌的雨打湿,寂寞的心脏开口发问,
“那只海鸟飞去了何方?
飞翔于命运的黑暗月夜
夜里啄食被海浪浸泡的腐肉并哭泣
啊 它飞向远方不再回来了。”
在朔太郎的笔下,不论是日常体验还是虚构的事物,都覆上了一层灰蓝色的阴郁感。稠密的冷寂如同生长在字词上的细小颗粒,又因为这些颗粒是可见的,让人隐隐约约地感到远处有微弱光亮。
长久的失望和暂时的平静总是交织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他写“生活只是没有丝毫含义的忧郁连续”,他也写“我喜欢看遥遥地、悲哀地飘过都市天空的煤烟和越过建筑物屋顶的、远处的小燕子飞翔的姿态”。
朔太郎的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生命不存在成长,诗不存在进步。他认为人生就像各个季节变化,既然不存在评定春夏秋冬的价值的标准,也就没有所谓的进步和成长。年老不是成长,也不是衰退,仅仅是“变化”,绝不存在今天的诗胜过昨天的诗的情况。
在不断流动的生命中,诗人这艘无锚之船总是游向更阴郁的角落,他循从美妙笛声的诱惑,变成不合时宜的逃逸者,逃离家乡、逃离人群、甚至想逃离自己的影子。书中那条对月长吠的狗,正是萩原朔太郎对自己的写照:
无论去哪里,
这条陌生的狗都跟在我身后,在污秽的地上爬,
这条在我背后拖曳着后腿的病狗,
是条不幸的狗的影子,
一边为遥远的、长长的悲哀而胆怯,
一边对着寂寞天空中的月亮高声吠叫。
他在序言中点明,狗是因为恐惧自己怪异的影子而吠叫,“在狗病苦的心中,月亮是个如苍白的幽灵般不吉的谜。”我想,狗通过月亮看见自己真实而怪异的影子,对着月亮吠叫如同对着自己看不见的灵魂在吠叫,这诅咒般无解的场景,也许就是人真正背负的宿命。
我也有过一段痴迷月亮的时光。那时候我还在上学,经常旷掉晚自习,跑到看月亮的最佳位置——靠操场的三楼走廊中央,悄悄地看一晚上月亮。月亮有时弯悬,有时饱满,无一例外的是它总是安静得让我产生一种与之对视的错觉。只要我看到月亮,月亮也就看到了我,那是无比明净的一刻,好像我出生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月亮心知肚明。
它是那么的温柔明净,可是全校的人都在教室里,没有一个人出来看月亮。我替月亮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落寞,同时也怜悯独自望向月亮的自己,比起的月亮拥有的永恒和不变,我的向往都显得多余。
那时,如果我知道很多年前也有一个逃课散步的不良少年,他上课时也望着窗外走神,也不断转学、退学,并且因为孤僻的性格和同学相处不愉快,我大概会开心得唱起来吧。尽管现在才读到他的诗,我也有一种喜悦的共鸣感。
《爱怜诗篇》中收录了朔太郎少年时代的作品,简朴而真挚,《乡土望景诗》虽然是诗人之后的创作,但也有纯情的咏叹风格,如《中学的校园》:
我的中学时光
是鲜艳热烈的烦恼
愤怒地扔掉书本
一个人躺在校园的草坪上
谁的中学时代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呢,写作之初的诗人依着纯粹的情感动笔,有一种朴素的语调。后来他经历离婚,带着两个孩子返乡时写的《归乡》,则是另一种乡愁:
过去连着寂寥的山谷
未来朝向绝望的河岸。
沙砾般的人生啊!
我已然勇气衰落
尽管朔太郎说,写诗日久,越来越对诗没有信心。但多少不合时宜的人,都是因为在另一本不合时宜里找到了联系,才感到人情之怜悯。诗为无法用语言说明的事物提供了容身之所,这是我们在诗中获得慰藉的理由。
当陌生的狗对着一切悲哀的源头,持之以恒地吠叫,无处发泄的焦躁和不安终于被钉在了纸上。但是从月亮的角度注视狗,那使它显现影子的光晕,也可能是庇护它兽性的唯一一块阴影,月亮也是有怜悯之心的吧。
《吠月》读后感(四):“我想到诗歌,就要为人情之怜悯而落泪”:《吠月》译序
文/小椿山
萩原朔太郎是日本著名诗人,在大正时代(1912—1926年),他以前所未有的口语自由诗,打破旧制开创了日本近代诗歌的新局面,被誉为“日本近代诗之父”。他的第一部诗集《吠月》起初虽只自费印刷了约500本,却一鸣惊人,成为书市上的热门作品,并且得到了文坛巨匠森鸥外的盛赞。他诗歌中充溢的寂寥感、阴郁和时而怪异的情绪,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萩原朔太郎诗集《吠月》原版
他的两首《竹》多次被选入日本教科书,具有相当的国民认知度。诗中描写的是在凛冬中生长的竹子,冻僵的青竹锐利地朝着天空生长。可是细读之后会发现,这两首诗并不像初读时那么积极向上。其中一首节选如下:
在阳光耀眼的寒冬,青青的竹子生长着,而朔太郎的视线却怪异地停留在竹根上——那些在坚硬的土地中蔓延开来的细弱如烟的根。在对比之下,它们显得更加赤裸而可悲,似乎这才是他真正想要描写的东西。
在《地下的病容》中,同样是描写竹根,竹根与地下的病人的脸、老鼠的巢同时登场——朔太郎的诗中常常出现“怪异”的东西,艳丽的墓园、腐烂菊花的气味、云雀料理、蛤蜊的舌头、尸体……他的感受力怪异而适切,在《春天的实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他笔下,春天是由亮晶晶的虫卵构成的,被虫卵挤得像皮球一样硬。想象这密密麻麻的无数虫卵,似乎是可怕的、恶心的,可其中也有着乱窜的、过剩的生命力;密集虫卵带来的不适感,更为那崩溃边缘的春光增添了癫狂的激情。春天就是这样的,只要我们经历过春天菜粉蝶乱飞、花粉滞重的时节,就知道,春天就是这样的。朔太郎的诗风为何如此沉郁而怪异,或许我们能从他的人生中找到线索。
萩原朔太郎《吠月》
1886年11月1日,朔太郎生于群马县的一个医生之家。父亲是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系的高才生,医术高明为人称道。而朔太郎是家中长子,理应在未来继承家业,自然被家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这样的期望带给朔太郎的更多是烦恼。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却仿佛要从父亲的阴影中逃开一般,彻底成了一个不良少年:他逃课去林中散步,上课时望着窗外走神,不参加考试,结果升学失败,即使后来得以入学,也不断转学、留级与退学。因为性格孤僻,他与同学的相处也并不愉快。
萩原朔太郎
他的高中老师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朔太郎的学业是没有未来的。”不过,也是在这学业一塌糊涂的少年时代,他开始接触并迷上了文学。他跟着表兄萩原荣次学习短歌,并醉心于与谢野晶子的短歌集《乱发》,他说:“接触到凤晶子(即与谢野晶子)的诗歌之后,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患了高烧的人。”
也是因为诗歌,他结识了一生挚友室生犀星。二人因同在诗人北原白秋主办的杂志《朱栾》上发表诗歌而相识。最初朔太郎对犀星的印象是“典型的乡村文青”,犀星对朔太郎的印象则是“矫情、倒胃口的人”——简直像漫画的开场。而后来两人一起办诗社、出诗集,成了文学与人生上的挚友。
在朔太郎的生活中,音乐的重要性恐怕不亚于诗歌。音乐与诗歌,也是他一生中两个相互缠绕的关键词。
朔太郎从小就显露出音乐天赋,总是一个人吹口琴、弹奏手风琴。中学毕业后,他曾经希望以音乐为志业,但是遭到家人反对。不过,他还是先后师从日本曼陀林演奏家比留间贤八、田中常彦学习曼陀林。1916年,他主办了“凤尾船西洋乐会”(后改名为“上毛曼陀林俱乐部”,也是群马交响乐团的前身)。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不少作曲和编曲,包括为室生犀星的诗歌谱曲,以及创作了曼陀林独奏曲《织布的女孩》——这是一首清新欢快的曲子。
他的诗歌富有音乐性,而且其中随处可见音乐的影子,关于音乐的诗句不计其数。譬如:
音乐也渗透到了他的诗歌观中。他喜欢以音乐作喻,将情绪比作“在春夜听到的横笛声”,说“一个人要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能依靠的唯有音乐和诗歌”,以“比起任何事物,诗首先必须是音乐”为信条。
诗歌或许称得上朔太郎青年时代的精神救济,让他可以短暂地从学业受挫、没有工作的挫败感中脱身,投入“超拔绝俗的思想、叛逆激烈的思维”。可是诗歌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说,无法解决一个文学青年和闭塞故乡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外人看来,他的故乡前桥绝非一个晦暗阴惨之地:天气总是晴朗干爽,利根川穿过城市流去,城镇安静而有古风。可是在朔太郎笔下,那里总是一个令人恐惧、枯寂晦暗的地方。
萩原朔太郎的故乡——前桥
1917年,《吠月》的出版给32岁的他带来了巨大成功,他一跃成为诗坛新星。可是当他把诗集拿给父亲,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时,父亲却在看到他描写的“病”与“死”时大怒,将诗集撕毁。他走在黑暗渐渐降临的田埂上,走在绝望的影子里——在乡里看来,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害群之马、名医没出息的儿子。
1925年,朔太郎终于移居东京。那时的东京作为一个摩登城市,西洋风格的建筑大量涌现,女孩们穿着洋装阔步街头,咖啡厅、舞厅点缀着都市生活,大型商场的屋顶上开设了动物园,老虎就在那里俯瞰着城市。在他向往的都会,人与人之间的漠然恰恰治愈了他——在这巨大、一视同仁的漠然之上,有着普遍的爱。
从高楼望下去,一个个人宛如渺小的虫子,可是走在人群中,陌生的熙熙攘攘也给人以安慰;黄昏时劳动者从城市的一部分被泵到城市的另一部分,满面疲惫的阴影;当地铁轰隆进站的时候,忽然感到莫名绝望。这种城市经验,让人感觉与我们当下在北京或上海的城市经验相通。城市给我们慰藉与孤独,它也捶打我们,只是与家乡捶打的方式不同。
1929年,朔太郎经历了离婚——来到东京后,他与前妻都一度沉迷参加舞会,据说后来前妻与一个青年舞伴私奔。他焚烧了大量的手稿与笔记,离婚加之父亲病重,他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前桥。记述这场返乡之旅的《归乡》写道:“啊 我又从城市中逃走了/去往不知何处的家乡。”次年7月父亲去世。10月朔太郎再次前往东京。
暮年朔太郎频繁地想到故乡,感到自己是一个失去了故乡的人,也感到故乡依然投在他身上的阴影。散文诗《乡间时钟》写道:
看过日本新浪潮导演寺山修司《死于田园》的读者,大概会立刻想起电影中青森那些破碎停滞的钟表吧。寺山修司这个渴望逃离故乡的人,是否也从朔太郎这里借取过灵感呢?顺带一提,朔太郎的长女萩原叶子也是作家,叶子的儿子(朔太郎的外孙)萩原朔美曾参加寺山修司的剧团“天井栈敷”。
寺山修司《死于田园》
1942年5月,朔太郎因急性肺炎逝世于东京世田谷的家中,时年55岁。据长女叶子说,暮年他总是在小酌后与自己一起演奏——父亲弹奏吉他,女儿演奏曼陀林。这堪称温馨的晚景。可是接近死亡的丧失感还是像风吹破屋窗。当朔太郎独自徘徊于酒馆间咀嚼着寂寥的时候,他说——
这悲哀而激情的祈求,像一股穿堂风,从他的青少年时代向结尾吹透。
在翻译中,有一处让我感到了额外的趣味。或许也是因为朔太郎的音乐素养,他的诗歌对声音十分敏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精彩的拟声。如《鸡》中对鸡叫的拟声:
从遥远乡野中传来的鸡叫声
咯咯哟——咯儿咯喔——咯儿咯喔——
(とをてくう とをるもう とをるもう)
在各种语言中,鸡叫都有其定式,比如中文中是“喔喔”“咯咯”,日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可是真实的动物叫声,到底是怎样的呢?在认真去想的时候,那些特别的音色与节奏就变得愈发难以捕捉。
朔太郎在这里并没有采用常见的拟声,而是打破定式,用音节着力还原了真实的鸡啼。而中文难以与假名直接对应,于是在翻译时,我努力回忆小时候听到的鸡啼,口中念念叨叨,掂量着字与节奏——想必,朔太郎在写下这句诗的时候也经历了这样的回忆,他脑内一定也曾一遍遍回放鸡啼声,口中也曾念念叨叨地模拟吧。
回忆着鸡啼,我也连带着记起了自己听鸡啼的场景:整夜失眠过后,房间中家具的轮廓渐渐从黑暗中浮出,鸡啼拖着长长的尾音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我盯着窗帘一点点亮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闹铃过一会儿会响,而我已经在为新的一天而提前感到疲惫。朔太郎这首诗也并不是一首快乐的诗,鸡啼令他痛苦焦躁,他想如扑灭火灾一般,让爱怜他的人来熄灭那不由分说地升起的太阳。看过太多用鸡啼喜洋洋地迎接新一天的叙述,那已经形成一种模式。我感激朔太郎这首不快乐的小诗。
萩原朔太郎《吠月》
萩原朔太郎《吠月》
朔太郎善于描写寂寞和焦躁,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从他的诗歌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像青年们很容易从太宰治的小说中找到自己的形象。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一种空间设置:自己在房间内,望着外界运动的景观,而自己一动不动。就像我们有时候感到自己是现实世界的局外人,不知为何无力向外踏出一步,于是在自己的沮丧中越沉越深。
“我想到诗歌,就要为人情之怜悯而落泪”,诗歌是他给自己和人类的安慰。希望这册中译本,可以让更多中国读者了解这位日本诗人和他的作品。
小椿山
2021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