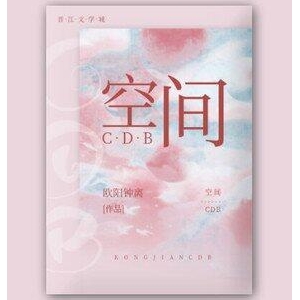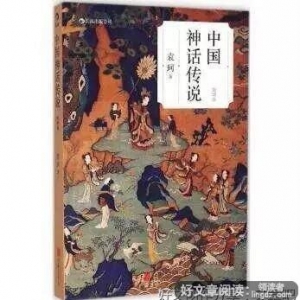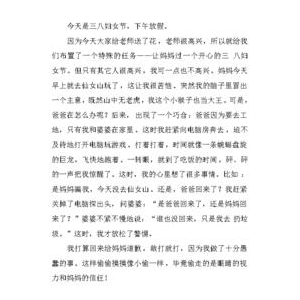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让安德烈和彼尔都爱上娜塔莎,这是意味深长的。娜塔莎,整个儿是生命,是活力,是“一座小火山”。对于悲观主义者安德烈来说,她是抗衡悲观的欢乐的生命。对于空想家彼尔来说,她是抗衡空想的实在生活。男人最容易患的病是悲观和空想。因而他最期待与女人的是欢乐而实在的生命。
男人喜欢上天入地,天上太玄虚,地下太阴郁,女人便把他拉回地面上来。女人使人生更实在,也更轻松了。
女人是人类的感官,具有感官的全部盲目性和原始性。只要她们不是自卑地一心要克服自己的“弱点”,她们就能成为抵抗这个世界理性化即贫乏化的力量。
我相信,有两样东西由于与自然一脉相通,因而可以避免染上时代的疾患,这就是艺术和女人。好的女人如同好的艺术一样属于永恒的自然,都是非时代的。
也许有人要反驳说,女人岂非比男人更喜欢赶时髦?但这是表面的,女人多半只在装饰上赶时髦,男人却容易全身心投入时代的潮流。
女人推进艺术,未必要靠亲自创作。世上有些艺术直觉极敏锐的奇女子,她们像星星一样闪烁在艺术大师的天空中。
女人聪明在于能欣赏男人的聪明。
男人是孤独的,在孤独中创造文化。女人是合群的,在合群中传播文化。
也许,男人是没救的。一个好女人并不自以为能够拯救男人,她只是用歌声,笑容和眼泪来安慰男人。她的爱鼓励男人自救,或者,坦然走现毁灭。
好女人能够刺激起男人的野心,最好的女人却还能抚平男人的野心。
女人作为整体是浑厚的,所以诗人把她们喻为土地。但个别的女人未必浑厚。
在事关儿子幸福的问题上,母亲往往比儿子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倘若普天下的儿子们都记住母亲真正的心愿,不是用野心和荣华,而是用爱心和平凡的家庭乐趣报答母爱,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
母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每一个正常成长的人来说,“母亲”这个词意味着孕育的耐心,抚养的艰辛,不求回报的爱心。然而,要深切体会母爱的分量,是需要有相当阅历的。在年少时,我们往往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母亲的关爱,因为来得容易也就视为当然。直到饱经了人间的风霜,或者自己也做了父母,母亲的慈爱形象在我们心中才变得具体、丰满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