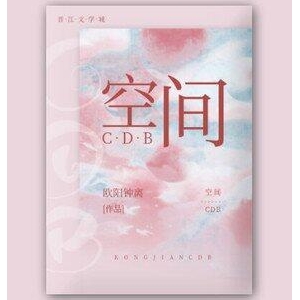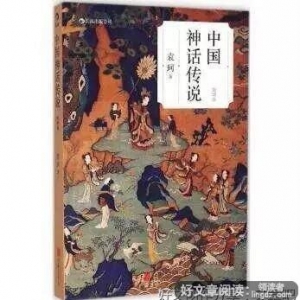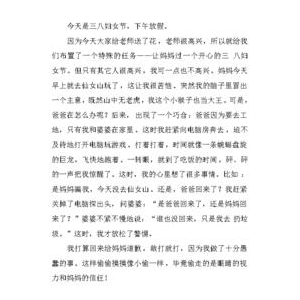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金瓶梅的艺术》是一本由孙述宇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瓶梅的艺术》读后感(一):评《金瓶梅的艺术》
很长一段时间都为向人解释金瓶梅的价值而深感头痛,就连知识渊博的爷爷在听到我读金瓶梅的时候都皱着眉说:“你怎么还看这?”但金瓶梅的确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古代文学之一,大学图书馆为数不多的金瓶梅馆藏经常被我霸占,读了不下两遍。金瓶梅读来因为真实而亲切,读中国古代文学总免不了黄粱一梦,但金瓶梅却比任何奢华的梦都更真实,以致待到繁华落尽,却很没有什么“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唏嘘。最初翻开这本书,本没有很大的期待,但随即发现它的独到,竟三言两语解决了困扰我多时的问题。另外对于围绕金瓶梅的重点问题例如书名的涵义、和红楼梦的对比等也都做了让我还算满意的回答。少有地希望对金瓶梅的解读就止步于此罢:继续深入就仿佛自讨苦吃。
《金瓶梅的艺术》读后感(二):。
金瓶梅首先是写实的,那个神秘的兰陵笑笑生不但不厌其烦地劝世,而且对任何角色都没有鄙薄或者批判的意思。他就把人性那点事情剖开了给你看,无非就是食色性,贪嗔痴,爱欲和离别。从前看金瓶梅一方面不好意思大大方方看,一方面自己确实也比较浅薄,注意力都在特定的篇幅上。后来自己的经历慢慢累积了,又觉得这本书太过凄凉,《红楼梦》至少有个水晶玻璃一般的大观园,有一些虽然易碎但也纯净的美好,《金瓶梅》的生活气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当你明白你在自己的生活中的真实位置,重读时再也没有年轻时那种鬼鬼祟祟的激动心情了,反而像兜头一盆冷水,冰冰凉。 这本书把很多之前自己看书并没有留意到的地方点出来了,醍醐灌顶。比如我知道凤姐有潘金莲的影子,但并没有看出来晴雯的影子也在这书里。 《金》与《红》我都很喜欢,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书,不用捧一个踩一个,真的不用。
《金瓶梅的艺术》读后感(三):坦白
这个人的语言特别有意思,他有学问,可并不故作高深,这本书有初见的惊喜,用直白的话表达出来。也不是直白,是坦白,坦然而明白,事看的明白,话说的明白,我看这本书,觉得说到我心里去了。 《金瓶梅》是最好的世俗书,自古到今,人性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们看书里的人,焉知书里的人是否也隔着历史的烟云在注视着我们,掂量着我们。 越来越觉得,有话就说,无话作罢,修辞什么的都是末节。真理从来不是什么俏皮话,真实就是真实本身。这个人他看透了这本书,就直接说出来,痛快又透彻,没看透的人才需要用云山雾罩的修辞来掩盖呢。 他屡次提到《金瓶梅》的作者有极其充沛的生命力与好奇心,说的真是对。这个生命力让他在见过和经历过之后,还能写出来,用悲悯之心。好奇心不用说,笨蛋玩不出那么多花样。 不同意他说西门庆死了以后作者意兴阑珊,八十回以后写的没有气力。我恰恰觉得,死亡之后的死亡,就是末路灰途,接连而来的战争,人不如刍狗,八十回以后的世界,是灰上又落了灰,不再会有清洁的那天。所以,八十回以后的味道,正好。
《金瓶梅的艺术》读后感(四):从李瓶儿的“爱”与“淫”来看《金瓶梅》的“情”——评《金瓶梅》,兼评本书
读了一多半,觉得本书有些过誉。但是作者的确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给了我启发。作者注意到,在宋惠莲这个人物形象上,书中的塑造体现出的矛盾性。一方面她跟西门庆私通,给丈夫戴绿帽,想要攀上枝头当“半主子”,另一方面却又在丈夫被西门庆诬陷流放之后拒绝再与西门庆发生任何关系,最终上吊自缢。作者从这个人物看到了兰陵笑笑生对于人的双面性的如实描写,对于可恨又可怜之人的同情。进而赞赏了兰陵笑笑生对于人性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尊重。
对于上面这个结论,我同意,但却不满意,于是我接着作者的思路开始自己的思考。
同样的矛盾性与复杂性除了体现在前文提到的宋惠莲身上,还体现在另一个更主要的人物身上,那就是李瓶儿。她们似乎是除了淫欲的满足与生活的依靠之外,对男性有精神希求的女性。惠莲对丈夫的感情体现在她得知丈夫被西门庆所害后失去了活着的意志,而李瓶儿更加明显,她和西门庆最后的生离死别是现代读者熟悉的情人离别场面。读到五六十回,我这个现代读者已经完全把她当成了一个爱儿子爱丈夫的普通女人,与她产生了深深的共情,在她死时特别心酸。
可是,回想起她们出场时,是妥妥的被作者定性为“淫妇”的。李瓶儿爱西门庆是因为她的前几任皆不能满足自己,读者在花虚子和蒋竹山那里明确地看到了李瓶儿“欲求不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她一点也不笨,一点也不贤良淑德,一点也不逆来顺受,她也会把汉子骂得狗血淋头,会釜底抽薪转移财产,留丈夫自生自灭,并且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歉疚。
这一段由色欲开始的出轨关系何时变为了爱情?作者没有说清楚。这一点不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西门庆的其他姬妾对他明显没有这种情,西门庆死了之后她们“食尽鸟投林”,因为种种原因各自散去,潘金莲更是一天都忍不了淫欲,在葬礼上就与陈经济勾搭。为何独独李瓶儿爱上了西门庆?比这更重要的一点是,李瓶儿,一个“淫妇”,何时成为了有爱的能力的人?
这就是本书作者的“人性复杂说”不能完全说服我的原因。作者说:“她(宋惠莲)的浅薄下面藏着爱心和贞节,一旦遭遇大变故,这些品质会绽放出来”。惠莲给丈夫戴绿帽,怂恿西门庆给他另娶的时候,爱是藏着的,丈夫被害就突然绽放出来了。李瓶儿抛弃前几任丈夫,吞掉他们财产的时候爱是藏着的,嫁给西门庆就突然绽放出来了。爱像是一个开关,在谁身上有,能不能开,到什么程度开,都是随机的,只用“人性复杂”一言蔽之即可。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来回头看看李瓶儿的正反面——潘金莲,这个彻头彻尾的淫妇,“有X就是达”的纯身体欲望代表。她在西门庆之死那几回的言行,简直不是一个正常人类——再欲求不满的淫妇,会不会在丈夫病的面如金纸,下面肿大如茄子的时候,想到的是趁他这么大来一回“倒浇烛”?这还是在她刚闯下大祸,强行喂了过量胡僧药让西门庆变身“精血喷泉”之后?如果说前七十几回潘金莲是“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那这明显就是杀鸡取卵的要命操作了啊。就算不在乎西门庆死活,她自己日后的性福也不在乎了吗?这显然不合常理,不像是潘金莲这样的聪明且极端自利的人做出来的事,但作者却这样写了。为何这样写?本书中提供了几个解释,一个是回目之间文字质量良莠不齐,西门庆之死为分界,作者仿佛一下子失了气力,潦草收场;第二个是,金瓶梅本就是一本劝诫书,为了突出“淫”的害处,作者进行了夸张的处理,代价就是失去了真实性。
但是,如果把潘金莲与李瓶儿放在一起比照看,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本书诞生于主写“情”事的文学与戏剧作品大量涌现的明朝中晚期,比公认的“情教”创始人,第一个高举“情”字大旗的冯梦龙还要稍早。如今提起情感小说在中国的发端,研究多以冯梦龙为代表,但兰陵笑笑生比冯梦龙更早看见了情,写出了情(写的还非常好)。只是,他不免在“有情”的人性与“淫妇VS良家女”的女性刻板印象之间产生了割裂,这种割裂突出地表现在宋惠莲和李瓶儿,尤其是后者身上。李瓶儿是兰陵笑笑生婴儿学步式的情感人物塑造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人物比潘金莲更有革命性。这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李瓶儿这个“淫妇”,何时成为了有爱的能力的人?李瓶儿是一个“淫妇”,也是一个具备情感能力的人,不是某个变故触发了爱的“开关”,而是“情”这一陌生的新兴概念尚未融合到传统的女性人物塑造之中。
这个答案还可以更进一步,李瓶儿不是一个恰好具备情感能力的“淫妇”,而是,李瓶儿具备情感能力,她就必须是一个“淫妇”。对这个结论的解释,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为何独独李瓶儿爱上了西门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稍微跳开些去,来看看另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吴月娘。西门庆的六房妻妾,只有月娘是“女儿填房嫁他”,其余几人皆是“趁来的老婆”。一个良家女,好人家的正妻,在小说中是怎样表现的呢?小说里写出的两人床事只有一场,几个月的冷战过后,西门庆来求和,月娘手上三推四阻,嘴里也骂,实在是推不过,才不得已遂了西门庆的意。两人平常说话,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西门庆与月娘谈正事,涉及家中财物、人员安排,另一个是月娘斥责西门庆,骂得丝毫不留体面。印象极深的是69回,西门庆嘲笑王三官放着媳妇不理出去偷嘴吃,月娘反手就是一个暴击:“你‘乳老鸦笑话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这井里水,无所不为,清洁了些甚么儿?还要禁人!”又一次说的西门庆一声不言语。月娘完全不在乎与西门庆是否“亲密”,她唯一在乎的就是要生下儿子。
反观潘金莲是如何迎合西门庆的,只消一例便知。72回有一段,两人睡到一半,西门庆要下床溺尿,潘金莲不放,说道:“我的亲亲,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里,替你咽了罢,省的冷呵呵的热身子,你下去冻着,倒值了多的。”于是就真的咽下去了,咽完还说“有点咸,拿香茶与我压压”。饶是我读书之前做好了“此乃淫书”的心理准备,也着实被惊吓到了,刚吃的晚饭争相上涌。
这就是良家女与淫妇,“正经女儿”与“趁来的老婆”的区别。这里要说的是,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别,并非金瓶梅个例,甚至不是中国独有。李海燕在《心灵革命》中论述道:“异性恋的去合法化直接引发的后果,是婚姻关系的仪式化(两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和依恋在此既不相关,也不道德)和将女性划为好女人与坏女人。好女人是作为一个人的母亲或妻子能助其履行社会秩序再生产之义务的女人,坏女人则是色情方面的专家,包括姬妾、妓女或仙女,满足男人在生殖与生产范畴之外寻求激情爱或冒险性经历的需要。”在中国与西方的封建时代,情爱与婚姻都是不相容的。代表婚姻的吴月娘是儒家规则的典范(书中女性角色比较来看),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她不与西门庆亲密,正是因为规则内不允许感官的想象和神秘的冒险,只有脱离了儒家传统的家族、身份、性别角色,才能够有亲密情感的发展空间。妓女与仙女看似天差地别,但她们都是儒家规则之外的女性,正是在这片“规则外”的肥沃土壤上,诞生了冯梦龙的“情教”对儒教的批判性继承。潘金莲与吴月娘,一个是典型的坏女人,一个是典型的好女人,两者都没有脱出女性的二元想象,只有李瓶儿,独独李瓶儿,爱上了西门庆。于是我们看到,有“情”之后,李瓶儿没有那么“淫”了。只是,掌握不好平衡的兰陵笑笑生在李瓶儿的“好”和“坏”之间反复横跳,甚至把瓶儿性格都变了,我自己在读到李瓶儿被潘金莲算计死了儿子依然只会独自躲在房里哭泣的时候,是觉得很别扭的。
时间又过了两百年,终于到了曹公的时代,李瓶儿进化成了秦可卿,甚至薛宝钗、林黛玉……“情”的精神性与孕育它的“淫”的肉体性之间的粘连不清被曹公划时代的“意淫”概念完美解决,真不知他如何想来,不得不令人击节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