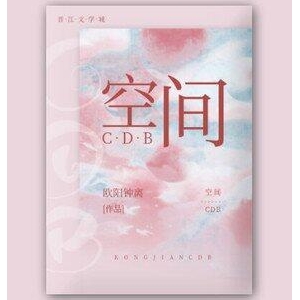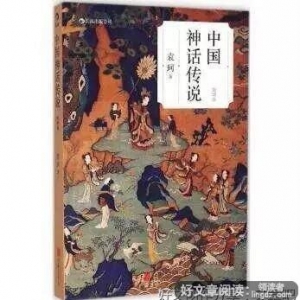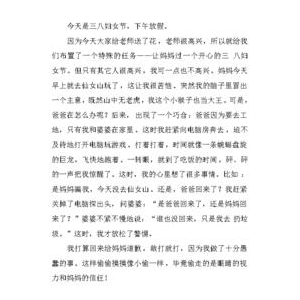早就过了掰着指头盼过年的岁数。但是,每到年关总有一些画面在脑海里时隐时现,那是儿时在乡里过年的情景。
记忆中最清晰的画面是“燎天蓬”。应当说那是一个特别而神圣的仪式,地点大多选在打麦场等开阔地,本家族无论老少都要参加。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各家就早早聚齐了。先由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者点燃事先堆好的柴禾,当红红的火焰腾空而起时,长辈们围着火堆撒些五谷杂粮,边撒边吟唱吉祥话。大家表情肃穆、庄重,谁都不敢说话,只有我们毛孩子心里窃喜,盘算着仪式结束了能捡些花生、瓜子之类的好吃的。片刻功夫,火苗跳得慢了、弱了,也就到了跨火堆的时候了,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从火堆上来回跨三次,燎掉侮气,燎来财气和旺气,让来年的日子火火的、旺旺的。我们家族有十多口人,大家以火堆为起点围成首尾相接的圆,在长辈的示意下开始了“燎天蓬”,那景象有点象口衔火珠的长龙,预示着来年的丰收。
还有一种祈福就是荡秋千。大概是借高飞的喻义,让来年生活步步登高。村里并不是家家都有秋千的,所以栽了秋千的人家就变得门庭若市,因为人多,我跟伙伴们只能让大人们带着荡,尽管这样,还是高兴得要命。秋千旁边专门有人当推手,每推一次,他就大声喊话:“高不高?”在场的和秋千上的人便齐声应答:“高!”“看见没?”“看见了!”“看见什么了?”“看见好日子了!”
我最喜欢的还是追社火和大拜年。社火演到那我和伙伴们就追到那,说真的,那些旱船、大头娃娃和秧歌表演,我们早就看熟了。每日穷追不舍,一是为凑热闹,二是为讨好吃的。因为社火队所到之处,乡亲们都准备了油棒子(麻花)、馓子、瓜子糖之类的年香犒劳他们,乡亲好客,散年香时当然少不了我们这些跟屁虫。我们也少不得给乡亲乐子,脸蛋皴皮的女娃,鼻涕冻成硬嘎巴的男娃可放得开了,插空加塞的也要给乡亲耍一段,逗得满场喝采。
再后来,一村的娃凑一块挨家挨户拜年,那架式就像地头上的家雀,到那家都得排队磕头,乡亲自然发不起这么多压岁钱,只是散些花糖和夸奖。但是,在我和伙伴们眼中这是最好的压岁礼,我们走家串户拜年致福,撒下一村的欢笑。
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再没有过这样喧闹的年,再没有这样纯朴的年味,乡野之年早已浓缩成“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寇简朴古风存”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