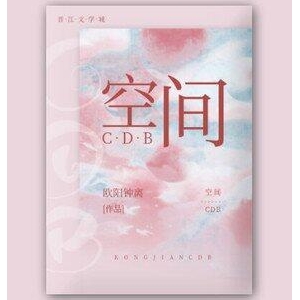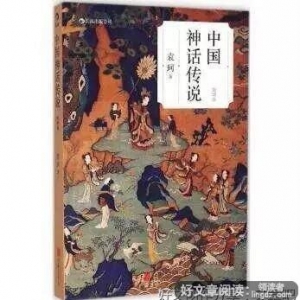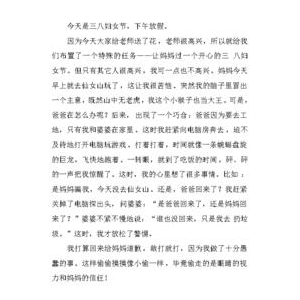类似的狂欢氛围频繁地出现在节奏紧凑的后半段。例如,旧布料可能呼应了原著中格里高尔的藏身之处──为了不吓到家人,格里高尔用床单将自己蒙住。这种安静、隐秘的行为在舞台上表现为非常激烈的身体性表演,由格里高尔与他的家人们伴随着喧闹而愉快的音乐共同完成。虽然气氛与原著大相径庭,却与剧场契合,并且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共通的家庭关系。剧场中格里高尔与家人们的关系仍是虚伪的,但通过疯癫怪诞而非冷漠疏离来表现。
影像与表演的配合非常出彩。拍摄快递员真实生活的纪录片出现在戏的开场部分,将这一位格里高尔的生活环境陈列在观众眼前。我们立刻意识到,剧场中呈现的不是那位旅行推销员,而是某一位曾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快递员。纪录片有效地实现了剧场中难以表达的环境描写,而社会环境的不同正是李建军的《变形记》与卡夫卡原著最重要的区别。
演员脸部特写的实时影像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快递员格里高尔每天与形形色色的人短暂接触,这些与格里高尔萍水相逢的人也出现在剧中。创作者以这种方式塑造了同一社会环境中芸芸众生的群像,而这些个体也同样是被异化的。在这一段表演中,扮演格里高尔的演员快速地依次再现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摄影机对准演员的脸,将影像投射到屏幕上,人们各异的精神样貌全部通过演员的脸表现出来。演员几乎没有表现出剧场中可观察的肢体动作,观众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屏幕上的特写上。影像的质量非常粗糙,但夸张的鱼眼镜头极具力量感,又如同安居家中的我们透过门镜一窥某位邻居的隐秘生活。此时,观众不得不认可演员精彩的表现,这种精彩并不一定证明演员演技高超,而是由于恰当的表演方式与恰当的影像相互配合。
妹妹的扮演者的表演在这方面更加明显。这位演员在前半段的身体表演不够出彩,缺乏辨识度,用方言说台词的方式也缺乏说服力。在演出的后半段,妹妹在网络上直播唱歌取悦观众,与原著中妹妹拉小提琴取悦房客一致。这时,演员的脸部特写投射在屏幕上,我们突然发现这张脸是如此单纯、呆滞却楚楚动人。创作者完整地保留了妹妹唱歌的段落,在整个作品的结构上显得过长。观众们热爱妹妹的歌声,无论是刻意跑调的还是优美悦耳的,甚至集体挥舞起点亮了闪光灯的手机。我们可以将这段表演看作是可消费的娱乐,一种蓄意的媚俗,却不能否认它出现在《变形记》的舞台上非常自然,甚至带着模棱两可的讽刺意味。演员的脸部特写是实现剧场效果的关键。这是一位擅长用脸而非身体表演的演员,但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一部作品指责演员的不完美,只要表演能以恰当的方式实现剧场性的表达就足够了。
影像的运用使剧场艺术能够选择性地呈现表演者的某些外观,这些外观的呈现足以制造强大的剧场效果。“在一切深刻的戏剧性之中,角色并不像有些人反复唠叨的那样,依靠心理分析而存在,角色是通过生物组织而存在的。演员的关键素质就是营造其生物组织:无论他是肥胖、蜡黄、胆小、汗津津还是爆裂,把人的物质状态抛上前台,也就是惹得我们犯恶心,这就是坚实的戏剧。”[1]正如罗密欧·卡斯特鲁奇曾经选择身体极度肥胖的演员来扮演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卡珊德拉,却选择极度瘦削的演员来扮演俄瑞斯忒斯,话剧《变形记》中演员的外观也因摄影机的参与而被恰当地呈现出来。格里高尔的扮演者看起来确实很像一只甲虫,这并不是因为他技巧性地模仿了甲虫的动作,而是因为他的身体状态给人一种与甲虫相似的坚实感。当鱼眼镜头拍摄演员的脸时,他的眼睛大得不可思议,并且灵活地旋转,像是某种长着许多复眼的昆虫。虽然甲虫不具有这种眼睛,但虫的意象仍然能使观众感觉到一种非人的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