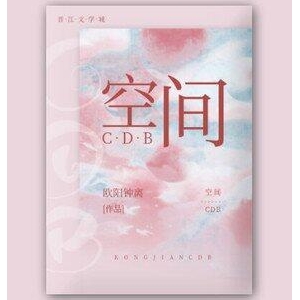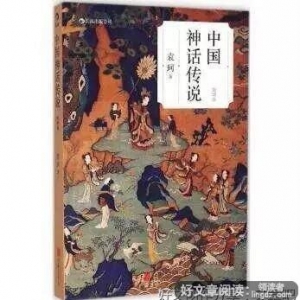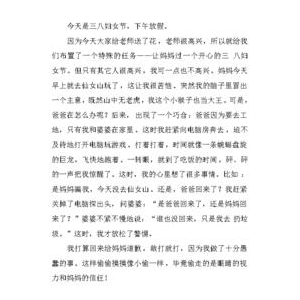女法医的口罩落在鼻子下方,脸上白色的肌肤和小巧的五官,都很好地掩饰了她的真实年龄,怎么看也不像四十六岁。她蹲下娇小的身子,拉了三下右手腕的手套边缘,这是她多年的法医生涯养成的习惯动作。
尸体虽严重腐烂,仍看得出是男性,还穿着夏天的短袖衬衫和薄棉西裤。现在已经是九月天了。
尸体周围有一滩早已凝固的深褐色血渍,不禁令人联想起先前血流成河的情景;后脑勺有个伤口,像一滩深褐色的死水潭,血水和损伤的骨肉混合在一起,黏糊糊的,白色的脑浆在黑红色里分外显眼,血浆和血渣令头发凝固在一起,像死水潭边的杂草丛;浅蓝色衬衫绝大面积被染成了黑色,胸膛袒露在外,胸腔骨和上腹部左季肋区之间区域遭到重创,伤口像一道深沟险壑,破裂的血管也裸露在外,白色蛆虫蠕动,虫卵也清晰可见。
在法医身旁不远,付燕青和贺嘉都在等待两名技术员的勘察结果,他们正在检查一个白色的稻草人偶。
人偶的制作工艺比较简陋,白布包裹着一堆稻草,用一根红绳系上,白布上画了眼睛、鼻子和嘴巴,很像传说中的幽灵,身上还扎了很多根绣花针。
可惜,技侦员没能从稻草人偶上提取到任何指纹。
「你怎么看?」 付燕青看着贺嘉,这个另类下属黑眼圈肿胀,如果不看那双敏锐的眼睛,他更像个颓唐的青年艺术家或者英俊的文化流氓。
贺嘉的食指关节放在鼻子下方,环视化肥仓库四周那几个通风口,感觉空气流通全靠墙上那几个 「猫洞」。
「报案人在哪儿?」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
「都在外边的警车上候着。」 付燕青说。先前县警搜查了报案人的家,没发现什么可疑,而后又被带回了案发现场。
「都什么人?」
「一个废品回收商,还有一只猫。」
贺嘉扬了下眉,看着直属上级,露出奇怪的笑容,觉得对方的冷幽默还行,但比起自己来要差点。
走到仓库外边,草婷再度假装没看见他,把脸撇到一旁,继续跟法医助理交流着什么。贺嘉的脸色沉了下来。
「儿女私情不要带到工作上。」 付燕青边走边说。
「我只是送水的,」 贺嘉耸耸肩,「还有你这话是对我说,还是对她?」
「你们 ——」 付燕青拖长尾音说道,掏出对讲机,「来人,来人,把报案人带过来。」
「收到。收到。」 同时,对讲机里还传出 「吱吱」 的电流声。
仓库四周是丘陵带,脚下开阔的杂草地延伸至一条小河边。据说河上流有个水电站,导致这一段水域窄,水流也极为缓慢,但没有受到污染,几只白鹭正在水面盘旋,还有几只长得像乌鸦的黑水鸡正在岸边觅食。
「这仓库建在这儿有点突兀。」 贺嘉说,双手比划成一个取景框,河风拂动他浓密的卷发,在秋阳下泛着亮光。
「非法修建的,化肥商欠债都跑路了,仓库查封也有一段时间了,本地新闻网上都报过。」 付燕青解释说。
这时,一名制服警察将报案人带了过来。贺嘉望着那人,以及他怀中那猫,眉心蹙起两道细缝。
废品回收商四十多岁,皮肤古铜色,酒糟鼻,烟熏牙,浑浊的眼窝有些充血,一看便知常年酗酒。他穿着一身又脏又旧的西服,白衬衫领口黑了一大圈,手指皮粗肉燥,好像被一层烧焦的脏东西嵌入皮中。
他怀中那只猫瘦成皮包骨,棕色的毛发像营养不良的枯草,浑身癞痢,裸露的肉坑上有明显的烟头烫伤。它的小脑袋瑟瑟发抖,惊慌的眼神可怜无助,有气无力朝刑警喵了两声。
「怎么回事?」 贺嘉质问道。
「同志,我已经说好多次了,昨晚追这只不听话的死猫,追到了这儿,然后就发现……」
「我问你猫怎么回事?」 贺嘉打断道,语气近乎呵斥,手指着遍体鳞伤的小猫,它配合着又喵了一声,绝望的眼神表明它对任何人类都不抱希望。
刑警这么一喝,废品商目瞪口呆,眼珠子怯怯地闪烁。
贺嘉看着猫,想起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都不应该存在」,这话出自澳洲黑金属乐队 「如渊深仇」(Abyssic Hate),现在来自这只猫的眼神。
「混蛋!」 贺嘉骂道,脸上青筋乍现,握紧拳头,指关节咔咔作响,吓得报案人退了一大步。
图片
看到新闻时,我的心跳又提到了每分钟 150 次。没想到第一次驱魔就成功了,回想起那恶魔的所作所为,他简直死有余辜。
我当时才十五岁,被当成疯子,绑在一张钢丝床上,手、脚、胸口都被病床绑带牢牢系着,那绑带跟航空安全带是一样的材质,可笑我当时还试图将它挣断。
炎热的夏天,在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
围在我身旁的几个盟友,都穿着 AC 米兰的黑红队服,他们一个个都像爬虫,冷冰冰地注视着我,静静等待那恶魔发号施令。
第一次看见那个东西,我觉得像二叔家新买的大型吸尘器。我当时不知道我要接受何种惩罚,心里害怕极了。他们将我五花大绑,我以为是要拿皮带抽我,或者脱掉我的袜子挠我脚底板。我不 是在说笑,我国古代有一种笑刑,在人的脚底板上涂满蜂蜜,然后牵一头山羊来添,这刑罚好笑又残忍吧?我当时真这么想了。我从小到大一直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这跟我父母身体里那些不负责任的艺术细胞有关吧。
盟友按照恶魔的吩咐,将 「吸尘器」 上的两条导线连接到我的颞骨上,也就是左右太阳穴,另外两条连在我的左右手虎口上。听到恶魔说检查电阻,我才明白那四条阴森恐怖的线是通电线。
盟友 7 号命令我张嘴,我咬紧牙关狠狠瞪着他。「啪啪」 两个大耳巴子打得我脸颊发烫。盟友 10 号和 9 号也走过来帮忙。这三个家伙的球衣号码正好是 AC 米兰队的舍甫琴科,鲁伊科斯塔和因扎吉。
鲁伊科斯塔掐住我的脖子,因扎吉捏住我的鼻子,几秒钟后我就乖乖乖乖张开了嘴。舍甫琴科塞了块牙垫在我嘴里,动作极为灵敏。我以为堵住我的嘴是怕我待会儿叫得太大声。
谢天谢地,后来还多亏了舍甫琴科给我的那块牙垫,否则我可能会咬掉自己的舌头。
电击的滋味简直让人痛不欲生。那种痛就像被人往肌肉里注射金属液体,耳边如同两把电钻发出巨大噪音,双手虎口像被刺入了两根又细又长的银针,一直扎进了骨头缝里,那种痛往心里一阵阵地钻,像一把烧红的切腹刀在肚子里搅动。
断断续续,被电了三次。
我当着众人面尿湿了裤裆,眼泪没有流出眼眶,而是滴进了心里。
「知道自己错了吗?」 那恶魔的声音在耳边飞旋,「父母辛苦养育你,你难道一点都体会不到他们的艰辛吗?」
「我日你娘……」
我还没骂完,耳边的电钻声又响起,眼前全是雪花片。
「知道错了吗?认识到打游戏的危害了吗?」
我浑身上下包括舌头都已经麻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脑子里天旋地转,感觉灵魂和肉身已经若即若离。稍微喘过气,再一看,10 号、7 号和 9 号盟友连样子都变了,他们真的变成了鲁伊科斯塔,舍甫琴科和因扎吉。
我当时就在内心诅咒他们,他们仨是那恶魔的主要帮凶,我诅咒他们下地狱。我顺带还诅咒了 AC 米兰足球队。
同年的欧冠决赛,AC 米兰输给了利物浦,鲁伊科斯塔和因扎吉都没能上场,而舍甫琴科发点球被扑了出来。
那天晚上在家看电视,当我看到诅咒灵验时,我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那一刻,电视机忽然变成了两扇闪着白光的大门,在我面前缓缓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