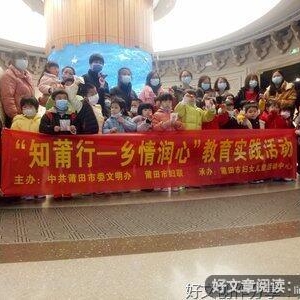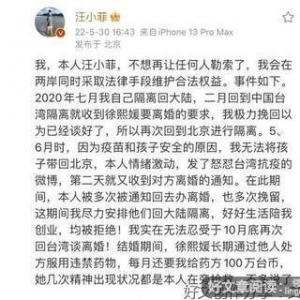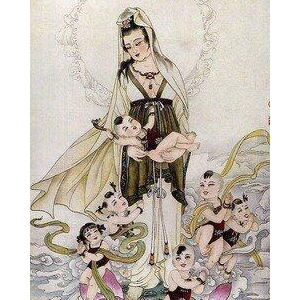那年春节前,我从青海省教育学院学习结束后,踏上了南归的列车——西宁—上海的178 次直快。
车,载着我对阔别数年的故乡、亲人深深眷恋之情,伴随着莽莽高原深沉而雄浑的节奏声,进入了夜间行驶。喇叭中传出列车播音员亲切和蔼的声音:“旅客同志们,卧铺车厢还有几个空床位,哪位旅客需登记,请到8 号车厢办理手续。”
半夜时分,一觉醒来,昏暗的灯光中,斜对面的三铺上坐着一位黑黝黝的近四十岁的男人,正探着脑袋向着窗外东张西望。戒备心立即提醒我:我的提包,里面装着相机!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哦,提包仍静静地躺在那儿,我舒了口气,又回到床上。那人似乎觉察到什么,朝我笑笑,随即又转过头去,目光,仍注视着漆黑的窗外。
为了避开晨起洗漱的高峰,我五点就起床洗漱完毕了。后来,从对铺同乡口中得知,我斜对面三床的也是从西宁上的车,刚从青海都兰监狱释放的,我心中仿佛明白了什么。
也许出于一种文学创作的本能,不一会儿,我便和他攀谈起来。他十五年前因犯流氓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入狱后又因打群架加刑十年。十几年西北高原的劳教生活,已使他的思想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彻底的转变。只听他喋喋不休:“这次回去了得重新做人,好好生活,好好干一番事业!要么经商,要么承包几十亩农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人发誓。
每每重复时,目光总是那样的坚定,充满着希望和向往。我的脑海不免跳出陶渊明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诗句。虽然生活的时代背景,事情的性质不一样,但那份渴望自由和向往幸福生活的心情是相同的。
列车,带着一千多人的酸甜苦辣,不停歇地奔驶着。他,很少静静地坐下来。他似一位不知疲倦的初次出门的孩童,这儿走走,那儿瞧瞧,满脸喜色,一切都感到新奇!他一会儿打开红塔山递到男同胞手中,一会儿拿出橘子、苹果塞到我们手里,一会儿又从包底掏出在劳改农场图书室照的相片。一张照片一个故事,讲得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犹如放开闸门的水,势不可挡!仿佛要讲完他牢狱生活的全过程。我的目光刚想离开,只见他又翻出一套崭新的西服穿上,领带系上,对着窗玻璃左照照,右看看,犹如待嫁的新娘,喜滋滋地问我们合不合身,他说那是他姐姐寄来的。他穿上,脱下;又穿上,再脱下,反复几次,说是等到下车之前再穿,好干干净净见家人!
车,经过一个昼夜的行驶,已发出疲惫而沉重的喘息声,而车厢里的他,却还在不停地忙碌着,穿梭着:谁的缸子没水了,他赶紧倒上;暖瓶空了,他连忙去打;地上有瓜果皮壳,他立即清扫;中转车站一到,谁想吃什么,他抢着去买……目睹着这一切,我的心里酸酸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在喷涌?这是一种来自他内心深处的一种人的本性的情感在狂泻!
此刻的他,仿佛浑身每个细胞都张开了大大的嘴巴,尽情地吮吸着大自然的阳光,在吸入的同时又在全方位地释放!他这分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追回曾逝去的时光啊!他一边在帮着别人,口中却不停地问我们上海车站何时能到。他说从办释放证的前几天就没睡着过觉,夜夜盼天明,也没给家人去电话,为的是给全家人来个惊喜!他归心似箭,一路的旅途都处在重获新生与自由的那份极度亢奋、喜悦中。我想:如果当初他就知道自己一失足就将成为千古恨,在大西北的深处一待就是十几年,他还会去触犯法律吗?值得欣喜的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呵!
翌日,晨曦未露,我还没有起床。他就把我的缸子洗净,穿越七八节车厢到餐车给我打来了热腾腾的稀饭,双手端到我的面前,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也许是感激我途中对他的信任、鼓励;也许他是浙江人,我是江苏人,都是近邻;抑或是十几年西北劳改农场生活的改造、磨炼、学习、反思,他真正懂得了人生的价值。一个人来到世上不仅仅只考虑自己,只为了自己,也要为别人,为社会做点什么,应该懂得怎样去生活……我记下了他犯罪的前因后果,他要求我別写出他的真实名字,我应允了。他再三嘱托我转达:告诫那些徘徊、行走在犯罪边缘的青年朋友,切莫像他那样,一定要做个懂法守法,对社会有用的人……
南京车站到了。
他帮我收拾行李,执意送我下车。冬日的南京站台,拥挤的人流中,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离别之后,我目送着东去的飞驰列车,伫立站台许久、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