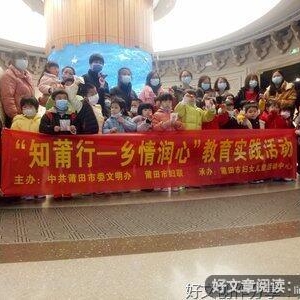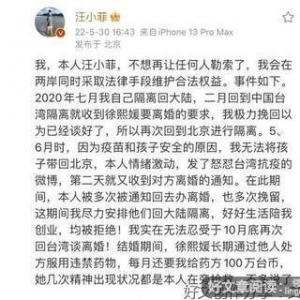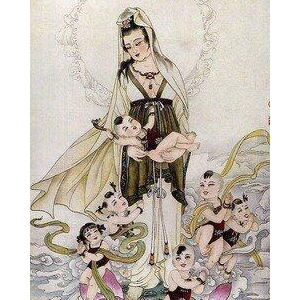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新五代史》是一本由(宋) 欧阳修 撰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0元,页数:10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五代史》读后感(一):【转】曹家齐: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新论
【作者简介】曹家齐,1966年生,江苏丰县人,师从徐规先生和龚延明先生,1997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又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辽金史、中国古代交通史等。著有《宋代的交通与政治》《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等专著七部,发表《宋代书判拔萃科考》、《宋代身言书判试行废考论》、《宋朝皇帝与朝臣的信息博弈》等论文九十余篇。
《新五代史》读后感(二):【轉】唐雯:《新五代史》宋元本溯源
唐雯.《新五代史》宋元本溯源[J].文史,2017(02):135-156
作者, 唐雯,時任復旦大學漢唐文獻工作室副研究員
內容摘要:《新五代史》由於作者的巨大聲名,在歐陽脩生前及去世後不久即廣爲流布,本文通過對《通鑑考異》《雞肋集·五代雜論》及吴縝《五代史纂誤》引《歐史》的梳理,展示了《新五代史》在歐陽脩去世後二十年内各類文本的面貌,並通過抉發《新五代史》北宋文本與現存宋元本之間的聯繫,梳理了現存宋元本的版本系統,並展示了現存宋元本各自獨特的文獻價值。
关键词:新五代史;稿本;刊本;國圖本;宗文本;慶元本
鏈接: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7&filename=WSWS201702010&v=b5DRDzC2nN72q%25mmd2B4dPglBr9jFwOleeOXjo1kS78jlwRx5dWpkgGO5g1rT9mEtJIDu
《新五代史》读后感(三):【转】王瑜:欧阳修经史之学与宋代义理史学的发生
本文原刊于《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1期 中文摘要: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义理史学的发生与逐渐形成是宋代史学的主流趋势。义理史学的成熟是在南宋时期,而学界对其何时开始则未有定论。本文通过考察北宋时期重要史家欧阳修的经学与史学思想,认为义理史学的基本特征皆已蕴含于欧氏的史学实践当中。而通过分析义理史学代表人物的相关言论,亦可证明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义理史学形成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欧阳修;经学;史学;义理史学 作者简介:王瑜,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官方史学与私人史学皆有建树,不单历史著作汗牛充栋,史学思想更有显著突破。当前学界对于宋代史学发展状况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然而还有不少具体问题值得探讨。宋代士人重振儒家思想,并且顺应着时代变化为其注入新的内涵。宋代史学最为当前学人所注意者,便是受到理学的影响而形成了“义理史学”[1],汤勤福将其特征总结为“以理阐史,以史证理”[2]。罗炳良则将宋代义理史学视为宋元明史学的主要思潮,与清代的实证性史学并举[3]。 宋代史学的确存在逐步义理化的总体趋向,但是以“义理史学”对宋代史学加以概括也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实际上,北宋与南宋史学的面貌便存在明显差异,不宜一概而论,即便仅论南宋,在义理史学之外的其他史学流派及史学思想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宋代史学的发展过程,需要对其进行分阶段的细致考察,尤其是探明宋代史学义理化何以发生、如何发生,以及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发展路向等问题。本文旨在以欧阳修为中心,探讨北宋士人关于经史关系的思考对宋代史学发展路向所具有的关键性影响。 一 宋代在思想学术方面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为中华文明开辟了全新境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谓“理学”思想体系的构建。随着理学的影响日益上升并在南宋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史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理学化的嬗变,最终形成了“义理史学”。 北宋的文化复古运动带动当时学者更新历史观念,对历史的原则与标准等根本性问题进行再思考。太宗、真宗时期,顺应政治与时局的需要,史家大都在历史著作中将“正统”“尊王”作为著史原则,同时也都比较注重凸显历史的鉴戒、垂训功能。仁宗至神宗时期,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编纂完成了一批重要历史著作,相当于对北宋前期史学思想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欧阳修的史学贡献在于对《春秋》的著史原则加以发挥,形成了注重义例、崇尚道德的史学思想;而司马光的史学贡献则在于史书体例的创新,以及对于史学之政治维度的强调。 对北宋学术思想发展状况稍加了解便可发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热衷于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阐释,关于《诗》《易》及《春秋》的著述数量尤夥。北宋时期较为重要的思想家如孙复、胡瑗、欧阳修等人,皆曾专就《春秋》的性质、义旨、体例等进行阐发。《春秋》一书一般被认为是孔子亲修,因而历来被视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但是从其内容与形式来说,原本应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鲁国两百多年历史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作为儒家经典,《春秋》自汉代以来便被视为关乎治道的重要文本,董仲舒甚至提出“春秋决狱”之说。然而北宋以前,历代经学对其加以注疏,使其“经”的属性得到不断地强化,而其作为史的一面却被渐渐忽略了。宋代之前,也曾有人对《春秋》的“去历史化”倾向进行反拨,如唐代史家刘知幾,他在《史通》中特别指出《春秋》所蕴含的经世功能是通过历史叙事而实现的,然而毕竟未能成为经学之主流。 汉代以来,经学因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得以不断发展,对经典的演绎和阐释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宋朝建立后,对传统经学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则成为思想嬗变的先导。《宋史·艺文志》中,与《春秋》有关的著作为二百四十多种,而在清代所修的《四库全书》中,收入的有关《春秋》的著作为一百一十四部,其中三十八部为宋人所作,故而四库馆臣曰:“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4],这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 二 欧阳修对于宋代的学术思想发展而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刘子健在《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一书当中指出:北宋中期是宋代学术思想和政治演变的关键时期,而欧阳修则最能代表当时思想上的活跃和创新精神。[5]他一生著述颇丰,在文学、史学、政治等方面皆有建树,而他的种种成就背后,是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思考。在学术上,欧阳修对经学与史学是同样重视的,或者说,他研究儒家经典与撰写历史著作之间贯穿着同一的思想内核。 在经学方面,欧阳修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毛诗本义》《易童子问》《春秋论》等。四库馆臣对欧阳修的经学成就评价颇高,称其“文章名一世,而经术亦复湛深”[6]。史学方面,《新唐书》《新五代史》二书皆列入二十四史。《新唐书》为官修史书,欧阳修负责主持编纂《赞》《志》《表》及《本纪》并整齐全书体制。《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私人修撰,对于研究其史学主张更为重要。此外,他还著有关于器物研究的专著《集古录》,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分支——金石学。除了经史两方面的成就之外,他的文学造诣更助他成为一代文宗,再加上在政治领域的地位,使其思想对整个士人群体拥有影响力。南宋史家王偁为其作传称:“孔子既没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有荀卿,荀卿之后而杨雄出,雄之后而韩愈继,继愈之后,而修得其传,其所以明道祕而息邪说,立化本而振儒风……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日月所不能磨而竭矣。”[7]可谓推崇备至。 欧阳修研习经学的基本态度是寻本溯源,突出地表现为对汉唐以来“疏不破注”这一传统的突破。他在评价孙复时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8]这种观点也贯穿于其本人的《春秋》之学,他特别注重对历代“传注”“曲说”进行驱惑。欧阳修对《春秋》三传颇有不满,直斥“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而已”[9],并且指出“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10]。欧阳修的批评针对的是三传对《春秋》带来的负面影响,即传文对经文的曲说、误读以及过度阐释淹没了圣人之言的本旨。他主张回到经典本身,拜托传注的影响:“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11] 在《诗本义》中,欧阳修对《诗经》之学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主张据文求义,抛开诸家成说,探求“诗人之意”及“圣人之志”。朱熹对欧阳修的《诗经》之学多有推扬,评价其《毛本义》“煞说得有好处”,对其开创性也做了正面评价:“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12]这种看法为后世学人所认同,至清代遂将欧阳修视为宋代《诗经》研究的开风气者。欧阳修的《诗经》研究中常被论及的是他的疑古思想,尤其是对毛、郑二家提出的批评,认为他们对许多诗作的解读有穿凿附会之嫌。欧阳修关于《诗经》的意见直接推动了宋代疑经思潮的发展,为新型文化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前提。 易学方面,欧阳修同样用力颇深,作有《易童子问》《易或问》《明用》《张令注周易序》《传易图序》《崇文总目叙释·易类》《刚说》《系辞说》等一系列文章。他的易学思想首先是从文本切入,认为“十翼”并非全出孔子之手:“余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13]这种认识是其“疑古”思想的明确表述,比之其在《诗经》上的态度更为激进。其次,他认为《易经》以人事为旨归,对一直以来将其视为卜筮之书的观念加以否定。欧阳修概括此书曰:“《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六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因此“学者专其辞于筮占,尤见非于孔子,况遗其辞而执其占法,欲以见文王作易之意,不亦远乎!”[14]他的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将汉代以来对于《易》的一般看法完全改变了。 三 欧阳修在史学领域取得的斐然成就,根柢在于思想的革新,就其经学而言,可以说体现出尊重客观现实、注重历史真相的历史主义倾向。这种倾向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尊经而疑传。欧阳修虽然是经学变古思潮的旗帜性人物,但是他对于儒家经典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所着力批判的乃是对圣人之言进行阐释的历代“经师”所留下的注疏文字。所谓经学,其建立过程便是不断地围绕着圣人与经典在思想体系上进行完善与丰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对经典的阐释自然会出现误读、曲解、穿凿以及过度阐释等现象。宋初依旧如此,甚而当经与传有所龃龉时,“学者宁舍经而从传”[15]。因此,欧阳修有意识地将经与传进行剥离甚至对立,目的在于祛除历代注疏加诸经之上的层层蒙蔽。欧阳修在抛出这些意见时,预见到了可能会遭遇的议论,同时也体现了他非凡的勇气,他自称:“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16] 宋代逐渐形成的疑古思潮,后来发展为以己意解经的风气,许多人将欧阳修视为始作俑者。如南宋王应麟所言:“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17]“排《系辞》”“毁《周礼》”“黜《诗》之序”等语皆指涉欧阳修,由此可见他的怀疑精神确乎产生了时代性的影响。 尊经疑传的基本态度在欧阳修那里是一以贯之的,从经学角度而言,他明确提出的理由是作者的身份差异。经的作者是圣人,在经学范畴内,“圣人之言”具有先验性的权威,所谓“万世取信,一人而已”[18]。因此他认为经学首先要从文本上确定哪些出诸圣人之手、哪些出诸后世儒生、经师之手,这相当于史学当中对材料的甄别,而采取的方法便是史学当中的辨伪。 第二,求情而责实。在尊经的基础上,欧阳修的解经是以客观与真实为原则的。他在《春秋论中》当中提出孔子之作《春秋》是为了“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9]。“别是非,明善恶”是圣人作此书之目标,而“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则是实现此目标的途径或方式。欧阳修针对《诗经》提出的“据文求义”和针对《易经》提出的“止于人事”皆是一种力求客观与真实的态度。 欧阳修对《诗序》的批评绝非凿空之论,而是建立在具体分析之上的。在欧阳修之前,韩愈等人也曾对《诗序》有过质疑,但皆属泛泛而论,欧阳修则提供了大量证据来支撑其判断。虽然他本人对《诗序》并未完全否定,但其疑《诗序》的态度影响深远,周中孚谓“其后王介甫、刘原父、苏子由、程伊川、朱文公诸家,各著其说,更相发明,而毛、郑之学益微。……其实皆滥觞于是书也。”[20]“是书”即指欧阳修之《诗本义》。 真实一直是史学的核心要素,但是由于以往中国文化当中经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史学难以避免地受到经学的影响。欧阳修的经学则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一种平衡,再次强调了真实的重要性,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21]正是出于对真实的追求,欧阳修在其史学实践中,一方面引入了考证的思想,注重对文献资料进行梳理考证;一方面引入器物等物质性材料,作为对文献材料的重要补充。 第三,重人而轻天。欧阳修易学的突出特点在于以“人事”为要,他说:“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22]在《易或问》中更进一步说:“或曰:‘……易之为说,一本于天乎?其兼于人事乎?’曰:‘止于人事而已矣,天不与也。’”[23]这一认识与以往将《易》视为对“天道”之阐发,并且不断将之神秘化、数术化的倾向截然不同。这一特征在其有关其他儒家经典的论述中也是屡加阐发。 欧阳修提出以人情为锁钥来解释《诗经》亦是重人事的体现。欧阳修对《诗经》当中许多篇目都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并对自己的基本立场作了总结性的陈述。以《关雎》篇为例,毛诗、郑笺及历来注疏皆将此篇理解为赞誉“后妃之德”,而欧阳修则指出:“此岂近于人情?古之人简质,不如是之迂也。”[24]他认为:“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25]在分析《鹊巢》《螽斯》《出车》等篇什时也采用“以人情求之”的方式。 有关《春秋》的议论最能反映欧阳修的历史观念,而对人事的重视也通过许多言论加以发挥。他说:“夫据天道,仍人事,笔则笔而削则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据天道、仍人事”又被表述为“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 [26]。 顾及到圣人之言当中不乏对日食、陨石等异常天象的记载,欧阳修对“天道”“天意”等说法并未完全摒弃,但是他对历代儒生附会演绎而形成的谶纬迷信则深恶痛疾。《易或问》曰:“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参焉则人事惑。”[27]《新五代史》中,欧阳修重申此意:“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28]欧阳修在《石鷁论》中提出“圣人纪灾异,著劝戒而已矣”[29]的看法,对历来传文及注疏中宣扬天人感应的说法加以驳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曰:“(修)但平日不信符命,常著书以《周易》、河图、洛书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鸟》之诗为怪说。”[30]他曾专上《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对谶纬之说大加鞭挞,这一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立场在其所撰的史著中也有充分反映。 四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引人瞩目,在史学思想方面的开拓与创新更是将中国史学带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之所以能够在史学领域有如许创获,与其学术整体的宏大格局是密切相关的。上文对其经学思想的粗略总结已经指出,欧阳修在经学方面的诸多观念为其史学实践所贯彻,使其在史学领域也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 《新唐书》为官修史书,乃集体作业之产物,欧阳修于至和元年(1054)任“刊修官”,开始主持《新唐书》的编撰。此前修史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年,因此欧阳修主要负责的是纪、志、表等部分的修撰,这些情况在其《辞转礼部侍郎札子》中皆有明白的交待。而《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自景祐年间(1034-1038)就开始着手的私人撰述,直至其死后的熙宁五年(1072)方才问世,可谓欧公心血之作。 学界关于《新唐书》《新五代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则着重分析此二书对于义理史学之发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经学在欧阳修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其史学著述加以分析也不难看出他的经学与史学有着深入的糅合。《春秋》一书由于本就具有史书的属性,因此最为研究者所注意,欧阳修自身也的确将《春秋》作为一种史书范本加以取法,从义例书法、材料采择到著史原则、现实旨归皆有迹可循。《春秋》对欧阳修的史学之影响,要之有以下几点: 第一,春秋笔法。所谓笔法,即通过文字体现立场的表达方式,或称“春秋书法”“春秋书例”“春秋义例”等。《宋史·欧阳修传》载曰:“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31]欧阳修对《春秋》笔法的理解与运用的确是其著史的一大特点,但是他并非是对《春秋》笔法的僵化模仿,而是追求形式与本质的统一。 从形式上来看,欧阳修对《春秋》笔法的借鉴首先表现为使用特定词汇以寓褒贬。比如《新五代史》当中,“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又如“以身归曰降,以地归曰附”。[32]这在《新唐书》中也非常多见,比如对于“弒”“赦”“伏诛”等特定词语的使用。其次则是寓褒贬于叙事,通过对比等手法来传达道德理念。如《新五代史》中的《刘守光传》,“守光将死,泣曰:‘臣死无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将诉于地下。’晋王使召小喜瞋目曰:‘囚父弒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尔邪?’晋王怒,命先斩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何不赦臣使自効?’其二妇从旁骂曰:‘事已至此,生复何为?愿先死!’乃俱死。”[33]刘守光乞降求生与妇人之刚烈勇决之姿态形成强烈对比,叙事者的态度也就自然传达与读史者了。此外,欧阳修还通过体例上的创设以发扬《春秋》笔法。在《新五代史》中他设立“死节”“死事”“一行”“义儿”等类传,亦是想以此针砭乱世之人心浇漓、纲纪陵替。 第二,正统思想。欧阳修认为孔子作《春秋》的主旨在于“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其中正名定分在史学领域主要是关于正统的认识与界定。基于中国漫长而又复杂多变的历史,正统问题对于修史而言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欧阳修关于“正统”所发之议论集中于七篇文字,即《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秦论》《魏论》《东晋论》《后魏论》及《梁论》,这些看法在其晚年又归拢为《序论》《正统论上》《正统论下》三篇。 欧阳修的正统观自然也呈现于所撰史书当中,《新五代史》将梁书为正统的做法引起了广泛而长久的争议。欧阳修“不伪梁”是有意为之,是其正统观的具体表现,他也明白地道出其理由:“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34]他如此认识五代的正统问题表面看来是不同于众人的异论,而实际上则源于欧阳修对《春秋》的理解。他在《新五代史》之《梁本纪》的论中特别申明这是符合“《春秋》之志”的,不伪梁并非是为梁进行辩护,而在于“不没其实”。他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能知《春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35]除了在《新五代史》当中以梁为正统之外,他对于秦、魏、东晋及后魏等王朝所持的观点也是如此。以此可知,欧阳修在历史书写时依然是重视正统的,他的观点虽然与传统观点相左,原因在于他对于《春秋》有新的理解,而绝非对《春秋》尊王思想的否定。 第三,以理驭史。欧阳修的经学思想在其史学实践当中最为根本的影响是,将价值理念置于历史书写的核心地位,著史作为手段是为了重构儒家价值体系。欧阳修对现实心存忧虑,他在《本论》当中说:“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一切苟且,不易五代之时。”[36]至于五代他的总体评价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37]欧阳修是希图以五代为鉴戒,召唤“天理”——道德纲纪的回归。在其叙事及史论当中,欧阳修不断宣扬的是忠与孝,像“长乐老”冯道这样迭事四朝的人他痛斥其“无廉耻”。 “理”的另一重内涵是是治乱兴衰之规律,欧阳修首先认为天地万物有其客观规律,即所谓“常理”,同时又强调“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38]在他论《易》时便已提出“治乱在人而天不与”的观点,撰写史书时则表现为以“人事”解释历史现象,而将天命的影响置于次要地位,尤其是很大程度上摒弃了长久以来极有影响的灾异谶纬之说。 五 欧阳修的经学思想对其史学的影响当然还有许多体现,然而要指明他的史学实践与宋代义理史学的关系,则以上三点尤为重要。师法《春秋》义例、强调正统之辨、论史以理为先正是史学义理化的主要特征。虽然在北宋时期,欧阳修的史学后继乏人,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在他的史学撰著中已然蕴含了义理史学的趋向,这一点也可借由义理史学代表人物的言论得到佐证。 朱熹被公认为义理史学的集大成者,在其关于宋代理学发展历程的言论中,时常提及欧阳修,并且认为他是开创性人物之一。宋代士林推尊欧阳修为“文宗”,认为其最突出的是文学上的成就,而对其经学造诣则存在很大争议,如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言其“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39]。然而朱熹对欧阳修在义理方面的贡献则作出肯定评价,他对《诗本义》颇为推崇:“因言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故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40] 正统论是义理史学的重要命题,辨明正统是义理史学的重要内容,而正统论的提出则应归功于欧阳修,是他对《春秋》大义的体悟与提炼,而其关于正统的理论也影响了后来的诸多史家。朱熹曾评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其于《史记》,善善恶恶,如《唐六臣传》之属,又能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固非一端。”[41]这是依其义理史学的立场而给出的正面评价。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一书,虽本于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但在历史观上则更接近于欧阳修。朱熹在欧阳修“三绝三继”之正统说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使正统之说更为缜密细致。比如他提出“无统”之论:“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42]其实就是对欧阳修“正统有时而绝”进行了理论化的发展。 学者们对于义理史学的批评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所谓“荣经陋史”,也就是将历史书写作为论证义理的手段,而往往不惜牺牲历史的真实。如批评朱熹之《资治通鉴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43]这种情形在欧阳修所著的史书中虽然并不凸显,但是与其史学著述却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 其一,欧阳修重视史论。他对于历史事实虽然重视,但也存在史学工具化的倾向,意在通过历史叙述来传达价值观念。其二,欧阳修重“道”重“理”。也就是希望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与总结而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与圣王与圣人联系在一起。其三,欧阳修治学意在经世致用。义理史学的主要兴趣不在于追求历史的真实,而在于以历史作为资源服务于现实。 从这三点便可看出,欧阳修的史学著作当中确实已经蕴含了义理史学的核心要素。或者说,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当更多人对此有所感触时,他们自然地认识到欧氏史学的价值内涵,对其核心命题的继承与发展正是义理史学得以生成的重要前提。 注释:
[1] 当前学界还有“理学化史学”“史学的理学化”“义理化史学”等提法,参见曹宇峰《南宋义理史学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2] 汤勤福:《义理史学发微》,《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3] 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 [4]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8页。 [5] [美]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页。 [6]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0页。 [7] (宋)王偁:《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604页。 [8]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一册)《居士集》卷三十《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7页。 [9]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一册)《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6页。 [10]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一册)《居士集》卷十八《春秋或问》,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11页。 [11]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一册)《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6页。 [12]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解诗》,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9页。 [13]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三册)《易童子问》,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19页。 [14]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一册)《居士集》卷十八《易或问三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1-302页。 [15]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一册)《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5页。 [16]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5页。 [17]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19年。 [18]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一册)《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5页。 [19]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一册)《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7页。 [20]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八,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30-131页。 [21]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梁本纪·太祖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页。 [22]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三册)《易童子问》,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09页。 [23]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居士外集》卷十一《易或问》,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78页。 [24] (宋)欧阳修:《诗本义》,《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25] (宋)欧阳修:《诗本义》,《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26]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居士外集》卷十《石鷁论》,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80页。 [27]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居士外集》卷十一《易或问》,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78页。 [28]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九《司天考第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05页。 [29]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居士外集》卷十《石鷁论》,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81页。 [30]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欧阳诗本义十五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46-47页。 [31]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欧阳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81页。 [32]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梁本纪·太祖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17页。 [33]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刘守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27页。 [34]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3页。 [35]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梁本纪·太祖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22页。 [36]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居士外集》卷十《本论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62-863页。 [37]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0页。 [38]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7页。 [3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庚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35页。 [40]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6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9页。 [41]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45册《答周益公第二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页。 [42](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7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36页。 [43] 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