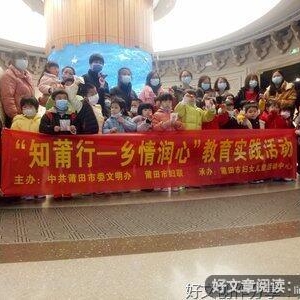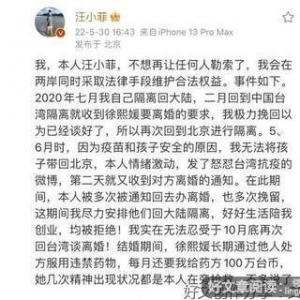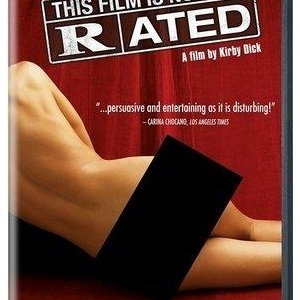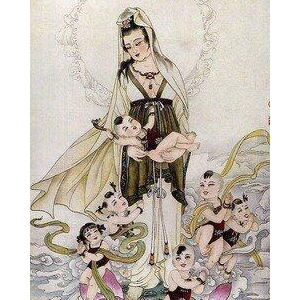大学期间,我曾去支教,班里有个稍显孤僻的小女孩,她从不跟人接触,一下课就躲在角落里自己玩,或者看其他人玩。可我总想为她做点什么,于是准备了果冻作为课堂提问的奖品。那节课上,我特意提问了那个小女孩好几次,她很聪明,每一次都答对了,甚至在后半堂课上主动举手了。下课后,我便将最大的那颗果冻奖励给了她。
她很开心,就在她被所有小朋友围在中间,准备在大家的注视下独自享用胜利果实的时候,我说了句不该说的话。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她融入集体,便学着卡通人物的声音对她说:“要不要和小伙伴一起分享呀?”她抬起头瞪了我一眼,一把將那碗果冻打翻在地,说:“那我不要了。”
5年过去了,我依旧无法释怀。那时的我凭什么就认为她应该分享用实力赢来的奖品,凭什么就认为躲在角落自己玩、看别人玩的她,是不开心的呢?这是一个“子非鱼”式的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只不过我隐约觉得,作为旁人的我,似乎是没有资格给出答案的。
很令人无奈的是,我虽然有了这个意识,却还是会不自觉对一些人、一些事妄下断语。工作以后,我结识了一位后来跟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那种淡淡的人,喜欢猫,喜欢无印良品,喜欢是枝裕和的那种安静舒缓的电影。
我年少无知时总爱借用“约你你说不来,来了你又不嗨”来嘲笑局上那些面无表情、事不关己、低头玩手机,和集体保持距离的人,那时我武断地认为,既然选择出来和大家一起玩,就要照顾到大家的情绪。
第一次带他和大家一起唱歌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穿了一件白衬衣,毕恭毕敬地对着大家鞠了一躬,抬起头时,脸上换了一副他从未有过的欢快神情,一看就是对着镜子练习了很多遍的那种。接着,他用极度不自然的俏皮语气说:“大家好,我是小北的朋友某某某,我就像我穿的白衬衣一样,安静又美好。”那个场面已经不能用冷场来形容,我们足足冷了有半分钟,简直像是在为什么事情默哀。
更让人伤神的是,和我预想的一样,他并不会主动唱歌,全程坐在角落里面带微笑,和着音乐轻轻晃动。我最怕这种场面,总担心自己照顾不周。因此,我不断和他互动。他倒是不拒绝,点给他的歌会拿起话筒轻轻唱,丢给他的骰子也会举在手里轻轻摇。可歌一停,酒一多,他就又坐在一旁不作声了。
我悄悄过去,小声问他是不是不喜欢和大家出来。他很纳闷,问我为什么这么问。在那之后,大家唱歌时总希望我能叫上他。因为叫他去有很多好处:他可以坐在点歌台前帮别人点歌,也可以站在桌前帮大家拍集体照。
关于这一点我非常愧疚,可他每次都自告奋勇。有次我实在忍不了那伙人,便对他提议说其实可以不用理他们的。他说,他喜欢帮他们点歌和拍照,相对于自己唱,他更喜欢看大家在那里又唱又跳的。
认识他之前,我以为我无法理解有人会喜欢帮人点歌和拍照,我太享受被照顾了,因此,希望场合里的人都能互相照顾,不希望有人被冷落。但在认识他之后,我终于了解了,原来对有些人来说,在一旁安静地照顾大家,看着大家,比跟大家一起嬉笑打闹更享受。
最终能够让我完全理解他特别之处的,是我自己遭遇的一些让我不好受的事。我曾为某个久未谋面的朋友的一句话,耿耿于怀了好多天。那是她时隔多年后再次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你活得不快乐。”我愣了。
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位在操场一角跟自己玩的小姑娘。我就是在那时终于确定了,原来自己曾经是这样可恶的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对别人的生活以及人生进行评判指点甚至横加干涉。对别人的生活和人生妄下断语、横加干涉的这群人当中,出于恶意的并不多,而大部分是因为关怀和善意。而这份善意却使他们忘记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法。
在我后来的人生当中,我又有幸结识了很多人。这些人当中,又有很多是特别的人。甚至在有些人眼里,我也很幸运地被视为特别的人。基于我并不开阔的眼界和我并不通达的世界观,这些特别的人,有些是我可以理解的,有些是我不能理解的,但不论我是否理解,也不论我是否接受,我都不会打扰他们,正如他们没有打扰我一样。
(一米阳光摘自《万物和你一样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