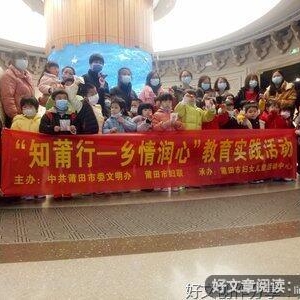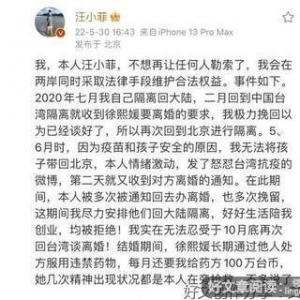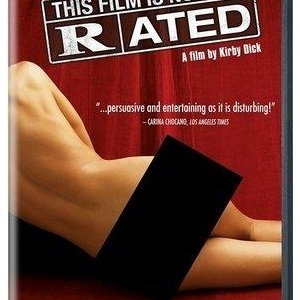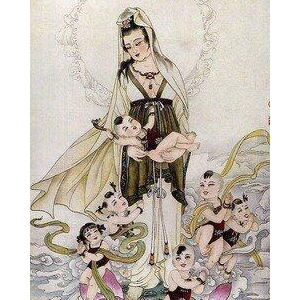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潮汐图》是一本由林棹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潮汐图》读后感(一):转载自南方文学盛典·2020年度对林棹颁发的最具潜力新人奖献词:
林棹出手不凡。《流溪》是她的小说处女作,但她无意加入任何写作的合唱,选择冒险、狂欢的话语姿态,也不过是想创造一个想象与现实的个人秘境。那些躁动的童年记忆、青春期情绪,被放大、照亮、提纯,并和博杂的知识经验相交织之后,幻化成了一个色彩绚烂的意识漩涡。这是一场艰难的自我辨认,不堪的现实、奇崛的修辞、极力在故事中隐藏自己的讲述方式,终究难掩一个女性独有的哀伤、虚空与绝望,以及她对爱与生机的呵护,对精神优游的想往。
《潮汐图》读后感(二):林棹《潮汐图》:粤语创作好胆量
林棹的《潮汐图》以粤语创作。北方读者阅读起来,大概会有与吴语开山小说—《海上花列传》的相似感受。但我大抵还能读懂,或许它更偏向于张爱玲的《海上花开》与《海上花落》。胡适先生曾说,粤语文学自招子庸以来,在韵文方面算很有成绩,但究竟离普通话太远,影响究竟还很少。不知身为广州人的林棹,是否潜意识里也希望增加粤语文学的影响力,才甘冒方言文学“许多字单有口音,没有文字”以及“懂得人少”这两大困难,写下清朝巨蛙奇幻的一生。
故事非常简单,讲述了清朝年间一只状如牛的巨蛙在广州中流沙地区被渔家女捕获收养,后又被英国博物学家携至澳门“好景花园”与众多奇珍异兽一起饲养研究,最后被运至英国动物园囚禁至几乎丧命,终老于一个教授家的大木盆(或死而复生逃掉了)里的故事。但正如林棹一贯的写作风格,角度和叙述方式令这个故事颇为不同。小说的第一人称是巨蛙自己,但同时辅以上帝视角,即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并用。读者走入故事的每一处都会踩着林棹最擅长的奇妙词语搭配和魔幻形容比喻,漫步于无边无际的虚空幻象当中。常人的想象力尚有边界,而林棹的文字则更像银河画上的水墨氤氲,唯有你想不到,未有她写不出。如果说《流溪》前几章原始森林般色块跳跃的话语是为了迎接一段悲伤至极故事所释放出的烟雾弹,那么如今的《潮汐图》则从头至尾就是作者将脑海中的全部奇思妙想与肆意妄为和盘托出、摊开、爆炸、散得漫天遍野,不再做特别故事性处理。而正如林棹所述,她也像小说里的H那般喜欢博物学、如契家姐这样爱水、与冯喜拥有同样以帆船探索世界的梦想,那么这部小说也许就是她个人喜好的完整清单,只是用蛙眼的视角表达出来,以小说的形式先行一步。
纵然这部小说未能再现《流溪》的惊艳与震撼(个人感受),且作为北方读者多少受限于方言障碍,但我仍随着一双蛙眼和凌驾于上空的神爷火华,穿越至清朝的广州,见到吃咸水饭的船公、船婆、船仔、船女、十三行街上的贫民、买办、番鬼和游走在村落撑船的货郎,被泼辣豪爽的契家姐与蛙仔之间以命相护的情谊感动,扼腕于她们身为女(雌)性同病相怜的苦痛命运;再漂至澳门大三巴,目睹番鬼乐园种种华洋杂处的奇葩与魔幻,笑叹人类装扮训练动物的迷思和诡异;最后远渡重洋来到曾经的日不落,为动物园内自残啄羽的丹顶鹤、冻饿至死的马来貘、下落不明的大羊驼、皮开肉绽的非洲象和死无葬身之地的饲养员们感到悲伤,因巨蛙能得迭亚高拼死相救而落泪。书至末尾,一场西班牙大流感将人类赶回“恐惧洞穴、抱紧自己”,而现实中的小说同样创作于另一场未完结的瘟疫。这一道书内书外的循环,真不知哪个才是梦。
《潮汐图》读后感(三):当巨蛙生吞文明
在大家的想象中,与文学相关的工作一定是充满诗意的、生动的。然而,作为一个学院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者,我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更多地与芜杂的文献材料、严谨的逻辑论证有关。日子久了,所谓文学的感觉甚至会遭到磨损,变得有些迟钝。因此,合上林棹新作《潮汐图》的时候,我在潮涌般的快乐中品尝到了一丝隐秘的羡艳。快乐自是不必说,羡艳则源自作者庞大充沛的想象力,和对语言近乎野蛮的直觉。
还记得初次阅读林棹,是她的处女作《流溪》。作为成长在岭南的女性,在翻开《流溪》的第一个瞬间就可以轻易地和另一个岭南少女相认,然后追随她逡巡在亚热带的密林、季风与潮湿里。如果说《流溪》是岭南的今生,那么《潮汐图》大概是岭南的前世。
这是一个由虚构生物巨蛙讲述的故事。巨蛙说,“我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生吞。”巨蛙通过生吞水中之物岸边之物认识了珠江、贫贱和汉字。于是,故事的语言风格亦犹如生吞。巨蛙不是作家,她不需要懂得何谓剪裁,何谓详略得当,不需要区分故事的主干或细节。她生吞下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所有,无需咀嚼,不经消化,然后宛如产卵一般泻于纸面:无论贵或贱、生或死、甚至有机或无机的一切,挤挤挨挨,黏腻密集得让人既恐惧又好奇。巨蛙不是人,她不做“万物的尺度”,因此她生吞之后模糊了一切事物的边界。她口中的颜料水彩“吃棉纸”,“自由地吃过去、吃开去”,“吃出老榕须格局”;她腹中的滚滚浓烟“发围,挺起孕肚”。在这些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萧红和北中国,那些寂寞的西红柿,张开大嘴的泥坑子,产崽的女人和猪。
我们常说雕塑和舞蹈是空间的艺术,因为身体和物质材料会占据一定体积的空间;而音乐、小说和电影是时间的艺术,因为它们都是线性排列的,占据一定长度的时间。因此舞蹈完全可以脱离音乐而存在,而我们偏爱为电影配上音乐,热衷把小说改编成影视。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潮汐图》是一部拒绝被影视化的小说。它的画面感当然很强,任何人看完描写鸬鹚胜的鸬鹚捕鱼的段落,都会赞叹其“历历在目”“栩栩如生”;观影经验丰富的读者甚至马上就可以想象出如何运镜如何剪辑,以还原出海皮自然史又或者是好景花园。但,这样的影像便不是巨蛙生吞下的世界了。林棹通过巨蛙的口腹赋予了语言一种空间感,或者说,《潮汐图》更像是一件巨大的装置艺术而非一部小说;不是读者在阅读文字,而是语言笼罩、吸附、包裹甚至圈禁了走进装置的读者。因此,如果有人害怕或拒绝,也在情理之中。用一个更浅显的比喻:《潮汐图》是一座语言的博物馆,字眼、词汇、句子和段落既是陈列之物又是建筑材料。再换句话说,在此处,语言本身就是意义、价值和美。也正因如此,小说在这里回归了其作为文学的本质。
那么,这是一部所谓“形式大于内容”的、炫技的小说吗?并非如此。巨蛙作为叙事者带来的不仅仅是生猛饱满的语言风格,同时带来的也是奇特的叙事视角。我们当然会想起卡夫卡和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由于格里高尔拥有曾经为人的记忆,甲虫提供了一种虽然陌生化但依然属于人类的视角。巨蛙诞生之初是尚未定型的动物,是通灵的怪兽,后来是被豢养的宠物,是被圈禁的珍奇,最终是孤绝的生物;虽然终生与人同行,但不曾有一日为人。因此,异类的视角——去人类中心化的视角在巨蛙身上获得了可能。在异类之眼的透视下,科学的光明投下政治的阴翳,19世纪欧陆博物学的蓬勃繁盛暴露出了殖民狰狞残酷的爪牙:“帝国人把人捆起像木料,推入舱底塞满”,但“他们还为植物定做专用船舱哩”。这是发达对落后的殖民,更是人类对自然的“殖民”。在这里,巨蛙当然是“反殖民的和反讽的”。
如此说来,巨蛙意味着原始的野性、返古的冲动?似乎也并非如此。巨蛙是兽,但巨蛙也是灵;巨蛙不是人,但巨蛙与人类共享了语言、情感和记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可以,弗兰肯斯坦造出的生物会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两百年后,林棹自如地扩张了玛丽·雪莱的野心,巨蛙开口说话,于是我们得以再次探寻文明与野蛮的辩证。
故事中时常会出现第二人称代词“你”。“你”既是故事中参观巨蛙19世纪男女,也是书页前阅读故事的21世纪的我们。这是巨蛙与人类的对望与对话。人类观赏巨蛙,巨蛙越是原始越是丑陋越是恶心,越能“腐蚀你的智识,撼动你的信仰”,人类就越是惊奇越是兴奋。原来,人类观赏野蛮以自证文明。巨蛙一边表演野蛮一边观看人类,洞察了赏玩野蛮正是文明最大的傲慢。然而,巨蛙依然是文明的学徒:冯喜给她讲古,H带她游历,茉莉·钟斯教她握笔,陌生的小女孩赐她圣祝。人类予以巨蛙知识和情感的滋养,巨蛙得以拥有自己的“成长史”,得以永恒葆有并封存最初的芫女和舢舨。随着故事的行进,小说的句子和段落越来越长,那是因为巨蛙逐渐拥有了“大忧郁”。
最值得玩味的是,巨蛙在动物园冷静地自剖:观察丹顶鹤与死神的缠斗带来关乎“审美、新知,和别的什么说不上来的”“自我感动的欢愉”。然而,当巨蛙逃出动物园遇到了更为远古的粉头鸭、恒河猴和袋狼时,她觉得它们“怪”,她表现得“很有教养”,她“用人的姿势坐下”,询问它们人的踪迹。巨蛙对它们不感兴趣,在生命的终点她仍然自觉地与雪达犬保持灵魂的界限,因为雪达犬把教授与女助手埃莉诺关于地球的辩论当成催眠曲。我们更不要忘记,巨蛙的挚友冯喜,是一个“要搏老命去”“远处地方”的画师。实际上,从珠江沿岸漂流到欧陆中心的巨蛙,实现的正是冯喜的一生所求。巨蛙是人类冯喜的兽影。一个岭南人“尽全部努力去想象冰川、白夜和极寒”,想象的不是远处地方的蛮荒,而是遥远的新知;“出海病”不一定是开疆拓土的野心,也可能是上下求索的欲望。好奇,或许正是文明的本能。
《潮汐图》的扉页有粤谚“听古勿驳古”,开篇第一句则为“我是虚构之物”。作者坦坦荡荡地宣布虚构的“特权”、故事的“特权”,正如太虚幻境的门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实,这是人类的童年,或者说童年的人类曾经最热爱的那种故事——是神话又是历史,是传说又是寓言。又是新世纪一个新的十年,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疫病作为开端的十年,如此大动荡大不安的时刻,正是阅读这样故事的最好时刻。
2021-11-21
注:本文已发表于《文汇报》,发表时题目及正文有修改。
《潮汐图》读后感(四):远方搭纸而来
2020年4月,林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流溪》,与此同时,她的第二部小说接近完稿。去年的采访里谈到新小说,林棹将其概括为关于清朝广东和一个女青蛙,她希望新小说对自己来说是足够陌生的。那么,对于读过《流溪》,已收藏南国的地域感和矿石般的语言来辨识小说家身份的这批读者,要如何在清朝与女青蛙之间,在熟悉与陌生之间想象这部新小说?
反而,所有想象因落空而满足。新小说取名《潮汐图》,写作缘起林棹曾偶遇的一幅19世纪中叶的水彩花蝶。历史学家西蒙·沙玛那句“对传统文化的挖掘者总会被突起于日常生活表面的那些东西绊住……引他前往历史的更深处”是对林棹一系列遭遇最贴切的描述。随后,林棹遇到一部粤英词典,一系列中国贸易画,动身游历珠江。双脚丈量的现实和历史不够真确的残片在小说家这里同时交汇,是作品雏形的发端。所谓“潮汐图”,既是两种时空交汇的结果,也是化身潮汐的虚构之物反复冲抵陆地般坚固的记忆淤层,在其真空处植入的一段奇幻之旅——亦是小说要讲述的:19世纪初的清朝,一头诞生在珠江边的巨蛙由此一路游历,先后落脚广州城、蚝镜(澳门)、游增(欧陆帝国),沿途吞食万物与见闻,得到数种身份,抵达一个早已明晰的终点。
1.
虚构之物不刻意掩饰自身的来历,小说开篇第一句“我是虚构之物”便干净利落地摊了牌。“我的万能创世主——我的母亲,一九八一年生在省城建设四马路某工人新村”(林棹于一九八四年出生在广东深圳),这是小说造物与造物主在纸上初逢,即将对视的时刻。“母亲睁开巨眼”,虚构之物从纸上跌落水下,踏上虚构的命运。它被捞至船面,收获第一个名字“大头怪胎”,尚无性别。
此后,“大头怪胎”的每个新名字都将它扣进命运的“每个暗扣”。它被船民契家姐收养,改叫“蛙仔”,被醒婆当作“灵蟾大仙”绑上船桅,保珠江渔民风调雨顺。它偶遇H——来自苏格兰的博物学家(他的身份之一),被捉去广州城外判定为“乸”(雌性),第一次拥有性别。它住进澳门的好景花园,被调教成“宠物”,被H编入他的收藏谱系,学名polypedates giganteus。它最后的落脚点在欧陆帝国,先被取名“巨蛙太极”关进帝国动物园,后成为“湾镇巨蛙”,与一名博物学教授、一只雪达犬度过余生。
当巨蛙的尸体冰封后寄出,随冰块一同消失,巨蛙结束飘零的一生变得自由,再也无法被命名和占有。林棹对巨蛙命运的书写带有哀怜的成分,哀怜一个独特的物种在各色人物手中如何降格为财产、奇观、活标本等等。但这份哀怜并不能覆盖巨蛙命运的全部,人试着从巨蛙的脊背上识别一张藏宝图或一部自然史,巨蛙也没放过用双眼“捉住”人,“我被梦着,我也梦着,一如我被看着,我也看着”。巨蛙看一种“浸润南北、通润东西”且“熔化万物又晶化万物”的时间,巨蛙既在时间之中,也在时间之外,它的存在成为永恒去见证周围的人与物出现再消逝。这样来讲,原本的虚构之物反而拥有了坚固的肉身,从历史虚无的浪潮中吞食并保存不复存在的事物。
读林棹的小说会想起J.A.贝克的《游隼》,作者在英格兰的土地上追踪游隼,幻想成为游隼用超越人类经验的眼光观看世界。《潮汐图》自然可以当作林棹对这种眼光的想象和再现,万物也都在巨蛙的眼光中倒转。于是,不再只是“他舔泥”,“泥也舔他”。风不再吹过,“风又咬旗,咬紧了甩,甩出猎猎声响”。珠江“年纪尚幼,它的愤懑就未受重视。珠江游,一味向东”。奶牛看刚出生的孩子,“亲吻他们,看他们如何向世界投去好奇、探问的第一眼”。诸如此类对万物视角的书写,未尝不是织就一张视线缠绕的密网,引我们低头、附身,随每一条不同的路径向世界投去”好奇、探问的的第一眼”,以物的眼光重新“捉住”我们自己。
2.
小说《流溪》里,林棹写一种“弯弯绕绕”的叙事,主人公张枣儿口述的前半生变得虚实难辨,分不清哪部分是她亲身经历的,哪部分是她臆想的。《潮汐图》也要经历一番关于虚实的揣度,尤其小说写到博物学家、夜的主人H面向众人讲一段自己创作的巨蛙的来历,听众里的“你”开始怀疑眼下的一切并非现实,“你开始怀疑你和他们、它们一样,只是主人即兴虚构、日出即化的角色。你被这个念头吓破胆,扔下早就喝空的杯子不辞而别”。
听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都在故事与现实的夹缝间摇摆不定,那么,所有巨蛙讲述的经历也就不再能经受目光真挚的一瞥。既然H可以凭空创造巨蛙的来历,巨蛙讲述H在苏格兰的童年、研究博物学的经历,以及他与一头大象悲剧的遭遇未必不是巨蛙创作的。
意识到这点,林棹的小说表露更复杂和迷人的质地。有金红巨眼的母亲在天空的一角俯瞰巨蛙和它的世界,巨蛙习得母亲虚构的能力,在它的世界俯瞰另一个世界,世界与世界交错,投下变幻的影子便长出新的故事——并非唯一也并非最后的故事。
小说里,巨蛙与画家好友冯喜去黄埔望大船,讨论海的那边是什么。再次见面时,巨蛙与冯喜在澳门夜游,冯喜告别巨蛙,搭一艘大船出海。海的那边是什么,冯喜心里有答案,要亲自去看一看,“实情他是知道,一切故事终要脱离大地、落出去变做大海的。所以他不顾一切舂入大海,与故事汇合;他是要活作一个故事,要做千万故事一份子、永恒流传”。
故事成为人物最长久和可靠的归宿,恰如林棹将巨蛙放进《潮汐图》。明白了肉眼在彼此逼视时的受限,巨蛙甘愿将冯喜、或者说任由冯喜脱离陆地(现实)的命运,走进故事的大海,因为未知,他的存在就有了无数种可能。他的归来最近可以“相距一小时”,最远可以“相距一次日出和一次日落”,这样新的风景、新的世界,是巨蛙为他预备好的。而在巨蛙的大海上,“我亲爱的远航人不会遇见更坏的事了”。
从《流溪》到《潮汐图》,林棹看待世界的信条之一似乎都借《潮汐图》里那个给巨蛙讲故事的女孩点出:“在这人世间,除了故事,我们一无所有。”联想某次对话里林棹提到的一个基本观点,“一切都是虚构的”,再回到她作为小说家的身份——如果存在一种求真的极限,在林棹这里或许能找到虚构的极限。故事身穿层层虚构的外衣,故事生出更多故事,这样的故事存在,难以被讲述——至少难以被一次性完整地讲述,于是故事就也是自由的了。
3.
是否存在“小说家的自觉”这类说法?
小说《流溪》里,林棹首先让读者惊异、惊喜的是她矿石般的语言。林棹极少限定一件事物出现在读者眼前的面貌,那幕奇异底片便是“玫瑰色沁着温柔的绿、愁惨的蓝、雌性的酒醉的黄,梦游的云絮贴着海平线走钢丝”。这并非林棹出于对语言的迷恋,没有节制地将其缠绕在事物身上,一如植物塑造了《流溪》现实以外的维度,语言在此形成另一种维度。所谓“小说家的自觉”,或许是意识到事物无法被语言单一地描述和占有,主动回避精确、果断的观看需要,尝试了解并想象它们存在的多种面貌。
来到《潮汐图》,林棹延续了这份“自觉”。巷道“极窄的,回环的,令人安乐,令人厌倦”。明娜出现时,“她是蛮石山、大泥河、烫的沙、深深林薮。她是四种颜色。她的眼睛是埃及的,下巴是印度的,她有欧罗巴的、牝牛的肩线。她是四面八方。是一丸珍珠,被厚厚的棕油含住”。巨蛙自述的语言随地域的改变而改变,从珠江两岸的粤语方言到澳门的国语官话,再到欧陆帝国的翻译腔,在此,语言的流变也再现了江水与故土中滋养的感官和筋脉怎样消退。
另外来讲,这份“自觉”或许可以等同于“自省”。在写到巨蛙和众多异域动物被关进帝国动物园,巨蛙看自己周遭的“新狱友”,“雪下着,世界簌簌发响。丹顶鹤长颈打结死结,细腿几乎拗断,痛苦地啄尾羽,彻底发狂”。对痛苦的观看随即引发巨蛙内心的自省:“我是否有罪,假如此刻我被他人的大雪感动、在异域新知中尝出欢愉,我是否有罪假如我以囚徒之身尝过并承认这确是人间欢愉之一种?”
巨蛙的自省是否可以看作林棹的自省?进而是否可以视为林棹对写作伦理的疑虑?在亲历一种现实,叩问模糊的过去,落在纸上的虚构世界还能否心安理得地安放欢愉?——来自写作的欢愉。由此,我想到《潮汐图》里最真挚同时最危险的一幕,巨蛙为了帮它的船家养母,沉入海底寻找货物,它看到——
海底更暗。我向大船尸骸去。它不再是大船尸骸,而是变乱的签文,永失解签人;是所有被母亲剔除的定语的漩涡,是折断的腐烂的段落的渊薮。我命运的线索发着噗噜声一串串升起,我不复存在的注脚浮游,废稿碎成粉末,错谬的标点摆荡似鱼群,词条被海沙深埋。我浮上水面换过一次气。我再次下沉,向母亲幽暗的髓海,向打死结的经纬线、弯成穹隆的甲板和死神的旌旗,向蓝蔼蔼幽灵宫殿。
这样的海底,藏着巨蛙虚构的来路,也有母亲、造物主、小说家林棹与自觉、自省周旋过后的折损与消耗。纵使《潮汐图》有如此多的维度供读者打开、进入,但只有一种维度——大海的维度,只有一种方式——下沉的方式,允许读者短暂地看一眼小说家的残影。
至于“远方搭纸而来”,也就变得可以想象。远方绝非轻易地搭纸而来,远方经历揣摩,想要尽好地搭纸而来。《潮汐图》实现了尽好。
原载新京报,此处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