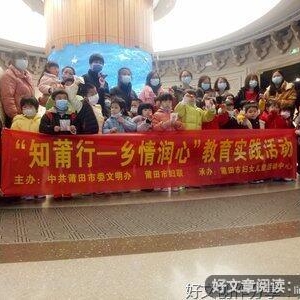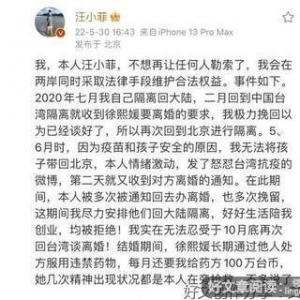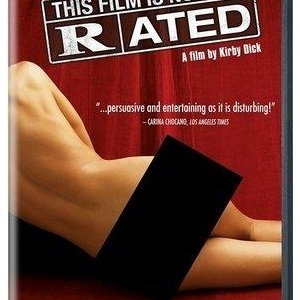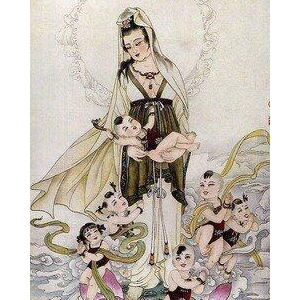我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的。
到村里不久,就赶上了农历新年,也是就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了。
农村不像城市,没有星期天和公休日,特别是农业学大寨期间,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干活,庄稼收了,还要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除了下雨,每天都得出工。但春节不一样,劳累了一年,过年的时候得好好歇歇,“吃点好的”。
那时的农村还相当穷困,常年不够吃,平日里窝头咸菜能吃饱就是好的。但老话是“穷年不穷节”,再穷的日子,过节不能马虎。
一进腊月,男人们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出着工,女人们却早早就忙开了,要拆洗被褥打扫房屋,要为全家老少每一口人都准备出新衣新裤,包括脚上的新鞋。这是一项大工程,平日里要抽空衲好鞋底,要把不能再穿的旧衣服拆洗干净,备成新袄新裤的里子。
这还不算,还要蒸馍炸糕,把正月里的主食准备出来。先要一笼笼的蒸馍,蒸好后晾掉水汽,一层层码进缸里,到时随吃随取。糕也一样,山西炸糕用的是黄米,磨成面和好后先要上笼蒸熟,再趁热揉成一团,揉好后揪成一个一个的剂子压扁,可直接炸,也可在里面放上枣泥豆沙之类。炸成金黄色时捞出,一层层压入小一点的缸中,也是随吃随取,但吃前一定得上笼蒸透,否则硬得没法吃。
杀猪杀羊是年前最热闹的时刻,杀好后队里按人头分配。平日农民的饭桌上是见不到肉的,肉领回家后要按照不同的用途分类处置。羊肉可以剁馅包饺子,还可以汆丸子;猪肉的做法就多了,村里一位公认的能人很得意地“教”过我怎样将二斤猪肉做成八个肉菜:扣肉,咕咾肉,过油肉,红烧肉……不一而足。对于当时的农村,谈论吃食,谁吃过什么,一种东西怎样吃又怎样做,都是极有吸引力的话题。
我和一些知青则被村民们纷纷拉到家里,为他们题写春联。
年就在这样的期待和准备中一天天临近了。
知青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节前就有人被“电报”叫走。那时回京要跟队里请假,一般是家里拍个“急事速归”的电报,虽然都知道是个借口,队里也就准了。临到年根,队里的知青大多还在,我们仍像平日一样每日出工,不可能也无从像农民那样准备过年。
记得除夕那天,十几个知青还商量着晚上吃点什么,农民们早早把我们分别拉到各自的家里,说早就准备好了,一定要去家里吃年夜饭。
我去的这家有四口人,大叔大婶、未出嫁的女儿和小儿子。一进门炕桌上已摆满凉菜,有拌粉条,土豆丝,炒豆腐等,中间是刚刚点上火的火锅,灶上笼屉里热着蒸馍和炸糕。大叔说我是城里来的“大学生”,坚持把我让到炕桌的“首席”,我坐好后他坐,小儿子才跟着上炕,大婶和女儿一边一个侧在炕沿,并不正经吃,要忙着端菜上饭。就着烫好的酒吃了一阵凉菜,火锅沸腾起来,掀开盖子,锅底铺着白菜,依次一层层码放着炸土豆、粉条、肉块、炸豆腐、肉丸子,咕嘟咕嘟地冒着气。
这就是当地农民待客最隆重的菜式了。
我们边吃边聊,大婶问我家里有几口人,父母现在哪里;那时我的父母正准备下干校,妹妹刚在工厂上班,未成年的弟弟去了内蒙。我据实告诉他们,一家人边听边叹,说“可怜一家人分了好几处”,又说“你们这大过年的也回不了家。”我忙解释,是我自己想留下来在村里过年的。大叔又信又不太信地点点头:“既来了,就安心过,哪一方水土也养人。”我便不再说明。
除夕后半夜起,村里零零星星响起鞭炮。那时的农民还很穷,能买百响一挂的小鞭就很不错了。燃放前先将编起的炮捻解开,一个一个的点,孩子们成群结队地从这家燃到那家。大年初一,看谁家门前的炮屑多,说明谁家来年的运道好。而这炮屑,初五之前是不兴扫掉的。
由于大年三十睡得太晚,我是在初一半前晌才走到街上的。猛然眼前一亮,但见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喜气洋洋地立在街口,每个人都一身新袄新裤,包括脚上的新鞋。这使还是平日劳动打扮的知青们很是乍眼。去家里磕头拜年被当做旧风俗早已禁止,人们就在街口互道过年好,问候的同时也用目光彼此打量,看谁家的新衣最合体,谁家的花袄最漂亮。从这儿就能看出谁家的日子过得好,谁家的女人能干。
我从小到大自然已过过不少年,但那个年让我感觉特别新鲜,也是我至今印象最深的“年”。那在眼前晃动的新袄新裤,那冒着热气香气袭人的火锅,都成了我对“过年”最形象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