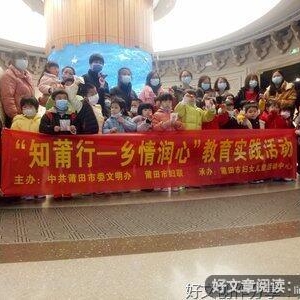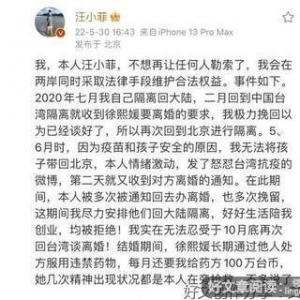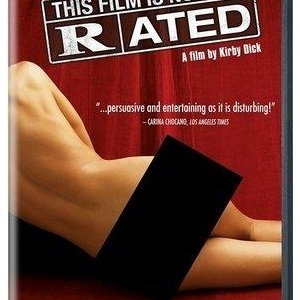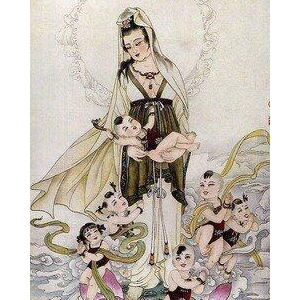我十一二岁时,常去家乡东头的老井上去挑水。
那时候,全村几百户人家,只有两眼人能吃的甜水井。我们家住村东头,吃东井水,井很深,约四五丈深。井口到井底都是用青砖砌成。井口用几块长石条横卧砌成。井口四周竖立着几个木滑轮梯架子。井台儿下面——北面和东面放着几个长条形石槽,供乡亲们饮牲口,或妇女们洗衣服用。石槽外围是空地,北面通东西大街,东连戏台子。
挑水时用小水桶拉水。有劲儿的青壮年,拴一只大水桶,拉两次就够一挑了。井绳很粗,我的小手刚好能攥住。拉水时,要浑身使劲儿,用力甩胳膊,两手不停地交替着一上一下地拉着木滑轮滚动。双腿叉开,整个身子重心向后,屁股随手交替拉井绳而用力左右扭动着。拉上来的井绳随手的交替,在木梯架下的大石头尖儿一圈儿一圈儿地盘好。这样井绳不沾水,用起来不滑,能保证挑水人的安全。
冬天,十几岁的孩子去井沿上去挑水是很困难的,也比较危险。因为挑水的人不断,从早上天刚亮到傍晚天快黑,哪阵儿都有人去井沿儿上挑水。井台儿上,滑轮梯架下经常是滴水成冰,脚下溜滑。当水桶吊上井口时,要一手伸出去,斜着身子抓住井绳的一头儿揽过水桶。此时,脚跟儿一定要站稳,不然就会重心前倾。如果抓不住井绳,或抓不牢吊上来的水桶,水桶就会带动井绳下坠,而木滑轮飞速地倒转,连水桶带井绳将一齐掉入深井里。更危险的是,如果站不稳脚跟儿,水桶下沉带起井绳霎时间井绳就会把人带向井口边沿儿。
十几岁的孩子去井沿上挑水的并不多,家里大人都不放心。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父亲在县上工作,生产队上的农活和家里大小事儿全靠母亲一个人承担。母亲经常是天刚亮就下地,除过吃两顿饭,到天快黑时才回家。有时候,奶奶做饭或热猪食时急着用水,不能等母亲回家时再去挑水。那时,每天放学一回到家里,自己先望望水缸里的水有多少。如果说水少不够用,放下书包就去井沿儿上去挑水。由于自己年龄还小,个子还没有长起来,扁担搁在肩上时,那扁担钩儿勾起的两只水桶还碰地呢。我只好把扁担钩儿往扁担上环绕一圈儿。我根本挑不动两桶水,只能挑两个半桶。开始挑水时,一迈步左右摇摆,像拨浪鼓似的,担子压得我呲牙咧嘴。
当年,每当我去老井上去挑水,只要二弟知道了,就会马上追我到井沿上。我们俩一块儿往上拉水,我们弟兄俩用长扁担抬两桶水。蹲下弯着腰往起抬时,二弟个子高,他总是把扁担往前捅一捅,或者把扁担钩儿往后拉一下。我在前,二弟在后,扁担压得像弯弯的小船儿,两头儿在我们的肩上翘起来。抬着满满的两桶水,我们迈不上家里大门的台阶,只能放下扁担一桶一桶地往水缸边儿上挪。挪到水缸下边,喘口气儿,我们兄弟俩再一齐用力,将水桶抬到水缸沿儿上倒水。一趟又一趟,直到水缸的水满,清凉的井水在水缸中滴溜溜地打旋儿。
而今,我们家乡的老井早已封死,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但是,那一口永恒的老井将永驻我的心中,那清澈透明、微甜爽口的井水将时时滋润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