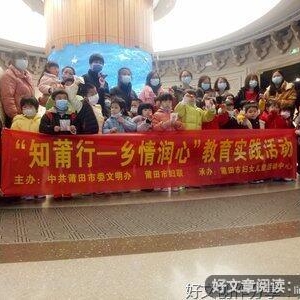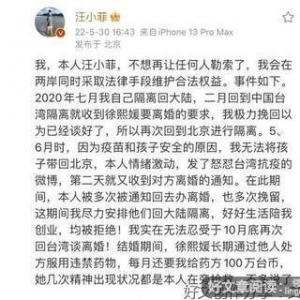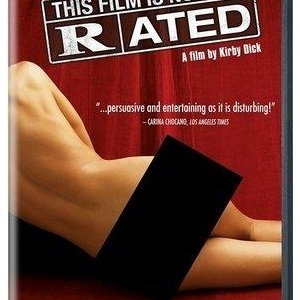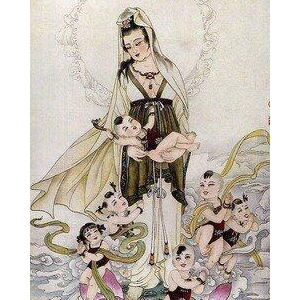东北的冬天冷的厉害,这里的人常说:“吐口唾沫还没等落地就已冻成冰坨子。”,当然,这有些许的夸张。但东北冬天的寒冷确实很难让人消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北风似乎夹杂着银针在呼啸,把人们的脸蛋刺的生疼。如今一入冬家里就会用暖气取暖,屋里和屋外简直就是两个季节,屋里惬意如春,屋外寒气逼人。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家里是用火炉子来取暖,到夜间的时候,屋内的余温殆尽,凉气爬上了炕沿往人的被窝里直钻,把人冻的蜷缩着。
东北的冬季是昼短夜长,天没放亮,大人们就已经睡的大醒。那时父母总是早早的起来生炉子把屋子烘暖,而我还在偷睡着懒觉。等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见遮在窗外的天空篮莹莹的,上面缀满了点点星光,就像遥远村庄里的万家灯火。母亲催促:“起来了,老儿子,校车快来了。”我犹犹豫豫的穿好衣服,慢慢吞吞地爬下炕,在母亲的唠叨下洗漱准备吃饭。扎好红领巾之后我颠颠地跑去厨房,当我拉开门的那一刻,厨房里的水蒸气瞬间接纳了我,水蒸气密的不透风,只有白炽灯撒下的泛黄光线与水蒸气纠缠起来,笼罩在我脸上时感觉暖洋洋的。我看不见爸爸、妈妈站在什么地方。我踩着小碎步摸索走着,一头撞进了爸爸怀里。爸爸将房门开了一道细缝,顷刻间,寒风顶着热气视死如归的涌进屋内,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水蒸气也顿时落荒而逃。原来锅里煮着爸爸妈妈早起包的饺子,饺子被烫的肆无忌惮的翻滚,恍若对屋外的寒冷独一的向往。“饺子好了,吃吧,老儿子,吃饱饱的,校车快来了。”母亲一如既往地唠叨着。
吃罢那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我登上厚厚的棉鞋,背上爸爸收拾好的书包,爸爸又把棉帽戴在我的头上。就这样我走出家门。脚下踏着厚厚的积雪,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在冰天雪地之间踏出悦耳的音符。头顶上空的晶莹雪花在胡乱的飘浮,似乎为那悦耳的音符伴起舞来,那冰冷苍白的冬天也显得生机勃勃。当我踏上校车的那一刻,我的奏乐就谢幕了,但余音仍冲向云霄,雪花正舞的兴高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