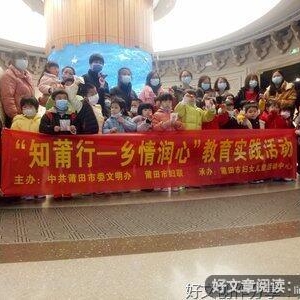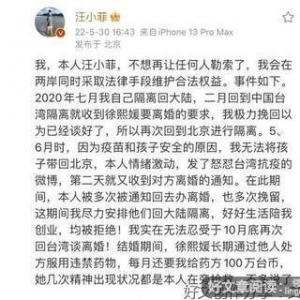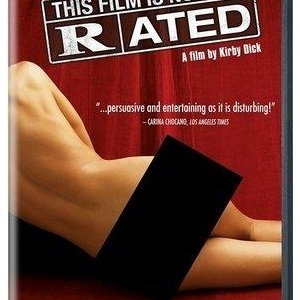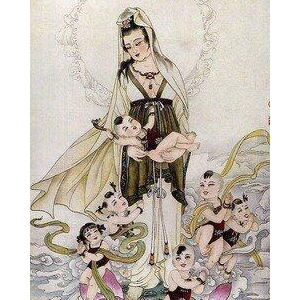我站在医生们难以察觉的角落里,看着医用无影灯发出的惨白光线打遍我的全身,平铺在我肤体之上的冷艳白光里掺不得半点肉色,身上插满了用于监测生命体征和输送药物的各种管子,我好像一个木偶一样任人摆布。医生们手忙脚乱而又井然有序的传递着手术刀、剪刀、镊子、血管钳、止血棉。手术已经进行了二个多小时,手术医师眼睛不眨的盯着我这个血肉纷呈的身躯,生怕割错了一个细胞。不知是过度劳累抑或精神紧张,额头沁满了汗珠,一名女护士频繁的替他擦拭。另一名护士心无旁骛的盯着心电监护仪屏幕上时断时续的波浪线,仿佛是她的生命与这台暗示生命存亡的机器紧密相连。目睹他们如此用力的挽救一个陌生的生命,我似乎知道了生和死之间的区别,生者时刻逃避着死亡,但每天义无反顾且争分夺秒的向死亡冲刺而他们却浑然不知;死者一旦被死神眷顾,无论如何都再不会卷土重来,走出生命的人将生者搁置在时间里面,让他们向死者默哀。那条意乱情迷的波浪线终于身心具乏的停止了跳动,暗示着我将像一条直线一样,一劳永逸的躺在那里。这时我才知道,活泼的生命不是一马平川而是凹凸有致。那个心无旁骛的女护士声音凄戚的打破了手术室的阒静:“郝男,男,26岁,死亡时间,十点零八分”。这是我在人间草木之上留下简洁而又有力的死亡证明,证明我成了孤魂野鬼,无家可归。
我的那具可怜的尸体被护士们抚推着,在主刀医师的带领下,走出了那扇阻挠着阴阳两隔的虚掩之门。当门被无情的推开,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那眼底发红,面容憔悴的母亲,和倚墙站立,神色慌张的父亲。母亲的双腿仿佛被铅球拖拽着步履艰难的往前走,母亲好像用那死气呆滞的目光一眼就看见了如盐一样干白的裹尸布之下我那面色铁青的脸。母亲的两条腿瞬间好像两根面条一样软,使整个身体坍圮在冰凉的地面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如黄河决了堤,汹涌而来的嚎啕大哭,泪水在被岁月雕刻的褶皱之间肆无忌惮的横流,哭喊着:“救救我的儿子,没死,让我替儿子死,求求你们,……儿子”。这无力的哀求之声在白色的长廊里相互折叠,难突重围。被生活尘劳垂压的有些许伛背弯腰的父亲,面色苍白的望着他的妻子,父亲没有像母亲那样显现声嘶力竭,如入熔炉之痛,他的内心被巨大的悲伤锁扣,苦涩的泪水流向胸中脉动的地方,熬淹心田。父母的悲伤程度,我无法用比喻去描摹,父母痛失子女的伤悲只能去用作比喻。我是脱离了皮囊的魂魄,面对眼前苦戚泛滥成灾的场景,展现不出任何的感情,只能平静的观看着,我看到了父母的悲怆不止于此,他们失去唯一的儿子之后,等行将就木之时有谁能伏床递药,等百年之后,又有谁去坟茔插香。生活的强大之处不是庞然大物的招摇过市,而是这细微之处的脱颖而出。
从事一项自己喜欢的工作,和自己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