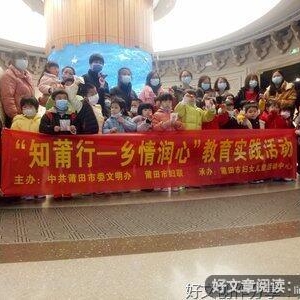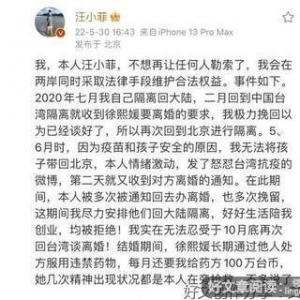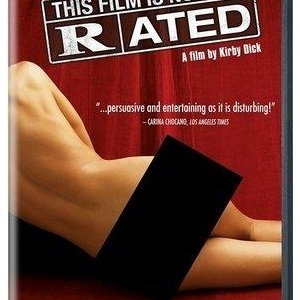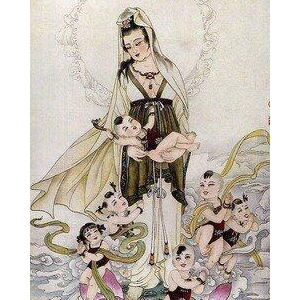袁午把手机放回口袋。那些砰砰作响声音消失了。
父亲停止了呼吸。在关掉电视的那一刻就已经…… 或许比那会儿还要提前一些。
来不及了,叫救护车已经来不及了。
袁午发觉自己许久没有端详过父亲的面容。
眼睛和嘴巴都自然闭合,没有痛苦,没有留恋。黑色的棉外套是若玫买给他的,穿了许多年,褪色领口好像覆了一层薄霜。
没有父亲,袁午无法独自生活下去。
现在该怎么办?妈妈,我该怎么做呢?
那个炎热的夏天,母亲躺在冷气柜里,柜壁内侧的两排小孔中缓缓流出白烟,白烟融作一片,成了一条蠕动的棉被。
冷气柜放置在丧礼大厅的角落,就像一件普通的家具,没有人关注。客人跪拜的对象是烛台中间的黑白遗照。
尸体和照片,哪一个才是母亲呢?一旦失去生命体征,反而是一张硬纸来的更实用啊。
照片忽地晕染上色彩,母亲的嘴动了起来。说的是什么?完全听不见啊,太吵了。音箱里播放的诵经声在脑中无限循环起来,还有若玫的哭声,木鱼敲打声……
小腹间一阵绞痛袭来 —— 不能留在这里。去找小红吧,现在就去!
袁午推门而出,想起身上的钱包几乎已经空了。
父亲的口袋里有钱吗?要把手伸进父亲胸前的口袋?没有这个必要。这么长时间没出过家门,钱放身上没有意义。
餐厅与厨房的隔柜上只有几枚硬币。他走进父亲的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几盒药和一副老花镜。另一个床头柜的抽屉被锁住了。
环顾四壁,最显眼的就是那个衣帽间了。刚来看房时,袁午就对衣帽间心生好感,原木色的柜格大小独具,三面环抱,让人感到安心。如果能当成房间住在里面就好了。
拉开柜门,摁亮筒灯,父亲洗干净的几件外套和裤子挂在一侧,袁午掏遍所有的口袋,什么也没找到。
退出衣帽间,看到床上高高蓬起的枕头,剥下枕套,里面却只有一个枕芯。袁午失望地坐在床沿上,马上意识到了什么,抬起床垫一角,终于发现一叠现金。粗略一数,大约有五千元,是平整的新钞。
袁午在通往 「大友」 的浓雾中疾走。刚刚走出小区时,还有三三两两的汽车出现。其中一辆贴着他的身体掠过,像瞬间遭遇横风似的扭动了一下。隔着紧闭的车窗,还是能听见司机尖叫了一声。走到半道,这个世界就只剩下路灯了。
路灯成了悬空的光晕小球,连灯罩和灯杆都难以分辨。灯光的投射距离明变短了,留在地面的光圈比平时小,边界也更模糊,相邻的路灯之间出现了完全的黑暗。
是不是走错方向了?他有点想回去,然而回头一望,前后的景象毫无分别。还能回去吗?现在回去,回到一个小时以前,抢下父亲手里的酒杯……
不能再喝了。
或许只要说这么一句,父亲就会放下酒杯。为什么一直沉默呢?
前方的上空总算出现了红绿交替的弱光,是交通信号灯,已经到路口了,两旁的樟树枝杈呈现出袁午熟悉的形态。穿过路口再走一段,拐进一旁的小巷,「大友」 的入口就在那里。
卷帘门拉上了三分之二,白光从下面撒出来,在水泥地上铺了一层银粉。袁午猫腰钻进去,感到通体温暖。里面是七八平米大的小隔间,作为接待使用。小红正挂着耳塞面对电脑屏幕。
「唉?怎么这会儿过来?真是难得。」 她拔掉一个耳塞,从前台后面探出脸。
袁午觉得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一看墙上的钟,居然已经九点多了。除去吃饭和路上的时间,自己在父亲的尸体旁至少站了一个小时,那时却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怎么了?」 小红皱着眉笑起来,「被人追杀呀?」
袁午惊觉自己呼吸急促,他精神一凛,马上摇头。
「打牌吗?」 小红拔掉另一个耳塞。
袁午点点头,摸索上衣内袋。刚才走的仓促,一大叠现金卷成一团放在一起。他只想抽出五张,颤抖的手指却难以拿捏,纸币像撒落花瓣一样漏出来。
小红连忙绕过柜台,蹲下身帮他把纸币拢在一起,幸好没有别人在场。
「哪来的钱呀?老实交代。」 等袁午把钱重新收好,小红故意贼声贼气地问。
袁午低下头,答不上来。
小红叹了口气:「去吧。」
掀开角落的门帘,里面就是麻将大厅,骨牌碰撞的声音和人群的嘈杂声让他松了一口气。此时的 「大友」,就像风雪漫天的荒野中一家孤立的客栈。
烟雾缭绕的包厢里共有六张牌桌,两张空着,排风扇在天花板上嗡嗡作响。袁午独自坐到空桌旁,一个五十来岁的秃顶男人马上兴冲冲地坐到对面。
「玩梭哈对吧?」 男人把自己的塑料水杯放在桌上,里面的茶叶和水面一样高。
袁午认得他,但不知道名字。牛仔夹克褪成了浅灰色,领子像薯片一样翻卷着,夹烟的手指满是污垢,让袁午想起小时候路边的修车师傅。
玩了几把,袁午始终无法像平时那样集中精神。他连牌面也记不住,输赢都是对面说了算。手边的筹码忽高忽低,对方大概也没有做手脚。
父亲仍然坐在那里吧…… 一定是的。
围观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也可能一直就是那几个人在牌桌之间游荡。男人不时抓挠着自己鸟窝似的头发,但无论怎么挠,杂乱的形态始终保持一致,他的头发摸起来应该和棕绷差不多。
「要夜宵吗?」
耳畔传来小红的声音,袁午努力将视觉焦点落在她脸上,周围的声音清亮起来。
他摇摇头,看着桌上排成一条线的纸牌,感觉像突然从水里探出脑袋。
当前这一局已经进入最后一轮投注,十张牌都发完了。袁午的牌面上有一个七对,他记得底牌是也是一张七点,而对面全是单牌,最大一张是九。
男人试探性加了一注,正蜷着一条膝盖等待袁午回应。
袁午慢条斯理地将所有筹码推到桌面中央。对方大不了是个九对,这局必胜。
男人看傻了眼,支在椅子上的脚后跟向前一滑,整条腿弹了出去。
筹码片倒塌的声音吸引了邻桌的看客。
「跟啊,别怂!」
「眼睛一闭冲了,又没多少钱。」
这些人都熟悉袁午的牌风,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绝不会孤注一掷。他们围成一圈,探头弯腰,在牌桌上方形成一个半球,都等着看那男人的好戏。
男人放弃了,他大骂一声,抄起杯子从人缝中挤了出去。围观者们嘘声四起,水花一样散开了。
袁午默默捞回筹码,顺手翻开自己的底牌。
不是七点!
记错了,七点是上一局的底牌,也许是再上一局。如果男人跟注,自己就输了。
一阵燥热涌上脸颊,就像刚刚撒了个弥天大谎。他看向四周,人们纷纷沉浸在自己的或是别人的希望之中,已经没有人关注他了,没有人知道这张底牌不是七点。
这种程度的心理战,在牌局中是司空见惯的小伎俩。但打牌的人是袁午,袁午不会耍这种伎俩,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若非如此,对手也不会果断投降。
那么,只要永远不翻开那张底牌就行了。这样真的可以吗?
「今天运气不错呀。」 小红收回筹码,从前台下的抽屉里取出现金递给袁午,看起来是真心为他高兴。
袁午接过纸币塞进口袋,也没看多少钱。
「我爸他,今天回老家去了。」
「嗯?」
「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晚上还过来嘛。」
「哦 ——」 小红作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这么说,以后晚上也会常来?」
「到时候看吧。」 袁午盘算着接下来的行动。
「你今天脸色不大好。」
「有吗?」
「也对,整天泡在这儿,脸色能好才怪。」 小红为自己的结论点了点头。
刚才输掉对局的男人撩开门帘走过来,手肘支着前台。
「我说你么,还是把头发放下来好看,有女人味。」 他笑嘻嘻地掏出一叠对折的纸币,抽出十五元放在桌上。
「关你什么事?」 小红白了他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两包廉价烟,「我剃光头也跟你没关系。」
「那是,老板喜欢就好。」
「去去。」 小红赶鸡似的把他轰了回去。
顾忌到老板的威慑力,这里的熟客对小红有所垂涎的虽不在少数,可大多也只能像这个男人一样,止于口舌之快。
「大友」 的老板是镇上的头脸人物,据说本行是经营贷款公司,开设 「大友」 是为了孕育市场,类似的网点在全市还有好几家。在这里,除了小红之外,还有一批人只看不玩。他们是老板手下的放贷人,同时也负责维持现场秩序,是 「大友」 真正意义上的掌控者。他们终日在数十张赌桌之间游荡,发现有人输净口袋,便上前兜售月息惊人的贷款。袁午败光家产之后一直囊中羞涩,也就没有受到过这批人的照顾。而小红,实际上只是个兼顾端茶倒水的收银员。
老板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关于小红和他的关系,这里的人整天在念叨,但谁也说不清楚,于是化繁为简,归结为 「情人」 了事。小红由此获得了一道屏障,她自己也就懒得解释。
——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也没什么不好。
小红曾对袁午这么说过。言下之意,她和老板并不是那种关系。
「你…… 有话要跟我说吗?」 小红赶走男人,看袁午仍站着不动。
「没有。」 袁午慌忙收回眼神,「也不是……」
「什么呀?」
「最近可能要忙一阵子。」
「有项目做?」
「嗯,挺棘手的。」
「那就好。」 小红凑上来小声说,「在这里呆久了,人会烂掉的。」
「你说这样的话好像很奇怪。」
「奇怪的是你吧,来的比谁都勤快,偏偏从头到脚都不像个赌鬼。」
「怎么样才像赌鬼呢?」
「就像刚刚那家伙。」
这时连续有四个人走出来,大声讨论着惊心动魄的牌局。其中两人找小红退筹码,粗暴而又不自知地将袁午隔开了。
见小红忙于应付,袁午便转身离去。
雾气丝毫没有消散,袁午低着头,步履迟缓地朝住处走去。这条路他已经走过上百遍,闭着眼睛也不会迷路。
接下来,要无声无息地处理掉父亲的尸体。
—— 父亲已经离开人世。这条信息写在牌面上,但只有袁午一个人看见,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张牌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