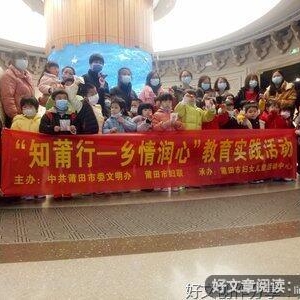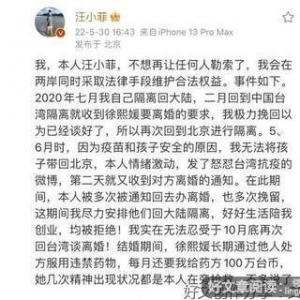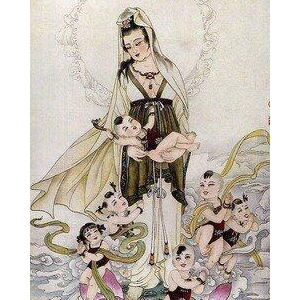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是一本由[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78元,页数:7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读后感(一):天才的赞歌:《席勒传》
在评论这本书之前,想先聊一下为什么会来读这本书。很多人通过作品来了解作者,随后会阅读作者的传记,我恰好是这类读者。大学学的专业是德语,有一年同学们想组织一起表演一个节目,最后选定的形式是舞台剧,选定的剧目碰巧是《Kabale und Liebe》:阴谋与爱情。其时我对席勒依然是处于毫不了解的状态,惭愧,大二专业生一点也没长进;虽然最后排练无疾而终,但增进了同学情谊,也打开了了解席勒的窗口,但依然实在围绕着他大打擦边球,这次是通过德国文学史专业课中的Sturm und Trank... 错了 Sturm und Drang:狂飙突进,了解与歌德同时代的席勒,如同魏玛歌剧院广场上的铜像一样,代表德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比肩的双峰、手握桂冠的诗人。
再次读到席勒的作品已经到了多年以后,翻看商务印书馆的《三十年战争史》,赫然看到作者是席勒,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中文序言中深刻地指出,作者没有犯同时代史家的通病,将德意志国土上肆虐的战争看做是王朝公国战争或者宗教冲突,而是点出即使像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这样貌似师出有名、救民于水火的英主,恰恰是全体德意志人面前不折不扣地侵略者。通过这种表述,让我对作者依然有一种粗浅而且模糊的印象:作者才华横溢、文史兼具、洞若观火。之后就和席勒作品就此别过,不仅《强盗》、《华伦斯坦》即使是《欢乐颂》都没有完整的背下来,回想起来真是可惜。
恰好看到德国谐星Matthias Schweighöfer演绎的席勒生平电影中,席勒身穿制服,要从军队中脱逃;在看到阴郁的Florian Stetter演绎的青年席勒“周旋” 于两姐妹间,我也会产生疑问,席勒的一生真的像这些200年后的电影一样,如此困顿、窘迫、浪漫而又毋庸置疑的辉煌吗?
解答这个问题,于是就到了现在:席勒传——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带着问题找答案,也许是最好的方法,而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分段切入,前后扩展,也许也是一种帮助读者快速沉浸如时代和作品的方法。我仅谈谈几个让我映像比较深刻的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我熟悉的几个历史片段:
一、席勒生活的时代
伟大的诗人年少时生活在符腾堡公国,作为传统的亲法和天主教势力范围,公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升格为王国,在普法战争中才为德意志统一事业出力。席勒作为廷臣之子,年少时不仅有着成为神职人员的梦想,但最终不得不屈从于恩主的安排,进入了符腾堡公爵的宫廷学校。看到了公爵的政绩不由一笑:肆意践踏法律,动辄将臣民打入大牢,如此刚愎之人虽然在腓特烈大帝的宫廷接受教育,却丝毫没有熏染这位君王的风范;增加赋税、强征劳役、整租(贩卖)士兵给英法以支撑铺张堪比小凡尔赛的宫廷,军队还不堪一击,丝毫不及大帝另一堆铁粉黑森系公国军队。看来年轻席勒活在绝对专治与开明专治之间,虽然逃过了在腓特烈大帝麾下在刀尖枪口火线前舔血卖命,但也逃不过一个腓特烈半吊子徒子徒孙的专治统治。虽然他日后在写作某些作品时惦记的是不给自己的领主丢脸,但最终还是成了服役期间脱逃的“逃兵”。
二、席勒与莎士比亚
席勒在早期医科学习的同时已经熟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能够背诵章节。在《强盗》首演后,席勒的评价是剧中的角色都是“按照莎士比亚的风格”构思的。恶棍弗朗茨“是个物质主义者,既然自然待他不公,那他又为何还要相信自然的善意?” 我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也就局限于劳伦斯·奥利佛的几部莎翁电影和描绘莎翁秘史的《匿名者》,于是我直接在这段的旁边备注下了《理查三世》。
三、历史与戏剧创作
历史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玫瑰战争给予了莎士比亚金雀花武士国王们的悲喜剧,也给了冰与火之歌以灵感。历史让席勒着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历史为创作提供了重要灵感,而虚构的想象力无法提供创作所需的长久基石。席勒的历史和戏剧写作相辅相成,在写作《唐卡洛斯》时研究了尼德兰历史,也就觉得《尼德兰独立史》对他的胃口;接下了《三十年战争史》,也就推出了《华伦斯坦》三部曲,《玛丽·斯图亚特》、《威廉·退尔》和《迪米特里乌斯》等历史人物纷纷进入他的创作篮子。
四、戏剧创作与金钱
我们的主人公不断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根源是经济因素,有时写作多部作品只换回1000塔勒对席勒来说不是个很划算的生意;在创作时一边写作一边学习,让学习帮他赚点钱,于是便有了写历史作品吸引更大的读者群的主意;在收到一部作品收益的同时就用其中一大部分支付债务也是家常便饭,正如同在《Die geliebten Schwestern》里看到的一样,席勒也要为了获得垂青,不厌其烦的向未来的丈母娘介绍自己新获得的职位。
五、双峰还是群星
如前文所写,总是将歌德和席勒相提并论,看了才知道其实和赫尔德、威兰德、诺瓦里斯、荷尔德林、费希特、黑格尔是同路人。
书中对席勒众多作品如何诞生都做了详尽的描述,同时也多众多哲学思想贯穿席勒的创作生涯和整个时代着墨不少。席勒所代表的的理想主义脱胎于古典哲学,而他去世后不久,世界即将进入民族觉醒和浪漫主义的新时代。众多看点既留待广大读者探究,也是自己继续重新发现的新起点。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读后感(二):46岁的德意志恒星
当我们谈到德国文学巨匠的时候,很多人首先想起的是歌德,一部《浮士德》足以写成一部人性史诗。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是写出了无数青年人的爱情和迷茫。然而,德意志理想主义的旗手其实另有其人。他就是约翰·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席勒,一位生于1759年11月10日,逝世于1805年5月9日的文学家。尽管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46年,但席勒的影响却深深改变了德国,乃至欧洲。他让这个时代激情澎湃,在歌德、黑格尔、谢林等璀璨群星中熠熠生辉。《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就是这样一本全面展现席勒这位旗手灿烂一生的精彩传记。
书影
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知名学者、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传记大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他通过洋洋洒洒七百余页,借助翔实的材料将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生平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全书分为24章,以时间为顺序展现了席勒的生活和事业。席勒是如何从一个军人的儿子成为文学大家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
作者像
在少年时,对诗歌的热情已逐渐在弗里德里希心中醒来,并与宗教情感结合到了一起。但席勒却不得不进入卡尔学校,这里既是军营,又是修道院和大学。学生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由公爵本人亲自监督。在军校迁移至斯图加特后,伴随着“狂飙运动”的兴起,席勒感受到了激情与活力。席勒在莎士比亚那里发现了宏大的世界舞台,发现了人类命运和冲突的喧哗与骚动。他对人类的最初认识都来源于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随后倾心于哲学,尝试运用分析的手术刀切开人类的头颅,去探索其中是否真有君王的宝座。毕业后,席勒作为军医,仍然进行着写作,《强盗》是他关于反叛的重要戏剧。
席勒像
在目睹了好友的抑郁退学和另一位好友的去世之后,1782年9月22日,席勒逃离斯图加特到了曼海姆,进入流亡生涯。随后前往鲍尔巴赫,开始了新的生活。《阴谋与爱情》等剧作的发表奠定了他的地位,但曼海姆剧院的苛刻合约让他一年得写三个剧本。德累斯顿是诗人的下一站。1787年,在鲁多尔施塔特,席勒与待字闺中的22岁少女夏洛蒂相逢相识,后来,二人于1790年成婚,共养育了四个孩子。
席勒夫人
1788年12月,席勒成为耶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尽管他已经闻名遐迩,但这位副教授却得不到固定的工资。只能依靠拼命写作来维持生计。1791年,席勒得了“伴随着干性胸膜炎的格鲁布肺炎(kruppöse Pneumonie)”。这个病就此伴随他的余生。
耶拿大学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爆发极大地影响了席勒。他在思考成为伟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代人乃至见证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些历史事件触及个人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又应该发生些什么?法国革命的形势使席勒失望也使他深思。人们不能把国家这一块“钟表”先捣毁再发明一个新的,而是必须“在钟表转动的情况下更换转动着的齿轮”。1796年,席勒主动邀请歌德合作,为他主编的文学刊物《季节女神》撰稿,从而开始了两位诗人至死不渝的友谊和对双方都受益无穷的十年合作。历史剧《华伦斯坦》是席勒创作的新高峰。1799年之后,席勒更是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推出巨著,从《玛利亚·斯图亚特》到《威廉·退尔》、《奥尔良的童贞女》和《墨西拿的新娘》,创造了光辉的人物形象。通过《华伦斯坦》和之后一系列剧作,席勒创造了德国戏剧艺术的典范,并奠定了“德意志莎士比亚”的地位。其中《威廉·退尔》因为罗西尼的歌剧而广为传唱。
威廉退尔
可惜天不假年,1805年5月9日,在经受了病痛的长久折磨之后,席勒旧病复发,在忍受了9天的痛苦之后,与世长辞,年仅四十六岁便结束了自己光辉灿烂、可惜过于短暂的一生。死后解剖发现,他的肺已“坏死溃烂,成了糊状,彻彻底底的一团糟”,他的心脏“没有肌肉物质”,他的胆囊和脾脏已肿大得极不自然,而肾“就其本质而言已彻底瓦解,完全畸形”。
席勒与逆境奋斗终生的事迹、高尚的人格以及精彩的作品,使得他始终像一颗明星闪耀在天际,指引着后人前进的方向。这也是这本传记所要传递给我们的内容。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读后感(三):同席勒一起,进入德意志精神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伟大的德国诗人、戏剧家、美学家。一生追求真理、美与自由,德意志理想主义的开创者。
1805年5月9日,席勒英年早逝。人们在他死后解剖了遗体,才发现他的肺已“坏死溃烂,成了糊状,彻彻底底的一团糟”,他的心脏“没有肌肉物质”,他的胆囊和脾脏已肿大得极不自然,而肾“就其本质而言已彻底瓦解,完全畸形”。魏玛公爵的御医胡施克(Dr. Huschke)在尸检报告的最后简短地补充了一句:“在此种情形下,人们不得不感到诧异,这可怜的人究竟是如何活到了这个年纪。”可席勒自己不是曾说过,是精神为自己塑造肉体吗?在他身上,这句箴言显然得到了实现。他充满创造力的热情在身体腐坏的期限之外保住了他的生命。在席勒临终前一直陪伴着他的海因里希·福斯(Heinrich Voß)写道:“只有他那无穷的精神可以解释,他为何竟活了如此长久。”
从席勒的尸检报告中可以读出理想主义的第一重定义:理想主义就是人们凭借精神振奋的力量,活得比肉体所允许的时间更为长久。这是受启发而澄明的意志的胜利。
在席勒身上,意志就是自由的器官。若要问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席勒的回答毫不含糊:意志每时每刻都开启一片新的视野,包含着触手可及的无尽可能——这样的意志怎么可能是不自由的?人们眼前所拥有的可能性虽有限制,但到底是无穷尽的。因此,自由便是开放的时间。
只是与自由意志相关的不仅仅是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更重要的是自由充满创造性的那一面。人们可以依照理念、目的或纲要的规定,影响事物、他人或自我。创造性的自由将某种缺了它便不会存在的东西引入了世界,因此总是在“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但自由又是毁灭的力量,同时可以抵御种种负面的作用,例如肉体病痛的袭扰。对于自然、对于自己身体的本性,席勒总是持一种针锋相对的战斗姿态。身体就是那害你的刺客!因此席勒认为,我们“完全不应将自己受到自然制约的物理状态当作我们的自我,而必须将其视为外在的、陌生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席勒最大的对手与最好的朋友歌德(Goethe)却不敢苟同。他将之称为席勒的“自由福音”,却表示他自己“不愿意看见自然的权利遭到克扣”。
歌德的观点反过来又让席勒觉得不妥。对他而言,自然本身已足够强大,不需其他帮助;人们倒是应该援助岌岌可危的精神权利,确保自由的力量。席勒酷爱自由的冒险,也因此成为18世纪晚期的萨特(Sartre)。席勒的理想主义意味着坚信人可支配万物,而非为万物所支配。他像后来的萨特一样宣布:重要的是从人既有的状态中,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来。
熟悉他的人曾众口一词地说,席勒几乎总是集中注意力、神经紧绷、忙个不停,好奇而警醒,近乎多疑。妻子夏洛蒂说:“现实的一切总叫他惴惴不安。”与歌德不同,席勒对这世界并没有宁静而淡然的信任。他并不觉得有某种仁慈的自然支撑着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得由自己亲手创造!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意志麾下的健将,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里。
难道他的生命从一开始便伴着不幸?他的命运并没有那么糟糕。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位聚少离多的父亲;小市民的环境,倒也并非穷困潦倒。童年的世界几乎像一曲田园牧歌。然而,他之后却进入了卡尔学校(Karlsschule),落入一位时常独断专行的公爵手中。他爱自己的生父,却惧怕像父亲一样盯着他到寝室的君主——直到他公然起来反抗。
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长得太快,满脸痘疹,四肢僵硬,迟钝笨拙,穿着学校的制服就好像稻草人一般。但他并不囿于他的身体,也不喜欢自己的外表,只是在内心涌起莫名的冲动,四下里横冲直撞。他感到自己被掷入大千世界,便用一幅幅蓝图回应;他总是有各式各样的计划,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勉强忍受。他常遇困扰,停滞不前,却倏然挣脱束缚,开始演说,语速迅捷、毫无征兆、滔滔不绝。他的听众很快就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他的思绪飘到哪儿去了。
席勒的激情源自对生活的厌恶。他不得不反复克服这种厌恶,后来又在《强盗》(Die Ra¨uber)中将之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出来。这部天才的作品像一种自然现象,闯入德国既有的戏剧世界;席勒在这出剧中追溯了恶之起源的种种痕迹:他发现了自然的丑闻,即它偏爱一方而亏待另一方,毫无意义、罔顾公正。人们于是被卷入种种不幸与意外,有充足的理由去怀疑生活。这就会产生一种有毒的怨恨。为了那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席勒坚决与之斗争。
因此,他对自由的热情也就意味着一张自己开具的解毒药方。在与歌德的交往中,席勒将会特别需要这剂解药。同歌德的友谊与合作——德国文化史之亮点与大幸——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席勒已认识到:“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致歌德,1796年7月2日)
席勒并不怯于将个体与人类等同起来,而是公开地将爱宣布为世界性的力量。他在年轻时就发展了一种爱的哲学,将古已有之的博爱母题“存在巨链”续写了下去。席勒是自我暗示的大师,他可以自我激励,升入这句“亿万生民,一起相拥”的诗里去;然而,他也会为自己泼一泼冷水,甚至陷入虚无主义的恐惧僵化之中。他清楚无意义的深渊,这也是为何在他世间万民皆兄弟的愿景中,总还能体会到一丝新教徒式的“尽管如此”的无奈。坊间传有席勒式的赌注:我们倒要看看,究竟是精神胜过肉体,还是肉体胜过精神!
席勒将要证明,人们所承受的不止一种命运,还有另一种,也就是人自己。他不能不注意到,自身命运之强力是多么吸引人、多么具有传染力。因此才有他结交朋友的天赋,才有他的卡里斯玛(Charisma)。甚至歌德也被席勒的热情裹挟。最终,席勒让一整个时代变得激昂澎湃。这种激情及其中所诞生出的,特别是在哲学领域,就在之后被称为“德意志理想主义”,而贝多芬则将其谱成音符:“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本书将要描绘席勒是如何打磨自己,把他的人生活成了一部戏、一场演出。在他成名之后,他成了公开的灵魂。他的危机、转向和变化,一幕幕都上演在观众眼前,而他们则满怀景仰与惊异欣赏着这一出生命的大戏。歌德之后甚至将好友身上这种不断精进的特质加以神话:“他当真是一位奇妙而伟大的人。每过一周,他就像是换了个样,变得更加完满。”
席勒的作品就是这一生命之作的游戏形式。他坚守着自己所订立的原则:“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艺术的游戏是自由的显现。席勒本也可像尼采(Nietzsche)一样说:正因我们有艺术,才不致在生活中坠入深渊。
从席勒的角度出发,理想主义才重获光彩。若是人们像席勒一样去理解,“理想主义”之上其实并无多少过时的东西:为自由开辟道路;由精神为自己创造肉体。这样,席勒也就成了18世纪晚期哲学的重要启发。他决定性地参与了介于康德(Kant)与黑格尔(Hegel)之间的跨时代的哲学事件。我们将会叙述他如何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中发挥作用;他如何竟能与歌德一起成为德意志精神生活中的那颗位居核心的恒星。席勒——一座源源不断产出启迪的发电厂。对于他的敌手而言,也同样如此。浪漫派需要与他划清界限,才能找到自己。他们想要摆脱席勒,却因此更不能离开他须臾。
一出精神的伟大歌剧就这样诞生了: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创造力分布的密度史无前例,歌德、赫尔德、维兰德W、莫里茨、诺瓦利斯、荷尔德林、谢林、施莱格尔兄弟、费希特、黑格尔、蒂克,竟同时登上了同一个舞台。而在他们中间就站着席勒,这位玻璃球游戏的大师。
席勒开创了一个时代。人们因此得以跟随他的足迹,翻开古典与浪漫时代的传记。背景则是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开场的政治大戏。
海涅(Heine)有一次曾说,德国人只在“梦里的空中王国”里闹过自己的革命。
或许理想主义不过是一场幻梦。而真正的革命呢?或许不过是一场更可怕的梦。当席勒于1798年终于收到迟到了5年、由丹东(Danton)等人所签发的法国荣誉公民证书时,丹东他们早已上了断头台,而席勒也与歌德观点一致:人们给他送来了一份来自“死者之国”的公民权(致歌德,1798年3月3日)。
同席勒一起,人们进入过去的另一个阴影之国:进入了德意志精神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那是神奇的岁月,它帮助人们保留住感知人生中那些真正重要而充满精神之物的能力。
(摘自本书序言)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读后感(四):成为席勒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对德意志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德意志分裂为三百多个不同的政治实体,互不统属,在政治上是孱弱的,因此遭到革命法国的入侵。但同时,这是德意志文化的黄金时代,在历史的这个瞬间,“创造力分布的密度史无前例”,歌德、荷尔德林、谢林、费希特等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弗里德里希· 席勒也位居其中,在德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2005年,在席勒逝世200周年之际,德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德国知名学者、自由作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撰写的题为《席勒传: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的席勒传记荣获当年莱比锡书展非虚构及散文类图书大奖。在这部书中,萨弗兰斯基为我们展现了席勒的一生,叙述了他如何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中发挥作用,也展现了那个年代德意志文化界的精神风貌。
席勒是符腾堡公国军中一名上尉约翰·席勒之子,他于1759年出生于德国小城马尔巴赫。席勒的家庭是传统的严父慈母模式,父亲胸怀大志,忠诚地为符腾堡公爵服务履职,换来职务晋升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在家中他也以义务为评价一切的标准。席勒就在这一父权的世界秩序中成长,终身保持着对父亲的尊敬。席勒在童年就展现出了文学天赋,并希望从事神职。但按照符腾堡公爵的命令,1773年,作为军官之子,他不得不进入强调服从和纪律的“军事育才学校”,穿上制服,过上了纪律严格的军营生活。符腾堡公爵每天都亲临学校,他将自己塑造成极其强势的父亲形象,心情好时则会称学生们为“最亲爱的儿子们”。公爵展示的权力给席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与家中的温和父权相比,这一权力显得更为专断冷酷,令人感到压抑,因此令席勒感到不满。但也正是在这里,席勒从阿贝尔教授等人那里接触到了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并阅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克洛卜施托克的诗歌以及“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他在文学中找到了慰藉,并燃起了对哲学的热情。在此期间,他转入医学专业,试图将这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但同时,他继续写作诗歌,并开始创作《强盗》一剧,以逃离军校中严酷的处境。
1780年,从军校毕业后,席勒被派往驻扎在斯图加特的掷弹兵团任军医,由于薪饷微薄,加之该团军纪败坏,席勒感到心灰意冷。幸运的是,他的《强盗》一剧于1782年首演,并大获成功。席勒为自己的作家身份而感到振奋,他现在相信,自己的未来不在医学,而在戏剧。此后他多次未经允许,擅离职守,前往剧院所在地曼海姆。符腾堡公爵得知后对他加以申斥,并予以拘禁14天的处罚,之后还禁止他从事与医学无关的创作,否则就剥夺他的职位或将他关入大牢。席勒决心逃亡。1782年9月23日夜里,在公爵盛宴的焰火映照下,席勒逃离了故乡。这一决绝的出逃从此成为席勒为自己新生活奠基的神话,他决心除非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否则绝不回国。
作为逃亡者,席勒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他之前为印刷《强盗》背负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老于世故的曼海姆剧院总监达尔贝格顾虑符腾堡宫廷的反应,回避与他的接触,这使得他出售新剧本获得报酬的希望破灭了。幸运的是,席勒同学的母亲封·沃尔措根夫人邀请他前往自己在鲍尔巴赫的农庄小住,在这里他开始写作《阴谋与爱情》的剧本。到1784年,达尔贝格邀请席勒前往曼海姆担任剧院诗人,写出三部能上演的戏剧,但席勒完成的《斐耶斯科》《阴谋与爱情》都没有取得票房成功,而他与演员们的关系也迅速恶化,这使得他最终被辞退。这使债务缠身的席勒陷入了绝望的处境。
但到1785年初,席勒恢复了自信,他前往莱比锡寻找新的生活。他与之前曾通信的科尔纳等人交好,在友情的滋养下,席勒情绪高昂地写下了后来因贝多芬的谱曲而闻名于世的《欢乐颂》。席勒在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地度过了两年时光,期间断断续续地写作《唐·卡洛斯》等作品,并接触了康德哲学。可德累斯顿的文化生活之荒芜令席勒失望,1787年,席勒前往魏玛这座文化名城,结识了维兰德、赫尔德等人,进入了当地文化圈子。在这里,席勒转向历史,写作了《尼德兰独立史》。以此为契机,席勒被耶拿大学聘请教授历史,在此结识了费希特、谢林等人。也正是在这里,席勒得知了法国革命的消息,他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却谨慎地没有发表看法,避免过早得出结论。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他的心被爱情占据了,1790年2月22日,他与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成婚,开始了家庭生活。
婚后,席勒继续忙于工作。他全身心投入《三十年战争史》的写作,这部作品的热销使席勒情绪高昂。但1791年1月,席勒突然病倒,几乎不治,到处流传着他已经去世的谣言。面对命运的重击,作为医生,席勒心里清楚自己时日无多,他决心用好剩余的生命,把注意力集中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回归文学。就这样,席勒一边与疾病共生,忍受着折磨,一边想要从身体上赢得尽可能多的东西,“当整座大厦最终倒塌时,我或许已经从大火中抢救出了值得保存的东西”。在这之前,他潜心钻研康德哲学,他希望藉此来更好地理解自己对艺术的热情。
1794年7月,席勒与歌德在耶拿会面,由此开启了两人的友谊。1795年,席勒编辑出版了《季节女神》杂志,提出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概念,希望自己关于秀美与尊严的理想在杂志上起效,刊载有品位的文学和有思想的学术内容,并邀请歌德参与编辑工作。他开始阐发先前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刊载在杂志上的《审美教育书简》提出自己的美学思想,以解答为什么要艺术?为什么反思艺术是值得的?他否定了艺术的有用性,也否定艺术要服从道德等观念,在他看来,“伟大的艺术什么也不求,只想要它自己,它邀请我们在它这儿驻足,因为它是那实现的瞬间。”同时,作为给刊物的稿件,席勒重拾文学创作,写作了《理想与生活》等大量诗歌。
1796年,席勒转向了《华伦斯坦》的创作。在之前对三十年战争收集的大量素材基础上,席勒设法克服了浩如烟海的资料,将复杂的事件浓缩为清晰的情节线索,完成了这部杰作。席勒早年已经意识到,充分定义的性格不过是一种虚构,在真实的生活中并不存在。在每个真实的人当中都留有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可以将他卷入自由的冒险。在《华伦斯坦》中他同样塑造了这样一个亦正亦邪,真实意图不明的人物形象,在舞台上再现了恢弘的权力游戏。在写作过程中,席勒一直寻求歌德的建议,而他也为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提供分析和建议,两人的合作越发紧密,两位文学巨匠的友谊结出了硕果。《华伦斯坦》的成功奠定了席勒“德意志莎士比亚”的声誉,这也使他大受鼓舞,之后几年中,他以惊人的速度将《玛丽亚·斯图亚特》《威廉·退尔》等剧作接连搬上舞台,创造了德意志戏剧艺术的典范。
到19世纪初,席勒声望如日中天,已成为神话。剧院争抢他的作品,出版商付给他丰厚的稿酬,他终于过上了自足的生活。他甚至受到宫廷青睐,获封贵族,可以出席宫廷盛会。但名利双收之际,席勒的身体也每况愈下。1805年5月1日,席勒在观看剧院演出时病倒,9日,席勒与世长辞。
王国维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席勒一生恰好诠释了这三重境界。年轻时,席勒曾在医学与文学之间摇摆,但他最终追随自己的心,选择了那条更艰辛的道路。逃离斯图加特后他一度陷入绝望,之后的岁月也不乏艰辛,但他始终坚持,从未放弃对艺术的热情。最终,席勒在多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与歌德相知后,席勒的创作更是进入黄金时期,成为与歌德齐名的文学伟人,赢得了身前身后名。
席勒的人生虽然短暂而坎坷,其成就却极为辉煌。《席勒传: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为我们展现了他的成长经历和重要作品,也阐释了席勒所理解的“理想主义”——为自由开辟道路,有精神为自己创造肉体。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席勒的一生充满了强劲的生命力,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从不安于现状,而是不断打磨自己,完善自我,追求着无尽的可能。对席勒而言,阻挠他人完善自我是一桩罪行,百般阻挠他按自己的构想投入文学创作的符腾堡公爵“亵渎了个体将自身的丰富带向世界的权利”,因此,他决然逃离,以赢得按自己所想度过人生的自由。作为普鲁塔克笔下那些伟大人物的崇拜者,在席勒的价值秩序中,强有力的美德位于榜首,其次是强有力的恶人,道德正确所要求的的那种软弱的善人位居第三,既邪恶又软弱的则属于人类的浮渣。为此,席勒在诸多作品中鞭挞暴政、歌颂自由,并创造了超越凡俗的英雄人物群像,描绘了他们如何采取行动,赢得作为人的尊严。席勒自己也如笔下人物一般,不顾病躯,在文学、美学和史学等多个领域释放着创造力,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们倒要看看,究竟是精神胜过肉体,还是肉体胜过精神!”凭着这般完全不屈的精神,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命运,把生活过成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