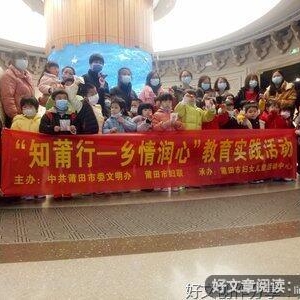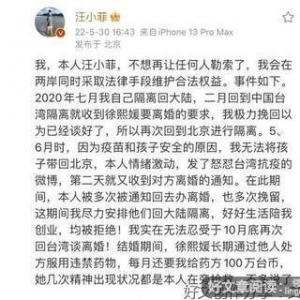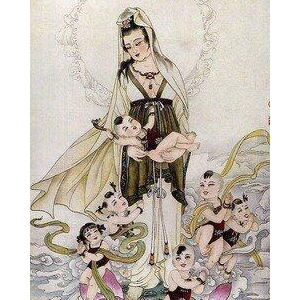一朵飘走的“云”
一点飞鸿

时光流逝,不经意间又到了一年的暮春。在这个落花风雨的黄昏,独自伫立在窗前。沙沙点滴声夹杂阵阵蛙鸣,不时轻叩着我的心扉,让我突添几分伤感。再过两周,就是清明节了。屈指一算,云妹与我们别离已经277个日夜。我感念她“来如飞花散似烟”的短短47个春秋;多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她的一颦一笑,宛如昨天,从我脑海里不断闪现。想着,想着,思绪又把我带回到了从前……
认识云妹,是在多年以前。1986年,高考落榜的我来到县城补习。通过熟人介绍,我暂时寄宿到他城郊姐姐的家里。这是一个经济条件很一般的家庭。姐夫在砖瓦厂上班,姐姐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家里有两个孩上学的孩子,男孩上初中,女孩刚上小学。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的云妹,是年她才9岁,梳着一对麻花辫子,模样俊俏,轻声细语的。放学回家,总是自觉地帮着妈妈做手工。虽然我们非亲非故,但姐姐姐夫待我如同手足,他们非但不肯收取我的食宿费用,还想方设法为我补充营养。后来,“不识事”的我,又把同样在补习班学习,遇到困难的敏介绍到他们家,再后来,敏又把同村的彪同学介绍了进来。姐姐姐夫虽然识字不多,但非常淳朴善良。他们知道农村孩子读书考学的不易,竟然在接纳他们的同时,还是不肻收取任何费用。就这样,我们三个“穷书生”,占用了他们家仅有的一间两层房的底层,他们自己则挤在二楼的一个狭小空间。
感动之余,我们只有更加发奋的努力,报答他们一家对我们的关爱。每当夜深人静,学习累了,我们一头扎进旁边的小河,洗个澡,清醒一下;有时候也会跟他家男孩一起在小河边钓钓鱼,以放松一下。但每当被姐夫看到,他总会告诫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要好好学功课,才对得起父母。最后,我们三个终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分别考取了法律、建筑、工商院校,跳出了所谓的“农门”。
随着年岁的增长,云妹和她哥哥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与高个小伙。只是本来成绩不错的云妹,在三中毕业后,不知何故没有继续深造便参加了工作。再后来,我们分别在城里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值得欣喜的是,云妹在与阿彪的不断接触中,互生情愫,结成了夫妻。三十多年来,我们早就把彼此当成了亲人。每年的春节,我们大家总会带着另一半及孩子到姐姐姐夫的家中共聚共叙。这种感觉犹如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样舒坦、自在。
前些年,得知云妹得了慢性肝病,每次相遇,我们总会提醒她不能劳累,要多保养身体。可她总是笑笑说没事,自己在吃抗病毒的药。没想到,两年前病情逐步开始恶化,他的丈夫(兄弟阿彪)不得不放弃项目经理几十万的高薪,全程陪护她去大医院看病。但是,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她的生命。
她生命的最后时光,我再次去医院探望。只见她痛苦地卷曲在床上,病魔已经把她折磨得如纸片一样瘦弱。尽管自己如此境况,她还是问我中饭吃了没有,一边叮嘱阿彪去打饭给我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永远装着别人,唯独没有她自己,所以无论走到哪儿她的人缘都特别好。我劝她不要放弃治疗,要坚持。她吃力地对我说,自己已经看淡生死了,该交代的事也都交代清楚了。我知道讲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内心有多么的不舍和无奈。
云妹走了,她真的走了!这个我们看着她长大的小妹;这个在我困难时侯,拿出积蓄帮我渡过难关的小妹;这个在我女儿考取重点大学,她比谁都开心,忙着帮我们挑选专业的小妹;这个在我困惑的时候,总是慢条斯理地开导我的小妹;这个最爱唱《女人花》的小妹;这个最爱吃山核桃的小妹,她带着丁香般的愁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每每想起她,我的心总会隐隐作痛。
一段时间,我总是想不通一个道理。为什么这样善良的家庭,这么善解人意的好人,会遭遇如此厄运?现在我终于想通了。如果说坏人的早死,是阎王爷催命让他早下地狱,那么好人如云妹的早逝,一定是上帝另有重用,接她去做了天使。我相信云妹一定上了这个道,她化作了一朵彩云,飘向了美丽的天堂;她在那里沐浴爱的光芒,没有痛苦,只有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