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婚之后,周旋于职场和家庭的女性,生活半径日益缩紧,聊天话题围绕房贷、育儿和养老。曾经叛逆的女孩成为人妻,一碗从酒吧里端出来的冒菜,成为她们逃离日常琐碎,连接少女时代的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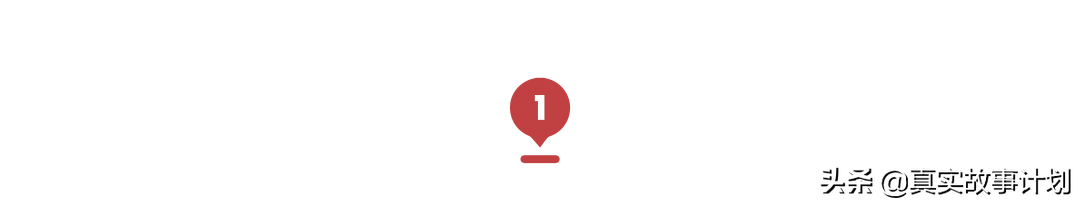
下午5点半,我不顾老板黢黑的脸色,脚底抹油般奔出办公室。半小时后,我抵达成都一家知名酒吧,除了我,只见到服务员在做营业前的准备。
每月都有这么一天,我会推掉所有工作和家事,赶去见一个人。为了这场持续到凌晨的约会,我要提前一天做准备。
首先,得征求我家5岁小朋友的同意。哄儿子睡觉时,我轻言细语地跟他商量:“妈妈明天下班后想和朋友吃个饭,得在你睡着以后才到家,可以吗?”
持续的沟通,加上玩具的贿赂,我总算拿下第一轮谈判的胜利。
下一步,谈判对象转向丈夫。我央求他暂时中断“996”工作制,下班准时回家,替代晚归的我陪伴孩子。
让我费尽心思去赴约的人,是我最好的朋友唐小雅。
第一次见唐小雅,是高一刚开学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我缺席了军训。同学和我说,军训时,和她同组的女生相当自闭,俩人相处了七天,没讲过一句话。
这个女生便是小雅。一次调整座位,小雅调到了我后桌。与同学描述的相反,小雅和我,几乎每堂课都要变着花样聊天,聊到兴致勃勃时,我们一前一后,躲在课桌前捂着嘴笑,或者咬着钢笔头,眼噙热泪。
对于这巨大的性格反差,小雅说,是因为自己遇上了对味的人,那个人就是我。
我和小雅的口味颇为一致。每天中午,同学们都去食堂吃饭,而我和小雅偏要走20分钟的路程,去吃一家叫“二毛”的冒菜馆。
二毛冒菜馆窝在一个曲曲折折的小巷子里头,是名副其实的苍蝇馆子,店里长期不开灯,墙面沾满污渍。第一次来,见老板端上黝黑的汤底锅,汤面上零星飘着几颗油珠,我和小雅都没动筷子,以为是隔壁桌吃剩的,老板来不及收拾,随手放一下。
直到第二碗同样卖相不佳的冒菜端上来,我俩才恍然大悟。撅起藏在汤底下的菜品,送进嘴里,是意料之外的辛辣,十分入味。我和小雅胃口大开,忽略了老板端菜时插在菜汤里的大拇指,一致决定,以后每天中午都来这吃。
外表乖乖女的小雅,其实情感经验很丰富。她有一个笔记本,纸页有四种颜色,几乎写完一种颜色的纸张,她就换一任男友。我没见她为任何一个男友伤神掉泪,每段恋爱,最终都成为佐餐故事,和冒菜一起端上饭桌。
当时,我戴着框架眼镜,马尾草草地扎在脑后,性格有些男孩子气,是很容易湮没在人群里的女孩。而留着齐耳短发,扑闪着琥珀般的大眼睛,皮肤又白又细的小雅,是男生们嘴里常常提及的名字。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的感觉,我概念模糊。小雅让我假想,哪位明星符合我的择偶标准,我不假思索,说,花儿乐队的大张伟。
小雅举着筷子摆摆手,说我和大张伟不合适,我本来就“闹麻了”,再找个闹腾的人当男朋友,无法互补。我崇拜地望着经验老道的小雅,认定她是我爱情之路的引路人。
那时穷学生时期的我们,会共享一碟辣椒面。一碗冒菜3.5元钱,我和小雅再轮流额外支付5角钱,找老板加一个装满辣椒面的干碟。
一边吃冒菜,一边听小雅讲她的恋爱故事,我总觉得格外有味。这一吃,就是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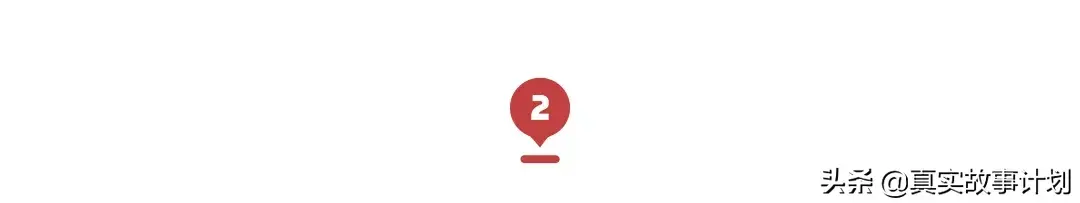
几分钟后,小雅推开酒吧大门匆匆落座,我们迫不及待地开始点单。
两碗热气腾腾的冒菜端上桌,我们默契地同时关闭话匣子,把鲜香麻辣的冒菜往嘴里送。
再次抬起头来,两层楼的酒吧已经座无虚席,大门口被排队坐着等待叫号的人占满。每张酒桌上,都堆满色彩缤纷的酒,酒精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令人晕眩。
这家酒吧,是我们和小雅每月定期约会的老地方。和其他畅饮酒精客人不同,我们是单纯奔着冒菜来的。桌上铺满了卤鸭舌、卤牛肚、卤土豆片等小吃,高耸的鸡尾酒杯暂时被放在地上,免得横在面前妨碍我们讲话。
待冒菜被扫荡得差不多了,我们放下筷子,把鸡尾酒杯端回酒桌。今晚的约会,才正式进入主旋律。

作者图 | 和小雅在酒吧吃冒菜
少女时代,我们的佐餐话题是小雅的恋情,时至今日,那些陈年往事依旧值得摆上酒桌,被我们翻来覆去地咂摸。
高一下学期,我和小雅在二毛冒菜馆的聊天有了新内容。我暗恋后桌的男生,但不敢表白,把情愫统统倾倒给小雅。课间、饭间、交换日记里,我总是提到他,周末见不到小雅,就和她短信交流。
一次周末,我发短信发到小灵通停机,又下楼买了一张IC卡,在电话亭里和小雅聊了一下午,最后,IC卡也欠费了。周一在二毛冒菜馆,我说自己一星期的冒菜钱都聊没了,小雅掏出40块钱,分给我20,说:“你喜欢的大张伟,有首歌叫‘我的果汁分你一半’,现在我的钱分你一半。”
那是第一次,我和小雅聊起友情的话题。我们质问对方,最好的朋友是谁,还一再强调,最好的朋友是“第一好”,和“好朋友”不一样。
16岁,我们煞有其事地将友情的排序问题,上升到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度,那顿冒菜,在思索中恍惚地吃完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深思,我们把自己心中最好朋友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给对方看。我展开纸条,看到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我的名字,开心得把头埋进躲在书堆,笑个不停。一回头,正好撞见小雅趴在桌子上,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
我们很满意彼此深思熟虑的回答。那之后,我们在二毛冒菜馆停留的时间更长了。吃完冒菜,恋恋不舍地往学校走,看到空荡安静的街道,我们心虚不已——下午的课又迟到了。我们边走边酝酿演技,一个人来月经、另一个人送卫生巾的梗,已经被说烂了。
后来,我暗恋的男生认了我当妹妹,每天晚上同我打电话,唱周杰伦的《搁浅》给我听。和他打起电话,我就顾不得回小雅的短信了。对此,小雅很忿忿。她看不上他暧昧不清的态度,从没给过他好脸色,有几次当面爆了粗口。
我不理解小雅的“双标”。她对感情向来很随意,喜不喜欢都可以试着谈恋爱,不开心就分手,无缝连接下一任。我冲她发脾气,她懒得争辩,只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没多久,男生跟另一个女孩好上了,但仍旧每晚给我打电话,分享自己恋爱的细节。我很难过,挂了电话就开始哭。
小雅骂我“脑壳有包”,第二天到学校,接着骂那个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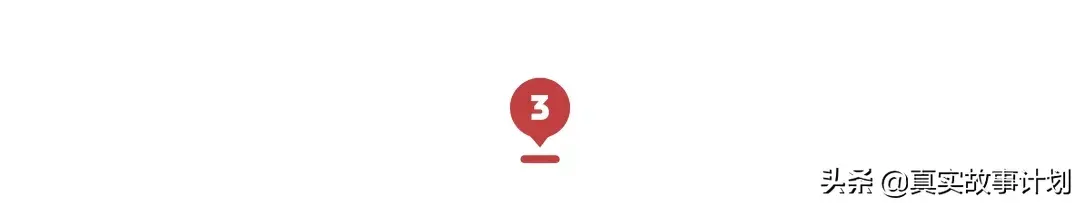
为缓解失恋的哀愁,我和小雅上课传纸条的次数愈发频繁,有时聊得不尽兴,还会先后举手,申请上厕所,在相邻的厕所隔间聊天。
一次,我们聊得正激烈,突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还没等我们反应,我所在隔间的门骤然被拉开,是语文老师。她看见我穿着裤子蹲在那,一把把我拎起来,接着,胸有成竹地敲开小雅所在的隔间门。
语文老师把我和小雅交到班主任那处理。班主任气得七窍生烟,随即请了家长,禁止我和小雅中午一起去吃冒菜。理由是,吃了那家冒菜,我们双双在课堂上尿频。
班主任越阻止,我们越是对着干,每天临幸“二毛”,顿顿吃都不腻。
当时,为节省时间来学习,很多同学自己带便当盒,中午排队去水泥炉子热饭。只有我和小雅,雷打不动,每天往冒菜馆跑。吃下那碗冒菜,就是未成年的我们眼中的叛逆指标。
班主任抓到我们“顶风作案”,大声斥责:“你们现在嬉皮笑脸耍得高兴,到了高三,有你们哭的时候。”
报应来得很快,也很惨烈。高三,我从重点班跌入普通班,小雅靠着强大的作弊手段,勉强维持在重点班倒数前三。高考临近,我们愈发不安,相约去卫生间聊天的次数骤减。

作者图|小雅送的生日礼物,巧克力印着我们的合照。
那年,我终于在成年前夕体会到了早恋的感觉,隔壁班的一位男同学成为我的初恋。小雅也谈了一个读职高的新男友,我们的二人冒菜小组,扩展成了四人冒菜小队。每天中午,小雅的男朋友骑自行车来我们学校门口等着,四人成功会师后,一路小跑着往二毛冒菜馆奔去。
高考的压力罩在我们身上,两对小情侣一起吃冒菜,聊天也很难风花雪月,多围绕着“高考”、“分数”和“未来”。
我的男友打算毕业去当兵,小雅的男友在职高学了一技之长,毕业后就业方向很明确,只有我和小雅,未来一片迷茫。
虽然两位男生每天中午都会轮流请我和小雅吃冒菜,但在我们担惊受怕之下,冒菜变得索然无味。我甚至觉得,恋爱不再是生活的调味剂,而是压力下的负担。
高考结束,我和小雅的感情都无疾而终。为了对毕业和失恋进行报复,小雅把头发烫成爆炸式羊毛卷,我也跟随她的脚步,把头发染成了金色。我们一起把指甲涂成黑色,在QQ日志里写无病呻吟的“火星文”,躲在厕所里学人家抽烟。
放榜那天,我和小雅正在KTV唱歌,听说高考成绩出来了,我们放下话筒就往网吧里跑。查出的成绩很喜人,我和小雅发挥超常,都有大学可上。
我们攥紧对方的手,激动地叫出了声。

填志愿时,我和小雅畅想,如果去外地读书,将会四年吃不到正宗的冒菜,当即决定,三个志愿都填报成都本地的大学。
最终,我们上了不同的大学。
大一时,我时常辗转多辆公交车去小雅的学校,她的学校后门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小吃街。后来,换成小雅频繁地来我的学校。因为,在我的大学,我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四人冒菜小队。
我和高我一届的学长陈智谈起了恋爱,经我撮合,小雅也开始和陈智的室友王石交往。
王石让小雅推翻了她此前玩闹般的恋爱心性,说:“以前都是小打小闹不懂事,不算谈恋爱,这次是要认真试试走一辈子了。” 王石对小雅呵护有加。冬天,小雅想喝银耳汤,他买过来,用嘴吹气,吹到不烫了,才让小雅喝。他是单亲家庭,生活费不多,为了和小雅约会,有时要节省下自己的饭钱。
我的恋爱也谈得顺风顺水。陈智高高大大,为人温文尔雅,和他在一起,我才真正体会到恋爱是多么美好的事。
王石和陈智都喜欢打篮球,我和小雅常去看他们打球。篮球场通往校外的小路上,有个三轮车改造的卖冒菜的移动摊位。打完球,这两个一米八几、热爱吃肉的男生,就会陪我们窝在矮桌子前,吃我们最爱的冒菜。
光顾的次数多了,我们和老板娘混得很熟。她知道我和小雅喜欢吃土豆,备菜不足时,会在旁边的菜摊买两个土豆,不紧不慢地削皮切片,丢进锅里。等我们冒菜吃得见底,她就提着竹篓把土豆片扣在我们碗里。有时怕两个大男生吃不饱,她还会特意在他们的碗里多加菜。
四个人一起吃冒菜,时常会吃一个多小时。那时候,时间过得很慢,我们不着急做任何事,慢慢地谈着恋爱。
才上大一,小雅就对我说,想和王石在25岁之前结婚,还嘱咐我,不要告诉王石她之前的恋爱经历。
我很惊讶。25岁和结婚,听起来都离我们好遥远。
大四,王石挂了科,他在电话里问母亲要补考费,否则不能毕业。王石母亲却认准这是小雅编借口,唆使王石问家里要钱。她要求王石与小雅分手,还给小雅打电话威胁,说如果不分手,就找人刮花小雅的脸。
一直处理爱情问题游刃有余的小雅,遇上了她解决不了的棘手难题。她经常跑来找我,躺在我寝室的床上,背对着我,一边听歌一边哭。
我心疼又愤怒,默默地想,我得像高中时小雅保护我那样,去保护她了。
没多久,我和陈智一起,陪王石和小雅吃了分手餐,还是在那个冒菜摊。
老板娘怕王石吃不饱,免费给他冒了些火锅粉。她不知道,那顿饭以后,王石是否能吃饱,就不再是小雅要关心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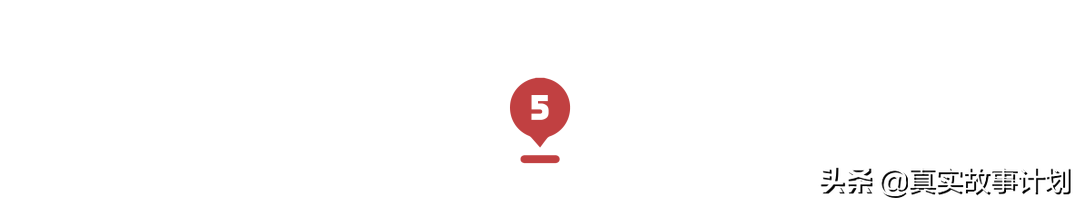
小雅说,要忘记前任,就得转移注意力,迅速找到新的桃花。但比桃花来得更快的,是大四实习。
又一次,毕业和失恋同时降临在小雅身上,只是这一次,她不再有任性叛逆的机会。
我和小雅在同一家早教机构实习,主管命令我把红发染回黑色,让小雅拉直她的小波浪锡纸烫。强行被改造外表,让我们初入职场的体验很糟糕。
我和小雅是中文指导师,负责给3-5岁的小朋友讲解动画片,做手工,常要面对家长上公开课。学校要求微笑服务,对待学生和家长要耐心、温柔。工作日,我和小雅要持续微笑8个小时,等到下班,我们立马卸下那张微笑的假面具,疲惫沮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频繁迟到,第一个月,小雅只领到100多元的工资。步入社会,我们才知道,学生时代的那些烦恼,实在太轻飘。
同事们都带便当上班,只有我和小雅出去吃。早教机构在商场内,里面的吃食偏正规,唯有一家冒菜馆,还算便捷廉价,12元一碗,但味道实在难以下咽,清汤寡水的底料,随意扔些叶子菜在锅里,大杂烩式地一顿乱煮。
但我们还是每天来到这里,吃一碗流水线般的冒菜。上学的时候,吃冒菜是一种仪式,现在,只是因为我们没得选。
主管对我和小雅时刻黏在一起的样子颇为不满,阴阳怪气地说:“早晓得你们两个关系那么好,压根不该把你们俩同时招进来,瞎了眼了。”搞得我们每天吃完冒菜后,还得刻意拉开距离,一前一后,错开走进办公室。
后来,主管干脆让我们各自带饭,跟当初的班主任一样,阻止我们一起吃冒菜。
我们自然不会顺从。中午吃冒菜的1小时,是我们逃离职场的宝贵时间。但廉价的实习工资,复杂的人事关系,我们无处遁逃。
三个月的实习期结束,我和小雅顺利地转正了。不过,刚转正没多久,我们各自找到了更心仪的工作,商量好,同一天向主管提出离职。主管气得吹胡子瞪眼,说白搭三个月工资培养我们,还解放我们的天性了。
2014年,我和相恋6年的男友陈智结婚了。婚礼当天,小雅是我唯一的伴娘。在扔手捧花环节,我扭头,反复确认小雅的站位。随后,小雅精准地接住了捧花。
主持人请手捧花的小雅上前一步,她举着话筒,哭成了泪人。
隔年,我的结婚纪念日当天,小雅发来一张结婚证的照片。丈夫是她玩网游认识的男生,小她3岁,为了她从外地赶来,定居成都。
我酸了酸鼻子。总是甩不掉她的,连结婚纪念日都是同一天。
结婚之后,小雅没再上班,成了专心看顾家庭的主妇。我在一家私企做文案,时常为工作焦心,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我和小雅各自忙碌着,很少再像上学时那样,带着家眷一起吃冒菜,生活的半径渐渐萎缩,只有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和养老问题。
去年,我和小雅30岁了。在我们四个人的结婚纪念日,我和小雅甩掉丈夫,相约一起去纹身。纹身师善意提醒,需不需要考虑工作,把图案纹在更隐秘的部位。我们相视一笑,坚决地摇头。30岁,我们渴望从按部就班的生活里抽离出来,取悦自己一次。
那之后,每个月,我们都会雷打不动地抽出一天时间,相约来吃冒菜。刚毕业时,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成为我们买醉的借口,而今,我们不贪恋酒吧里的任意一款酒饮,只是无比怀念那些为学业受罪,为爱情流泪的简单岁月。
酒或冒菜,都是只是回忆的铺垫。酒桌旁的炉火中看不中用,我和小雅聊到深夜,冻得声音都抖了,一把鼻涕一把泪,还是舍不得离开。
我从往事里冒头,抬起手,想敬小雅酒,发现酒杯已经空了。
驻唱歌手一首接着一首地唱歌,我们停下来听一听,小雅说,这首歌,和她某个前男友有关。我调侃她,为了备孕打算戒烟、屡戒屡败的人,还想啥前男友。
初识彼此,我们的年龄“1”字打头,如今已是“3”字开外。经历了15个春夏,女学生变为人妻,只有在吃冒菜的间隙,我们仍像两个少女,有讲不尽的话。
接近凌晨,桌上的菜和酒早已被我们扫荡一空,我们砸吧下嘴:“现在消化勒差不多了,是时候点宵夜了。”
服务员撤走残羹,不一会,又为我们上了新一轮的冒菜和鸡尾酒。
- END -
撰文 | 张小冉
编辑 | 刘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