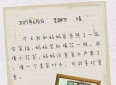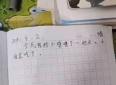电报送到时夜幕已悄悄降临。披头散发的我刚从公共澡堂出来,手里就被塞了张纸条,来人一边塞一边关切地说:“不要着急,你不要太着急。”
虚弱地对她微笑之后,独自对着那张面无表情的纸呆愣了好长时间,并没有哭。
父亲病了?父亲怎么会病呢?!日子还不到愚人节,谁在跟我开这种无聊无耻的玩笑?将那不大不小的纸在手里翻来覆去揉搓了好多遍,看得清清楚楚,收件人姓名的确是我。知道那孤岛一样的小小工厂里,也并没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者,那么莫非,父亲真的是病了?
病就病了吧。人活在世上,谁能不生病啊。这样想着,居然也并没有彻夜失眠,居然也还睡着了。
正是开春时节。父亲晚间组织村干部开会,照例休息得很晚。躺下不久,母亲听到了父亲的呻吟。
小镇没有医院,只有赤脚医生。半夜擂门喊来,却无法说出病情,于是父亲一直处在痛苦的半昏迷中。咳血、说胡话,心口疼起来,似有一把把尖刀在剜……母亲陪着他,嫂嫂忙着托人去请父亲的儿子们。
大哥在一所大学执教,二哥在一个乡镇派出所上班,说起来,似乎都不算远。然而当年,路是颠簸的土路;车是几个小时才发一趟的长途车,所以等儿子们分别接到消息匆匆赶回后,已是下午时分。
不用说,赶紧送往县医院。交通工具是全乡唯一的一部客货车。
路面坑坑洼洼,车上的父亲不得不忍受着一路颠簸。总算颠到医院。很重视。派来一名副院长一手负责。
没有好药!大哥给省城的朋友拍电报让想办法弄。药送来了,父亲却已没机会用了。
父亲的突然离去,让我变得癫狂甚至不可理喻。
大哥说他晚上做噩梦,梦到别人朝他的胸口开了一枪,我听后怒气冲冲地朝他吼:“父亲一定是替你挨枪子了吧?”
未婚夫长途跋涉赶到父亲的灵堂前伤心难过,我却冷冷道“他哭什么?”自己最亲爱的父亲年纪轻轻就没了,一时之间,我觉得全世界只有我最可怜,只有我才有资格哭鼻子。而你们,父母双亲齐全,倒是哭什么、哭什么呀?
我伤心、生气且恼火,看谁都不顺眼。哭,也似乎只有我才最有资格。最深的痛苦,一定伴随着无法言说的落寞,不能述说的孤寂。
我的天塌了,塌得干脆利落……而我,灵魂好似浮萍般无着无落。我在日记里跟父亲聊天,第一句是:“父亲,知道有话无处说的那种痛苦和难过吗……”
我想念父亲。想和他舒服畅快、酣畅淋漓地聊一次长天,说几句心理话,父亲却吝啬地连这样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我放假了。父亲的屋子却天天被一群人包裹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人。心底是觉得烦的。烦他们无限期霸占着父亲的时间。烦因为他们,好多我想跟父亲说的话都没有说,讨论的问题都没有讨论……
病魔挥起一刀,一切瞬间化为虚飘。
终于明白,除了时间,谁也解救不了谁。
时间多神奇啊!他像一位最高明的药剂师,把一味温药徐徐铺展在你面前,让你慢慢懂得,失去的,的确是永远失去了;让你逐渐明白,人一定要学会自己说服自己,因为这世界上能说服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
小镇还在,回去的次数却是愈来愈少了。于我而言,它是伤心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