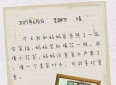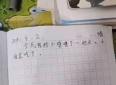陪父日记
(纪实随笔)
杨崇德
第10天
2019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十一。
星期天。
今天,是父亲住院的第10天。
凌晨2点15分,睡意朦朦的杨柳青,偶然瞥见:爷爷已经自己坐在了床沿上!
杨柳青惊醒过来后,一骨碌地爬了起来,紧急呼喊着我。
我顿时从梦中醒来。
父亲的确坐在了床沿上!
父亲低着头。默无声息。
这真把我给吓坏了!
父亲怎么一个人爬起来了呢?
他是不是想起来上厕所?
他怎么不叫我们一声呢?
哎呀,我和柳青两个陪护者,怎么就没有一点惊醒呢?
我们真是失职了啊!
我心里不断地责怪着自己:怎么躺着躺着,就睡了呢?亏你还算是陪护人呢!
父亲也算是失言了。
昨晚夜深的时候,我有点熬不住,我就靠着父亲的耳朵说:爹,如果你想屙屎屙尿,你就喊一声,如果喊不应,就拍一下床铺,你可千万不要自己行动啊,晓得么?
父亲当时应得好好的。
可父亲并没有喊我们,也没听见他拍床铺,他就这样,自己爬起来了。
这让人很是惊恐万状。
父亲的两只脚,吊在了床沿上,身子弯弯地缩坐在床上。
父亲或许喊了我们,或许也拍了床铺。只是我和柳青,都睡得太沉了,没听见他的召唤。或许,父亲一定是没有力气喊,也没有力气拍打了。或许,父亲是不忍心这样做,他怕影响我们睡觉。
可是,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应该让父亲深夜里一个人独坐!那样,就太让我们内疚了!
整个病房里的人,全都在熟睡。
只有父亲一个人,坐在那儿。也不知道,父亲爬起来多长时间了。
我光着上半身,爬了起来,一脚就踩到父亲的床上。
我双手扶着父亲的背。
我怕父亲倒下去。
我问父亲:“爹,你是不是想上厕所?”
父亲“嗡”了一声。
我和柳青,急忙扶起父亲,让他下床站起来。
柳青扶着父亲,慢慢向通往厕所的那扇门移去。
在病房的过道里,摆放着3张简易的陪护床。此时的空间,要比白天狭窄了许多。
过道陪护床上的另外2个陪护者,已经酣然入睡。有个人的手臂,还搁在他自己的额头上,像是怕灯光的样子。
我跳下床,企图追扶过去。
但我光着脚,觉得很不卫生。于是,我又侧了回来,去找母亲那双黄色塑料拖板鞋。终于找到了,就在我睡的陪护床下面。虽然是小了点,但还能挤着穿。
我趿起那双鞋,追到了门口。
我和柳青,扶着父亲进了厕所。
父亲站在里面,一只手撑着墙,一只手在下面掏。
我干脆把父亲要掏的,给掏出来,并说:“爹啊,您现在只管屙尿就是了。”
父亲站了很久,才缓缓排出来一点点尿液。
尿液黄得像打碎了的蛋黄。
父亲没有蹲下去屙屎。
他没有屙屎的欲望。
一般情况下,清晨起来屙尿,都会引发屙屎的欲望的。可父亲没有。
这说明,父亲可能肠道结了,也有可能,他真的没什么粪便可以排泄了。
一天到晚,没吃什么东西,怎么可能会有大便出来呢?

父亲上额的那副假牙,已经脱落在他的枕头边。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取下来的。
怪不得,昨天晚上,我观察父亲时,觉得他嘴唇下陷,老得不成样子了。
我把父亲的那副上额假牙,捡起来,放在一个一次性塑料杯里。并要父亲把他的下额假牙,也取下来。
我连续说了三次,父亲都没有回答。
父亲想倒下去,继续睡。我和柳青只得让他躺下去。为他盖好被子。
父亲睡在那里,一直没有闭眼。
我凑过去,把嘴唇靠在他的左耳边,轻轻说:“爹,我和柳青,今天下午,要去看一下他的外公。他外公,也住院了。晚上,我们要坐7点钟的高铁,回长沙去。我们明天,去上班。我去忙两天,又回来照顾你,好吗?”
父亲算是听明白了。
他“嗯”了一声。
我又说:“爹,我会把你的名字,记下来的,写成文字。以后,留给你所有的后代,让他们也都知道你老人家的名字,好吗?”
父亲又听明白了。他“嗯”了一声。并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良材,因为不识字,没有文化,委屈了他。
父亲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在那个贫困的山巅之上,他一直鼓励我,加油读书!加油读书!
父亲把读书比喻成挑担。他告诉我,不要怕呷亏,挑不起,咬着牙去挑。想像着,马上就可以把肩上的担子挑到目的地。别人力气大,能挑一百五十斤,你力气小,就多做一回挑;别人休息,你多挑一个来回,同样能把担子里的活挑完的。
我之所以要把父亲与我们同在的日子,一点一滴地留下来,就是想让父亲继续活下去,活在他的儿女们心中,永远地那么可爱、慈祥、伟大。
我这辈子,没当上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大富翁,我能够报答父亲的,除了在生活上,竭尽所能地照料外,可能就只有这些片言只语了。
父亲曾经知道我喜欢写作,很是开心。父亲认为,能写,也算是一种本事。
父亲甚至知道,我在支行工作时,偶然提及地区农行的汤胡子和钟主任两个人。我说他们两个能写,父亲就放肆地鼓励我,要我向他们学习,多写,争取超过他们。
住到地区农行那边后,我们遇到了汤学正和钟光成两位主任,打过招呼之后,我暗暗地告诉父亲说:那就是汤胡子,那就是钟主任。
父亲羡慕地说,日他崽崽的,那么肥肥胖胖,那么跛起一只脚,还这么会写呢!
我早就感觉到,父亲你就是缺了文化,要不然,以你的聪明和洞察力,你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写手。甚至是一位作家。
我想,父亲的聪明,就在这里了。父亲知道,文字能帮人延长寿命。
所以,当我提出要把他的点点滴滴,用文字留下来时,他毫不犹豫地重重地点了点头。
试想想,有多少达官贵人,生前风光一世,死后如尘土。一年死,二年亡,三年全无。
从这个意义上讲,爹啊,你比那些人都要强。至少,你的英名,会在你的子孙当中,流传下去,经久不衰。
放心吧,爹,我会努力!
父亲痴痴地躺在病床上,微闭着眼。
我说:“爹,你一定要吃中药。中药就是再苦,再不好喝,您也要喝啊。只有它,才能让你慢慢地好起来。”
父亲还是听懂了,他点了一下头。
喉咙里发出“嗯”的应答声。
现在,还只是凌晨2点半。
我说:“爹,你休息吧,天还没亮呢。”
父亲看着我,不回答。

早晨5点,父亲就要起床了。
他上了一趟厕所,屙了一小泡尿,还屙了一小节屎。粪便黑得出奇。
我开始给父亲洗舌头,洗脸,洗他的假牙。
我和柳青,把父亲扶到了轮椅上,早早地推着他,到楼外晨游。
二姐和母亲,是第一批赶到的。昨晚,二姐为父亲熬了稀粥,又熬了鸡汤。母亲也住在她家里。
紧接着,大姐、大姐夫、大妹、弟弟,也都赶过来了。
我们相聚在医院后大门左侧的休闲亭园里。
二姐给父亲喂稀粥和鸡汤。
在亭园里,呆了40多分钟,我们一直引导着父亲说话。
父亲有时问一答一,有时问三答一,有时根本不说话。
父亲只是静坐在轮椅上,无力地望着远方。间或,他将眼皮耷下来,作休闲状。
早晨7点半,父亲想回病房了。
我和柳青,推着父亲,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大队亲人。
大姐夫身上还背着透析药水袋,很不方便,也就没有继续跟我们回父亲的病房了。他要回家换药水。
大姐夫一般很少出门,现在父亲成了这个样子,他就是再艰难,也要过来看一看。
我们上了楼,来到三楼的走廊里。
开始为父亲喂中药。
父亲喝着喝着,吐了两回。父亲不想喝了。
父亲今天喝下去的中药剂量,远远达不到医生的要求。
再怎么劝他,也不想喝了。
这让我们个个张着嘴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没有药物进去,这意味着父亲,就没有武器对抗病魔了。
母亲一下子就撅着嘴巴,轻声地哭起来了。
父亲想躺到床上去。
我们扶他上了床。
上午,我们要去天星坪那边,要去看柳青的外公。
该是与父亲告别的时候了。
我回长沙几天,就会回来。
柳青却不一样,他工作很忙,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就很难请到假了。
因而,柳青与爷爷的告别,就意味着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或许,父亲现在是与他的长孙柳青在诀别。
柳青也有这个预感,心情变得异常沉痛。
柳青守在爷爷的枕头旁边,呜呜地哭。
他不愿意走。

上午8点58分,我和柳青,离开了父亲,离开了医院。
是弟弟开车,将我们直接送到了天星坪。
上午,这里由大姐、二姐、大妹和母亲,陪伴着父亲。
在我们离开后,查房的主治医生刘医生来了。
刘医生查看了我父亲的情况后,问我的姐姐妹妹,说:“你们是他什么人?”
二姐抢着说:“我是他女儿。”
刘医生说:“你父亲的情况,你们知道吗?”
二姐说:“知道。”
刘医生说:“你们可以把他弄回家了。”
大姐说:“我们想把他留在这里,继续疗养呢。”
刘医生什么也没说。走了。
接下来,二姐对着父亲的耳朵说:“嗲,你想回去吗?”
父亲不情愿地说:“你们这些人,总是要说回去。”
过了一会儿,父亲想睡觉。
他闭上眼睛,就开始说梦话了。
父亲说:吃粽粑,肾会痛的……
在父亲沉迷入睡时,我血缘关系最近的小族叔松娃叔,带着他儿子多胡子,也进来了。
父亲醒来时,松娃叔就说:“哥,你好一点了吗?”
父亲说了一句“你难得来的。”
说完,又沉睡过去。
松娃叔是“难得来的”。松娃叔现在自己都重病缠身。
其实,松娃叔也不算老,只比我大三岁,五十五六的人,现在已经是骨瘦如柴了。
我的族爷爷,一共有四个儿子,娃崽叔是老大,安崽叔是老二,松娃叔是老三,光子叔最小。前几年,光子叔四十出头就走了,他得了糖尿病,又爱喝酒,他没有老婆,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光子叔死的时候,瘦得只有十五六斤,老鼠把他的几根指头,都咬掉了。
现在,松娃叔,就成了我最小的族叔。
我对松娃叔是很有感情的。小时候,我们俩经常一起上山砍柴,经常偷他爹的旱烟抽。
我清楚地记得,族爷爷在木楼上凉的那些旱烟叶,一到变干发黄时,就被我们偷去一大半。我们两人撕了作业本,跑到屋背后田埂当头的干水沟里,卷了喇叭筒,大口大口地抽烟。一听到族爷爷(也就是松娃叔的爹)在楼上骂:是哪个鬼崽子,把我的烟叶捋走了,短命鬼!
我们两人就躲在后面的田沟里,偷偷地笑。
我真不知道,松娃叔那只左眼睛,是什么时候瞎的。反正,我有生以来,是看不到他的左眼珠子的,那上面经常被眼皮子包着,塌在那里。
松娃叔为人,非常善良,又喜欢说些大话,比较夸张,眼睛又是那样的。因此,就很有人缘。
父亲原来担心松娃叔,讨不到老婆。然而,好人自有天助,他不仅讨到了老婆,而且老婆,绝对不比别人的差。我们亲切地喊松娃叔的老婆为:娥婆婶。
村里的年轻人,都到怀化城里打工去了,松娃叔却丝毫没有这个念头。
后来,连娥婆婶都进城,帮人扯鸡鸭毛,挣钱去了。松娃叔还是一个人,呆在穷天老家种他的田。在那个穷山村,再怎么种田,也比不上进城务工划算。娥婆婶多次劝松娃叔跟她进城去,他就是不愿意。可能,是他的左眼有问题,怕丑。
那时,我父亲也说话了。我父亲说:“娥婆都知道进城划得来,松娃你怎么就不愿意进城呢?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农村,分开有什么好呢?你到底怕什么呢?你是怕你那只眼睛,长得不好看吗?你是去做功夫挣钱的,又不是去做表演的。你怕什么呢?”
我父亲的话,终于让松娃叔,鼓起了勇气,进了城。
进城的头几年,松娃叔跟着村子里的人拖板车。后来,因为他的诚实,因为他的幽默,他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怀化电业局的短期工。
电业局一有什么拉线的活,总是找他去做。这与松娃叔的勤快、开朗、能吃苦很有关系。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松娃叔近两年得了痛风,又好喝点酒。务工是务不成了,只能呆在城里养病,越养身子越瘦。
这让我们很为他担心。
现在,他能来看我父亲,已经是花了很大的气力了。

父亲今天的中餐,还是省肿瘤医院专家开的那种营养粉粥。
中午12点33分,大姐给父亲喂营养粉粥。父亲只吃了小半碗。吃过之后,就是喝中药。
然后,大姐扶着父亲走出病房,移向走廊。
大姐扶父亲出病房时,父亲看到病房口的走廊病床上,躺着一个男人。
父亲开口就说:“朋子佬的崽,易家佬,怎么今天躺到这里来了?他又不去做工夫啊?他就不晓得,给他爹买一顶帐子,朋子佬都快被蚊虫咬死了。”
病房的走廊口,确实来了一位新的病人。年纪很轻,看上去,真的有点像我们院子里朋子佬的儿子易家佬。易家佬一直在怀化城里打工,也买了房子,很少呆在老家穷天。
朋子佬是我老家的一位长者,年纪比我父亲小几岁。近些年,他一直患有哮喘病,就跟着他的儿子易家佬,住在怀化城里。身体不好,长期不怎么下楼。
朋子佬叔呆在怀化,已经好多年了。父亲每年都要去易家佬家,看望这个朋子佬。
在我的印象里,朋子佬有点文化,主要会打算盘。生产队时期,朋子佬是我们队的会计,算盘拨得叭叭响。他也爱抽烟,牙齿被熏得漆黑。
特别是朋子佬叔的笑,简直让人发麻,吱吱地笑。像拉二胡的声音。
真没想到,这种拉二胡的声音,竟然就成了哮喘病。走上十来步,就上气不接下气,异常艰难。
父亲很是可怜这位易姓老弟。
在穷天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同甘共苦那么多年,现在谁有病,都值得格外同情。
现在,我的父亲,自己身患绝症,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可他的脑海里,还装着哮喘病缠身的朋子佬。父亲要朋子佬的儿子,帮朋子佬买顶蚊帐,免得被蚊子叮咬。
爹啊,我猜到了,为什么你对蚊帐,是那么记忆犹新。
我早就听到你的好友眨巴眼叔说过,说你小时候,长期没有蚊帐,夏天睡的时候,整晚整晚睡不着。你就和眨巴眼叔一起,到山里采摘苦楝树的树叶。晚上睡在土床上面,蚊子来了,你们俩个就烧苦楝树叶。薰得满屋子都是烟雾。蚊子虽然少了,但你们俩个,却被呛得咳嗽不已。
这,或许是你对蚊帐的特别渴求吧。

父亲来到走廊边,望着窗户外面,他迷迷糊糊地说:“那不是长远里的亭子么?”
父亲口中的“长远里”,是个地名。那是我们乡通向我穷天老家的一处山顶。
国民党时期,那里就建了一个凉亭。据说,在那个凉亭里,曾打死过人。枪打的。有人将死者的头,挂在了凉亭上。
我读初中时,经常路过那里。一到亭口,我的心里,就麻酥酥的。根本不敢朝凉亭上面看。基本上都是怆惶而过。
难道,我可怜的父亲啊,你的游魂,是在开始回家了吗?
你看到了长远里的亭子,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四卧龙村了。再爬过一个山坡,下了杉子坳,过了桥龙头,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爬到树龙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老家了。
爹啊,你的身子还好好的,只是肚子有些肿胀,全身有些发黄。
你不能让你的魂游走啊!你得魂魄合一,留在我们身边。
我们想要一个清醒的、健全的父亲啊!
来到医院走廊那排板凳上,父亲坐上去。
父亲今天的举动,让陪护者很是不安。
父亲从病房出来,一直都在说似懂非懂的梦话。
父亲的病情,已经在恶化了。
三姐逗着父亲说清醒一点的话,三姐说:“爹,眨巴眼叔最近动了手术,花了一万多。你晓得么?”
父亲说:“晓得。”
眨巴眼叔是我穷天故乡的一位老叔,小我父亲近两岁。他和我父亲有着相似的命运。
眨巴眼叔从小没了父母,跟着他的外公,在我们穷天长大。他外公是我们穷天的人。
而我的父亲呢,也是从小丧父离母,他是跟着我的祖父,在穷天长大。
眨巴眼叔从小就与我父亲在一起。他是我父亲这辈子,最好最好的朋友,是无话不说的朋友。
三姐又问父亲:“爹,你上次在中医院住院,花了多少钱?”
父亲说:“还不是一万多。”
三姐问:“是谁的钱呢?”
父亲说:“还不是我自己的钱啊。”
一回一答,三姐她们感觉,父亲还是清楚的。只是偶然他自己一个人,要说些离谱的话。
下午,我和柳青去三医院,给我岳父送中饭。
岳父的身体很弱,胃口也很不好。在三医院呆了个把小时,我们也觉得累了,于是回到柳青的满舅家,蒙头一睡,就是3个多小时。
松桃早早地备了晚饭。
我和柳青回长沙的高铁,是7点28分。
6点半,我们就赶到了高铁站。
在候车厅刚坐下,长沙的同事程中媛大姐,来电话了,说是晚上9点,邓姐夫会开车到长沙南站接我们。
哎,真是麻烦程姐和邓姐夫了!

晚上10点37分,怀化的三姐来了视频,我们俩聊了16分钟。
三姐今晚和大妹,一起守护父亲。
三姐刚刚守着父亲,哭过一场。
三姐说:“从上午开始,爹就说胡话了。他只要眼睛一闭,就放肆地说。我喊醒他,他又清楚。有时候,他连自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三姐说:“医生今天又建议我们,把爹弄回家。我们不忍心,想让他呆在医院,多留他几天。可是,今天的变化,又太让人伤心了。爹除了闭上眼睛说胡话以外,他的脚肿得更大了,他的肚子,也胀得更厉害了。”
三姐说:“爹的肚子,肿胀得现在已经现出了青筋。下午上厕所的时候,他的脚,迈不动,简直要靠人推着走了。”
我想,父亲现在一定是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可他似乎对诸多强加于一身的痛苦,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儿女们现在所看到的父亲的痛苦,都是以肿、胀、恍惚、似梦似醒等状态出现。
这让儿女们声泪俱下。
爹啊,你太可怜了!
87岁的老人,还要承受如此痛苦的折磨!
晚上11点,父亲躺在病床上。因为被三姐取下了假牙,嘴唇塌陷,模样衰老,脸皮的肤色,既黑又黄。
父亲的眼睛,一直睁着,泛出艰难的光。
父亲的鼻息,急促而沉重。就像父亲曾经劳作时,挑了重担似的。
抑或,这是一种不堪负重的生命之气。
那种画面,那种声音,一直在折磨着我,折磨着目睹他的每一个亲人。
三姐用纸巾擦拭着父亲的眼角。
那里,浸泡着父亲的泪水。
父亲不懂得呻吟,他只是艰难地挺着,挺着。
我的老父亲啊,你真的受苦了!
从你进医院到现在,时光还只流逝了八、九天,你却衰弱了八、九年了!
你一个人走进这个医院,而今却再也不能独自走回家去了。你只能卧床抗争了,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1点过8分,三姐扶着父亲上厕所。
屙了一点点尿。
三姐希望父亲能屙出一点点屎来。却是一种徒然和奢望。
夜晚,三姐给父亲剥了3个山竹。
父亲吃着吃着,就摆头了。
父亲不肯吃了。
父亲躺下来。
他将熬过这个黑夜,迎接又一个黎明的到来!
(本篇写成于2019年9月25日。2022年10月30日夜,于长沙家中稍作修定。)
请看续文:《陪父日记》(第 11 天)
关于本纪实作品的几点声明:
1、本纪实随笔,写作于我父亲去世后的两个月里。当时,父亲在生病住院期间,国内还没出现新冠疫情。因而,我们七姊妹才能够日夜守护在医院里,守护在父亲的身边,直到他离去。我这个日记体系列性文字,写作于2019年9、10月间。父亲病重至离世期间,国内无疫情,这也是上天对我父亲的恩赐。
2、本纪实随笔,于2020年发表在本人的微信公众号上。曾经感动过许许多多的亲人和朋友。我是凭自己的真情和泪水,用文字挽留父亲。我希望父亲活在我的文字里。如果读者还想阅读本人的其他文学作品,可添加本人的微信号ycd0070,我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阅读欲望。也真诚希望读者朋友对我的文字,给予批评指正。
3、本纪实随笔,现特推荐给 “齐鲁壹点” 网络平台作为首发。读者也可在“今日头条”、“百度”网络平台上阅读到该作品。但是,本人在此声明,拒绝新浪网对该作品作“手机新浪网”发布。因为我有几个阅读量较大的作品,一经“手机新浪网”强行发布后,读者们所留下的所有评议性文字全部就被屏蔽了。
4、本人坚决反对:网络上某些靠流量赚钱的所谓写手们,肆意将本作品强行拖至其个人账号上,再次对外发布,以为其赚取所谓的流量。对此,本人将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
5、本长篇纪实随笔作品,共21章(21天的内容),约16万字。若有出版社看好,可直接与我本人联系出版事项。联系微信ycd0070。
作者简介:
杨崇德,男,1965年10月出生,湖南怀化市中方县人。1995年加入湖南省作协。曾在全国两百多家报纸、期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近千篇。数百篇被《作家文摘》、《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杂文选刊》、《读者》、《故事会》等刊物转载。上世纪,本人曾被《微型小说选刊》列为“微型小说百家”之一。2010前后,本人出版了文学作品集《故乡的云朵》、《冬天的生活》、《丛林狼》、《麻麻亮的天》等。有作品曾获《小说选刊》2016-2017年度“读者最佳印象奖”。有作品被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发行。有数篇作品被全国50多所重点中学选为语文考试分析试题。本人系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理事,现任湖南省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
壹点号崇德随笔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