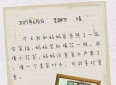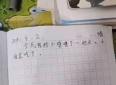陪父日记
(纪实随笔)
杨崇德
第13天
2019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十四。
星期三。
今天,是父亲住院的第13天。
这天早晨,我起来得算是最迟了。
昨晚,我从长沙赶回怀化。很晚才入睡。
母亲4点多钟,就起来了。我看到母亲时,她一个人默默坐在二姐家的客厅里,有些发呆。
二姐已经给父亲做好了早餐。
母亲对我说:“带崽啊,我们先走了,你后面来。”
我说:“还是等一等我吧,我马上就好了,我们一起去医院呢。”
早晨6点过3分,我、母亲、二姐3个人,从二姐家里出来。
我们提着米粥、中药,去医院看望父亲。
这天,天气尚好。
走在街道上,不时地听到有公鸡的叫声。
也不知道,是谁家养了几只大公鸡,在欧欧地叫。
在城里,应该是不允许养鸡的。
可是,怀化城里,却有怀化城的特色了。
巷道里,几乎看不到任何行人。
我们三个人,一直默默地朝医院走。谁也不说话。
到了主街上,我们碰到了昨晚在医院守护父亲的二姐夫。
二姐夫正在往家里赶。
二姐夫说:“昨晚11点多,你们离开医院后,爹只屙了2次尿。最后一次尿,还是今天清晨屙的。”
二姐夫名叫覃复长。原来生得单单瘦瘦,这几年,有些发福了。看上去,倒像个城市里的局级干部。
二姐夫的命运,与我父亲有些类似。
二姐夫3岁时,他父亲烧石灰,掉进了窑洞,被活活烧死。5岁时,他的母亲改了嫁。后来,他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过生活。爷爷奶奶膝下的儿女又多,生活相当困难。加上二姐夫小的时候喜欢哭,曾惹怒了一个叔叔,被叔叔强行扔在猪栏里,和猪睡了几个晚上。爷爷奶奶发现之后,抱起他,痛哭不已。
二姐夫与我二姐结婚后,1980年遇到田地调整,二姐一直又分不到田地。家里的粮食,也就远远不够他们吃。
我父亲,很是牵挂他们家。经常挑着粮食过去,给他们补济口粮。
在我印象里,二姐夫经常穿着一双皮凉鞋。是那种废旧轮胎割制的皮凉鞋。像两艘黑色的小船。脚背上面,则是两根黑色的橡皮带,给牢牢地绑着。二姐夫穿着它,忙碌于山间、菜地、田中。
女儿树英和儿子中华,相继降生,既给二姐夫脸上增添了笑容,也给他内心增加了不小压力。
二姐夫不是那种干活特别舍得死的人,他比较讲究劳作适度。但他又十分注重对儿女读书方面的启发和引导。那样的困苦环境,也就进一步锻造了我二姐吃苦耐劳的本领。
二姐过早地走上了既农又商的道路,成了当地较早从事衣服零售的农村妇人。
二姐到城里进货,在乡里逢集摆摊叫卖,挣着那份辛苦钱。
二姐夫俩口子,咬着牙齿,供养着他们那对儿女读书。特别是儿子中华,复读了3个高中。硬是考上了大学。
如今,二姐夫的一对儿女,都成了人民教师,都在城里工作。二姐家的日子,才日复一日地好转起来。
二姐夫是个性情豁达、富有远见的人。他说,从前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也该懂得慢慢放手了。二姐夫要享受这种难得的生活。
前几年,二姐夫看到父亲回老家挖茶油山,摇头感叹说,爹这么大的年纪了,还不懂得放手,真是服了这个老爹了。
在二姐夫心目中,我们的爹,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但又是他永远学不到、学不足的榜样。
主要是父亲那股子蛮劲。条件好了,手脚还不舍得停歇。天生一个勤劳的农民!
早晨6点40分,我们赶到了医院。
我们还是来晚了。
大姐早就到了。
没多久,弟弟也赶来了。

二姐和大妹,正在给父亲用温水擦背。
我、大姐、弟弟,一起扶着父亲,帮他换衣服。
我们给父亲洗舌头、装假牙。然后,又抬扶着父亲,坐上轮椅,推父亲到医院后门的林亭里去。
二姐开始给父亲喂米粥。
父亲只吃了八九口,就不想再吃。
父亲坐在轮椅上,毫无精神,眼睛微闭。
早晨7点10分,大姐夫摇摇摆摆地从家里走来了。他来看望父亲。
父亲尚还认识大姐夫,对他主动地微微“嗯”了一声。
这几天来,父亲是很少主动跟人打招呼的。
今天大姐夫来了,父亲能“嗯”出一声,说明大姐夫在父亲心中很有份量。
父亲一定是在怜惜着他了。
大姐夫名叫廖拾妹。一个很遭人现眼的女人名字。可他却是个男人,而且是个身材魁武、相貌耐看、性格温和、能吃得苦、能与厄运抗争的大男人。
先是大姐一连生了4个女孩,从第3个开始,大姐和大姐夫就当起了“超生游击队员”。他们过得躲躲藏藏的“逃生”生活。直到第5个是男孩,他们才肯安心回老家定居,安心务农。
大姐夫打拼了十几年,没打拼多少财富出来,却拼出来一身的病。
先是痛风。脚肿得发亮,长期打针、吃药。打着,吃着,毛病就越来越多:血管有问题,装进去2根支架;喉咙有问题,做了活检,做了化疗。头发脱了,牙齿松了,舌头一两年都尝不出酸甜苦辣来。
接下来,肾脏有问题,血小板有问题。进了几次重诊病室。
后来,糖尿病转化成了尿毒症,从死里来,往死边去,再从死里过来。长期靠透析维持着。自己动手,一日2次。
如今,大姐夫的腰上,长期插着管子。身旁,长期托着药水袋。到哪里去,都不是很方便。
父亲曾隔三差五去看他,鼓励他说,再有困难,也要熬住,不能放弃啊,不能让白发人来送黑发人。
大姐夫总算是熬过来了。
他听进了父亲的教诲,遵循着人间的原始孝道。
今天早晨,父亲对大姐夫所“嗯”出的那一声。应该是父亲心底里的一声呼唤。父亲希望大姐夫好好地活着,好好地面对人世间的病痛,好好地迎战死对生的折磨。
父亲现在是大姐夫的榜样,他是在做给亲人们看的!

松桃打来了电话,询问起父亲的情况。
松桃已经为内弟家的岳母做好了早餐,正在去三医院的路上,为我的岳父送早餐。
她想赶在医生查房之前,再了解一下她父亲的病情。
还好,岳父这几天,病情有所好转。这让松桃多少也宽了点心。
大妹告诉我说:“昨晚,护士查房时,说爹的肚子,也浮肿起来了。”
我撩开父亲的衣角,用手按了按他的肚皮。觉得很胀,也很硬。
弟弟今天要回一趟穷天老家。
父亲一天不如一天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往坏处想。
我和弟弟在病房外面,商量着砍树和搭台板的事情。老家的条件那么差,屋边的过道那么窄,需要扩宽。否则,去的人一多,大家都会屁股挨屁股的。
大姐站在父亲的轮椅后面,双手抱住父亲的头,说:“爹,你把眼睛睁开,四处看一看罗。出太阳了!”
父亲微微地吟了一声。
泛开眼,马上又闭上。
父亲仰着头,倒在枕头上。喉咙里,呜呜地呻吟。
我们推着父亲回到病房,然后又抬扶着他上了病床。
这时,小妹夫胡德良来了。小妹夫昨晚开了一夜的运土车,特地抽空过来,探望父亲。
小妹夫已经吃过早餐。我要他和母亲,暂时留下来,守护父亲。
然后,我和大姐、二姐一起,到街上吃早餐。
中途,我们碰到了三姐。
三姐说:“我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大姐夫,我和大姐夫说了一阵话。大姐夫说,今天他去三角坪,找一找人,帮父亲算一算今后离世的良辰吉日。”
也真难为大姐夫了。他自己也是个重病在身的人,还要这么四处奔波。太麻烦他了。
我们4人,在辰溪人开的一家“台湾水饺店”,各自吃了一碗水饺。我还给母亲备了几个,一并带回。
今天的太阳,依然很毒,照得大地,亮闪闪的。
医院的走廊里,全都住满了病人。一波一波的。
有的人,活着出了院。
有的人,无奈被转院。
或者是被运出去,等待着死亡。
人们在这里抗争着,在这里求生辞死。
我可怜的父亲,你是否能够闯过这一关呢?
父亲喉咙里的声音,嘈杂怪异。呼吸道里,聚集着废气和残液。它们凝结着、加固着,形成一种韧性强、黏合度高的痰。它们堵塞着父亲的气管,阻碍着父亲的呼吸,给父亲以额外的摧残。
上午9点多钟,贤朋叔提着2个西瓜,从乡政府上来,看望我父亲。
三姐轻轻拍着父亲的手臂,说:“爹,贤朋叔看你来了。”
父亲微睁双眼,朝贤朋叔这里注视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闭上眼。
父亲没了一丝力气。他不能说话了。
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向前来看望他的亲人们,打打招呼,以示感谢。
贤朋叔说:“我是听到你们大舅娘说的,后来又听到安崽哥说,大哥你病了,而且很严重。我养了几百只鸭子,那几天走不开,今天才上来看哥哥你了。”
贤朋叔也是我的族叔。上溯三代,我们同一根血脉。
贤朋叔的爷爷与我的太公是兄弟,后来却不在一个生产队生活。他们搬到了大队部旁边的胡家生产队安家落户,我们则一直生活在穷天生产队。我们的距离,隔了几座山,有四五里路远。
算起来,胡家生产队那边,有我们族叔先辈。他们是三兄弟。名字都取得有些怪:梗脑壳和尚、满心、齐苍。
这三位先辈,都在那里繁衍着自己的子孙。算起来,那边的同脉亲人,也有十几号人了。
贤朋叔就是满心爷的长子。他是那边族叔及表兄弟当中,目前搞得最好的一个。
贤朋叔的事业,主要是在养殖上。这些年,他一直养猪,经济方面,有所宽松。
他还在乡政府旁边,建了房子,成了“奔乡”之人。
然而今年,非洲猪瘟一流行,乡里死了不少猪。为了减少损失,贤朋叔请来乡政府的人,电杀了自己所养的数百头猪。遭受的损失,仍然还有四五十万元。
猪被电杀了。他就养鸭子。养了数百只鸭。贤朋叔就是靠与禽畜为伍,发家致富的。
他是我们家族中值得骄傲的人物。
父亲一直很看好贤朋这位族弟。
每次回老家,父亲都不忘要去看一看他。给他一点鼓励,一点自信。
父亲总是说,在农村,就得有个做派。不做,哪里会有呢?看看贤朋,全靠自己辛辛苦苦养猪,才有了一个出头之日啊!
现在,病床上的父亲,再也没有气力,夸奖我们的贤朋叔了。
父亲现在说话,很是艰难。如果放在前几天,父亲一定会问起贤朋的养猪情况。现在猪瘟流行,父亲肯定为他担心的。
贤朋叔走近父亲床边,握着他的手,说:“大哥,心里还舒服吗?”
父亲摇了摇头。
贤朋叔转过身,对我们说:“大哥他现在,心里还是清楚的,就是讲不出来了。”

送走了贤朋叔,我和三姐,去找刘医生。
我们要好好问一问父亲的情况。父亲他现在,到底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
前前后后,已经有3位医生,来看过我父亲了。他们建议我们:放弃治疗,早点把老人家运回老家去。
刘医生一见到我们,就说:“你们父亲的病,每况愈下,今天和昨天比起来,又差了许多。主要表现在肝脏部分,全被癌细胞给包围了。因此,我建议你们,早点考虑出院,早点送老人家回老家,留住一口气。”
母亲和大姐,坐在病房里。小妹夫开车去了弟弟家,他是去取父亲的衣服。
母亲说:“把你们爹的衣服取来,分给7个子女。每个人留1件,就当是对你们爹的一种留念。”
三姐听了母亲的话,一下子就哭了。
三姐说:“爹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衣服,都是穿两个儿子的旧衣服。大家给他买的那些衣服,他一件都舍不得穿。现在都来不及了。很多衣服,爹都没穿过一次呢!”
我们的眼泪,不自觉地溢了出来。
个个都在抽泣。在擦拭。
我打电话给弟弟,把刚才刘医生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他。
弟弟已经装着一车夹板,正在杨村的路上。
弟弟说:“我把板子卸下来后,马上就回来,再商量什么时候,把父亲运回老家。”
中午时分,儿女们聚集在3楼的走廊里。
大家商量着,是否同意父亲出院,是否同意运父亲回老家。
儿女们大多数的意见是:赞成父亲出院回老家。
因为,医生已经建议了,尽早让我们父亲回老家,以防不测。
但是,我们的这个想法,也得征得父亲的同意啊!
因此,就派大妹进去,事先征求父亲的意见。
大妹对父亲说:“爹,我们今天回老家去,好吗?”
父亲不做声。
又问了几次。
父亲有点气愤了。
父亲回了两个字: 不去!
父亲不想回去。
这就难办了。
我们必须征得父亲同意!
否则,我们这样做,就是不孝,归雷劈!

中午过后,同村的贤友叔和他老婆满婆婶来了,他俩特来看望父亲。
我们叫醒了嗜睡的父亲。告诉他,贤友叔俩口子,看他来了。
父亲疲倦地睁开双眼,嘴唇蠕动了一下。像是在问候和感谢这位村里的能人。
说贤友叔是穷天老家的一位能人,这不是高抬他。往上追溯五代,我和贤友叔,也是同一条血脉。
贤友叔年过古稀,个子依然高大,脸也宽泛,眉毛很浓。有几根眉毛,高高地卷扬着,和电视里的曹操有点接近。
父亲当了十几年的生产队长,贤友叔后来也当了大队干部,两个人在职务方面,有一段相互磨合的年代。
在率领村民开荒造田、修建水库的事情上,贤友叔对我父亲,一直充满着由衷的敬意。
贤友叔的近亲族兄弟较多,他们那一大家子,在我们穷天老家,说话是绝对有份量的。
念过高小、文化高、个子高、人机谋、口才好、兄弟多的贤友叔,在他们那一大家子中,算得上是最为出色的人物了。
贤友叔可以不把老家其他人当能人看,但他绝对会把我父亲当成能人。他佩服我父亲。尽管,我父亲没读过一天书,没识到一个字。
贤友叔佩服的,是我父亲的口才和胆量。
主要反映在卢桐冲那块山上面。
卢桐冲是一个树木茂密、常年溪水潺潺、清澈无比的好地方。青山绿水,荒无人烟。
我们老家的先辈们,就是靠着这块丰茂的大山,在那里砍树、烧炭、砍柴、摘野果、挖中药、割树皮、捉野禽野畜,讨乡村的山里生活。
那一年,相邻的小岩村与我们生产队,就卢桐冲的归属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他们要求,将该山划归他们所有。
这真是让所有穷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了。
穷天人的祖祖辈辈,都在卢桐冲,讨山林生活。现在,一下子要归小岩村了。大家就是把后脑壳上的头发全部拔下来,也是想不通的。
关键是,公社里有个小岩村的人当领导。他也在暗地里,操纵这件事。
全村的人都把目光,盯在了我父亲和贤友叔身上。
在这件事上,公社有人在撑腰,大队领导也就变得沉默、为难了。甚至,开始模棱两可,开始倒边了。
大队领导问我父亲说,你是穷天的生产队长,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父亲说,这还有什么好认为的呢?这就好像,你天天晚上睡的婆娘,现在有人说,你婆娘是他的了,要你婆娘跟他去睡,你能同意吗?
大队领导真是想不到,我父亲会把山和婆娘相比,而且又问他同意么,这让大队领导感到非常恼火。
虽然,我父亲的话里,有着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大队领导没想到,我父亲竟然会这么说出来。于是,也就撒手表示不管了。
大队领导撂出来一句话:鸡窠罗,你自己去跟公社书记去说吧!我们也不好怎么说了,搞不清楚了!
照理说,我们穷天生产队,是归四卧龙大队管辖的,和我们争山的那个生产队,是归小岩大队管辖。大队里的领导,应该帮我们生产队说说话才是。可他们把公社个别领导的招呼,当成了最高指示。他们在努力做我们穷天生产队的工作了。
然而,在我父亲这里,大队领导却碰了一鼻子灰。
贤友叔当时也在场。他被我父亲的正气和傲骨,深深地折服了。
我父亲果然跑到了公社。
接待他的,恰恰又是小岩村那个当领导的。
那人拿着一份写好的证明材料,要我父亲在上面签字。
我父亲说,我不认识字,你读一遍,我听一听。
当父亲听到判卢桐冲为小岩村所有时,立刻说,那你帮我在上面签字吧。
那人立刻就高兴起来了,拿起笔,准备代签。
我父亲说,你帮我在上面写上:穷天生产队队长杨贤云,坚决不同意!
那人呆了。
父亲又去找公社书记。
父亲跟公社书记摊牌说:书记啊,如果将卢桐冲的山,划给小岩所有,那么,今后所引发的村民争斗,打死人的事,公社里应该承担责任。
父亲的这句话,这才引起了公社书记的高度重视。
半年下来,事情彻底查清了。卢桐冲的那遍山林,维持原状。
卢桐冲,仍然是我们穷天生产队的卢桐冲!
父亲昏睡在病床上。
父亲现在的思维,已经浸泡在痛苦之中。
父亲当年那股卢桐冲的维权精神,可能在支撑着他,与死亡抗争。
贤友叔又与我聊起了卢桐冲如何养育穷天人的诸多事情。花了将近40分钟。
在此过程中,床上的父亲,一直没有任何言语。
偶然,父亲微开着眼皮,望着这边,眼里泛出无助的光。

三姐的二媳妇芳芳,对待我父亲,算是用了真心了。
我父亲是她的媒人,也是她的外公。
芳芳从小就没看到过自己的外公。她刚把媒人转化成外公不到二三年,外公却要悄然隐退,甚至消失。这是她非常不愿意的。
芳芳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舅舅,芷江路那边,有一位老中医,我认识他。他还给我一位同学治好了乳房,很厉害的。他说,可以过来看一看外公的情况。我要不要把他请过来?”
我说:“那就试一试吧,请他过来。”
芳芳立刻坐上小妹夫胡德良的车,去接那位老中医。
不到一个时辰,老中医来了。
老中医穿着一身青色麻布休闲衣服,手腕上还戴了一串佛珠。说起话来,温和,文雅。
老中医为我父亲把了把脉搏,然后说:“太晚了,全部腹水了。”
老中医又说:“你们应该把老人家运回老家去,以防出事。”
看来,老中医并不是什么江湖郎中。他也表示“晚了”、“无能为力了”。
听了老中医的话,我心里又忧虑起来。
于是给弟弟打电话,说,有位老中医,来给父亲把了脉,也建议我们,把父亲运回老家去。
我要外甥方才,再去试探一下父亲的意思。
方才靠近父亲的头,轻轻说:“外公,我们回老家穷天去吧,好不好?”
没想到的是,这一回,父亲却说“好”。
父亲同意回老家了。
我立刻给弟弟打电话,说:“你马上赶过来,爹同意回老家去了。”
我把在场的所在亲人,叫到三楼走廊里。
大家一起商量着父亲回老家的方案。
现在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母亲说:“这个时候回去,赶到家,恐怕天都漆黑了。还是明天走为好。”
我们也觉得,母亲说的很对。
于是,又改变了计划,决定明天早晨7点半之前,让父亲出院。我们陪父亲回老家。
然而,陪父亲回老家的人,实在太多了。明天需要运送的物品,也实在太多了。
于是,又确定了一个计划:我、大姐,小妹、母亲,先留下来,在医院守护父亲。其余的人,开几辆车,马上回老家一趟。主要是把老家的房屋卫生,打扫一下,把床铺弄好,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下,为明天大队人马回老家,做好准备。

父亲要屙尿了。
我们将他扶起来。
小妹给他擦拭着背,又给他换了一件干净衣服。
可是,父亲屙了十几分钟。一点尿也屙不出。
不得已,又让父亲躺下去。
对面一位病友的家属,买了一碗面条,正准备吃。
我们问父亲:爹,你想不想吃面?
父亲竟然想吃。
我们从对面分了小半碗面。
小妹给父亲喂,全吃完了。
太好了!
父亲能够吃那么多面了!
我们问父亲:还想吃什么?我们马上去买、去给你做。
父亲摇了摇头。他表示,什么也不想吃了。
下午6点半的时候,三姐夫来了,他过来接班。
小妹夫开着车,载我和小妹,去弟弟家吃晚饭。
弟媳妇冯梅在家里,负责弄几个人的晚餐。母亲和大姐的晚饭,也在这里,需要带一份过去。
吃完饭,我、小妹、小妹夫、冯梅、柳毅、柳彤6个人,挤坐着小妹夫的车,往医院方向走。
这时,松桃打电话说,她正从天星坪那边过来,想看一看父亲。我们在中途,将她一并带回了医院。
进了病房,友松舅舅已经吃过晚饭,坐在病房里。他守护着我父亲。
不久,弟弟一伙人,也从老家回来了。
他们累得精疲力尽。
晚饭后不久,松桃的姐姐喜桃,以及姐夫杨英孝,从天星坪那边走路过来。他们俩,还代表我的岳父岳母一家,特地来看我的父亲。
岳父现在自己重病在身,住在医院,岳母呢,经常头晕,身体虚弱,还时不时地要到医院招呼着我的岳父。
他们两位老人,一听到我父亲病成了这样,一个放肆地摇头,一个变得愁眉苦脸,都表示:我的父亲太遭孽了。
我和松桃结成夫妻,才使得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与一个干部家庭有了一种水到渠成的和谐。
那时,我岳父在我们新建乡当副书记,是一个地道的政府官员。而我的父亲,只是新建乡一个山村里的农民。
你想想,如果不是我与松桃的这种缘份,他们能够平起平坐、亲如兄弟、相互挂念吗?
岳父岳母行动不便,不能亲自来看我的父亲,他们特意委托他们的大女儿陈喜桃俩口子,带来了问候、祝福和安慰。
父亲平时也是很惦记着我岳父岳母的,经常通过我,去打听他们两老的身体状况。并交代我,一定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是松桃的父母,关爱他们,也就是关爱松桃。
这,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孝道法则。
爹,我记住了!
喜桃和我妻子松桃的名字,只差那么一个字。然而,她俩姊妹的性格,却大不一样。
喜,表示欢喜。因此,喜桃看到什么东西,都可以挖掘出它的某些笑料来,然后眯着眼睛,笑嘻嘻地,甚至还会打哈哈,有时真的像一个快乐的神仙。你如果不特别了解她,你永远都不会察觉到她心里的苦闷,她始终会以一种乐观向上的风貌展示给你。
松,当然是松树,挺拔,耿直,不为风雨所动。松桃就有这点品味。她喜欢有一说一,里里外外放肆地做事,不叫苦,不喊累。
总而言之,岳父岳母的这对宝贝女儿,我都熟悉她们的性格。一个是我的妻子,一个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外加姐姐。我经常叫这位同学姐姐为“陈校长”,喊得她满嘴哈啦哈啦地笑。
现在,“陈校长”一点笑意都没有了。
她看到我父亲病成那样,眼泪在一颗一颗地滴下来。
她对我说,平时看到你爹,身板那么硬,幽默无比,得了这种病,几下子就变成这样了呢?真是让人心痛死了。
“陈校长”抹了一把眼泪,去摸我父亲的手。
父亲呆呆地看着她,似乎没有多大的反应。
要是在往常,父亲肯定和她聊上了。
我靠在父亲耳边说:爹,是喜桃和她家英孝,看你来了。青青的外公外婆,走不动,也托她俩来看你了!
父亲点了点头。想说什么。却又说得不明白。
今晚,我留下来,守护父亲。
友松舅舅,也想留下来。
友松舅舅是我的满舅,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看到姐夫现在病成这样,知道不会长久了。他表示,一定要留下来,守护姐夫一夜。
夜,就这么越来越黑。
我们铺好陪护床,动员其他人,回去休息。
明天,大家还要赶早,我们一起护送父亲回老家。
晚上9点,贤友叔打来了电话,问起我父亲的情况。
贤友叔不仅会木匠活,还会油漆活,还懂些医术。他今天看了我父亲的情况,可能是知道,我父亲不会太久了。
晚上9点50分,我看到父亲扬了扬他的右手。
我立即趴过去,问:“爹,是不是想屙尿了?”
父亲有这个意思。
我和满舅,立刻忙活起来。移开陪护床,摇起父亲的病床,帮父亲褪下短裤,让他斜躺着。
我找来尿壶,对着父亲的排尿处,小心地对准着、斜置着。
没有尿液流出来。
我对父亲说:“爹,你屙吧!放心屙就是了。”
还是没有尿液流出来。
我提着父亲的隐私,抖了抖,耐心地等。
终于,尿流不止!
足足有半斤的量!
这是大好事!
这样,我艰难的父亲,就会减少许多痛苦!
我提来一桶温水,帮父亲擦拭着他的私处、大腿、屁股。
我想用这种干爽,为父亲在艰难中求得一份舒适。

夜晚10点半,病房里的灯全熄了。
我躺下来,倾听着父亲艰难的呼吸声:嚯……扑……嚯……扑……
那里面,夹杂着父亲无限的痛苦。
我能感受到。
大妹的儿子周芬,黑夜里,也进来了。周芬是来守护外公。
我让我很感动。
这个曾经异常调皮、很不听话的小外孙,曾让我的大妹几乎天天流泪,天天叹气。
父亲为了周芬的事,经常上门安慰着我的大妹。
周芬读书不行,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想读书。
小小年纪,只知道上网吧、玩游戏,有时还偷些铁丝去卖。
一家人都为他担心,怕他学坏。
任何人教育他,他只知道死埋着头,一声不吭。
最让人感到恼火的是,骂他几句,他就往外跑,不归屋。
碰到这样的儿子,哪个不会伤心呢。
我曾一直为大妹担心着,我怕大妹会因为这个周芬而疯掉。
人在变,天在看。
周芬这几年变好了。
虽然离了婚,还拖养着两个女儿,但他学了一门岩洞喷浆的技术,也能挣到钱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任性、玩皮、不听话了。
父亲病倒后,他特地从远方赶回来。他也是我父亲躺在病床上,唯一长时间对话的一个晚辈。
就凭这一点,周芬是能感受到外公的情意的。
周芬这个时候进来,要求守护外公,也是他对外公的真诚回报。他可能也感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聆听外公的苦心教诲了。
我、友松舅、周芬3个人,将为父亲,守护他住院的最后一个夜晚。
晚上11点40分,大姐的大女婿张静,深夜里进来看望外公。
他看到床上的外公,病成了这个模样,艰难到了这种程度,摸过去,握住外公的手,泪水直流。
明天,我们将回老家。
和我们的父亲一起,回到那个生养过父亲、也生养过我们的老家——穷天。
(本篇写成于2019年9月28日。2022年11月1日夜,于长沙家中稍作修定。)
请看续文:《陪父日记》(第 14 天)
关于本纪实作品的几点声明:
1、本纪实随笔,写作于我父亲去世后的两个月里。当时,父亲在生病住院期间,国内还没出现新冠疫情。因而,我们七姊妹才能够日夜守护在医院里,守护在父亲的身边,直到他离去。我这个日记体系列性文字,写作于2019年9、10月间。父亲病重至离世期间,国内无疫情,这也是上天对我父亲的恩赐。
2、本纪实随笔,于2020年发表在本人的微信公众号上。曾经感动过许许多多的亲人和朋友。我是凭自己的真情和泪水,用文字挽留父亲。我希望父亲活在我的文字里。如果读者还想阅读本人的其他文学作品,可添加本人的微信号ycd0070,我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阅读欲望。也真诚希望读者朋友对我的文字,给予批评指正。
3、本纪实随笔,现特推荐给 “齐鲁壹点” 网络平台作为首发。读者也可在“今日头条”、“百度”网络平台上阅读到该作品。但是,本人在此声明,拒绝新浪网对该作品作“手机新浪网”发布。因为我有几个阅读量较大的作品,一经“手机新浪网”强行发布后,读者们所留下的所有评议性文字全部就被屏蔽了。
4、本人坚决反对:网络上某些靠流量赚钱的所谓写手们,肆意将本作品强行拖至其个人账号上,再次对外发布,以为其赚取所谓的流量。对此,本人将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
5、本长篇纪实随笔作品,共21章(21天的内容),约16万字。若有出版社看好,可直接与我本人联系出版事项。联系微信ycd0070。
作者简介:
杨崇德,男,1965年10月出生,湖南怀化市中方县人。1995年加入湖南省作协。曾在全国两百多家报纸、期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近千篇。数百篇被《作家文摘》、《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杂文选刊》、《读者》、《故事会》等刊物转载。上世纪,本人曾被《微型小说选刊》列为“微型小说百家”之一。2010前后,本人出版了文学作品集《故乡的云朵》、《冬天的生活》、《丛林狼》、《麻麻亮的天》等。有作品曾获《小说选刊》2014-2015年度“读者最佳印象奖”。有作品被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发行。有数篇作品被全国50多所重点中学选为语文考试分析试题。本人系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理事,现任湖南省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
壹点号崇德随笔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