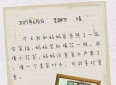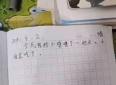1
周末晚十点,杨涛在酒吧唱到第二首歌时,被人砸了场子。为首的混混泼了杨涛一杯酒,余下的人起哄、喝倒彩。
申小玲从后台抄了根钢管出来,逮着那帮混混就抡。
她也算半个练家子,早年在大街上摆摊儿躲城管,成天抄摊儿就跑,练出了一身腱子肉,反应贼快。一棍子抡下去,不骨折也够人哼唧半天的。
挨了打的也不敢下死手打回去。毕竟申小玲是个女的,男打女有点胜之不武。所以除了自认倒霉,骂两声“杨涛你个怂逼躲在女人后头算什么男人”,也没别的招儿了。
唯一被申小玲追着打、还龇着牙乐呵的,是王奎。
王奎坚信,如果没有杨涛,他肯定能追到申小玲。
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他跟申小玲这样从小没人管、烂泥里打滚儿的贱胚才最般配。
杨涛是大学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到酒吧唱歌的。他从小爱唱,家里觉得搞艺术太扯,死活不让报音乐学院,逼着选了个机械专业。毕业后找工作碰壁,母亲去世,父亲另娶,后妈又添了个小的,他懒得回家,就找了个外省县城的酒吧驻唱。
反响还不错,头几天场场有人喊“安可(再来一场)”,喊得最凶的是申小玲。第一个给他送花儿的也是她。
申小玲的正式身份是对面西餐厅的收银员,非正式身份是女混混。她帮杨涛先后踹走了好几个故意找茬的小流氓后,拍着杨涛的肩膀冲他脸上喷烟圈:“以后姐罩着你,谁敢来找你的茬,姐打得他满地找牙!”
大概她太野太有名,杨涛还是从别人嘴里才得知,原来自己跟申小玲是情侣关系。
他没有很高兴,也没有不高兴。说不上喜欢,但也不反感。
人心若是空空,就愿意一切随缘。什么都无所谓,怎么样都行。
这一次闹得太狠,胳膊拉伤,还蹭破了皮,流了不少血。把申小玲送进医院,杨涛说:“下次别逞能,没人让你护我,让他们打我一顿,以后就消停了。”
“说什么呢?有我在,谁敢打你?你这么说,瞧不起谁呢!”
杨涛笑了一下:“没听他们骂我么?怂逼,缩头乌龟,我敢瞧不起谁?”
“你是个文化人,他们就是一帮臭流氓,难不成你跟他们比拳头?他们说什么,你权当放屁得了!哎呀,医生你轻点儿,疼!”申小玲疼得直吸气。
2
杨涛的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他没管。那是他前女友发来的。
杨爸给杨涛走关系找了个稳定单位,巧的是杨涛的前女友也在里头。
问了才知道,杨爸之所以能把杨涛安排进去,前女友她爸使了不少力。当初因为前女友脾气不好,杨涛伺候够了,分了。分了没多久他换了号码,前女友也是最近才通过杨爸联系上他的。
杨爸情真意切:“你回来吧,给你安排的是个闲职,你有的是时间玩音乐。莉莉跟你分了以后很后悔,要死要活的,她爸爸也没辙,全依了她。她爸说认识音乐圈的朋友,你要真想朝那方面发展,他可以给你引荐……”
前女友更是梨花带雨:“爸爸说了,只要你回来,他就同意我们结婚。婚房都看好了,咱两家各出一半的钱,我们家还负责装修。杨涛,你走后这一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没有一天不想你。”
申小玲的胳膊养了小半月,每天吊着膀子去酒吧,一场不落。好像她不在,就会有人把她的心上人给吞了似的。
杨涛每次在台上看她,她要么举着一瓶啤酒边傻笑边灌,要么抱着大袋薯片消磨,笑得见牙不见眼。时不时咬着指头吹两声口哨,或待他一曲终了冲台上特夸张地喊“安可”。
以前杨涛觉得特丢人,久而久之习惯了,瞧她那卖力劲儿还挺想笑。
而现在,只剩心酸。
他想,一个人究竟有多快乐,才能像她那样毫无保留地笑啊?
他不知,这些快乐其实都是他给她的。
王奎见申小玲一个人缩在角落里乐,腆着脸凑上去:“那小子有什么好?把你迷得五迷三道?再迷,你俩也不是一条道儿上的人。人家一线城市的本科生,能娶你?你俩到一块儿有话说吗?”
“嘿!”申小玲这暴脾气,单手把人提溜进后台,一脚反踹上门,揪着人衣领钉墙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老大隔三差四找杨涛的麻烦,是你撺掇的,对吧?我跟他是不是一条道儿上的你管不着,但我跟你肯定不是一条道儿上的,你丫趁早死了这条心!”
王奎在她身后大嚷:“瞧你能高兴几天,人家爹都找上来了。两个人在贵宾酒楼吃的饭,老子都看见了。人家迟早要走的!”
申小玲步子一顿,几秒后,扔出一句:“管好你自己吧!傻逼!”
3
杨涛走的那天,风很大,申小玲在杨涛的出租屋的床上发着烧。从两天前他说要走,她就开始生病。
他把他爸、前女友、前女友的爸,跟他说的那些话,给的那些承诺,一字不落告诉了她。包括他当初来这儿的原因。
他语速缓慢,态度诚恳,不疾不徐,天生温吞,“小玲,我来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过渡。我没想过留在这里。我的家人、朋友,所有熟悉的东西都不在这儿。我在这边没有归属感,没有前途,始终像个外人。我从一开始就没给过你任何承诺。你对我的好,我很感激……”
“行了,别说了,我明白。”申小玲抖着手给自己点了根烟,才吸一口,就呛出了泪:“什么破烟,呛死了。你哪天走?我送你!”
“后天。”
“卧槽这么快!”
就是这么快,快得她来不及反应,快得她连替自己筹谋争取一番的时间都没有。
他确实没有错,是她自己贱。
当初她卷了铺盖去给人暖床,一夜不合眼盯着人后背看,也没看出朵花儿来;一大早给人煎蛋做早餐,烫了一脸的油,把厨房弄得一片狼藉,被人说邋遢;洗衣服忘了给人掏兜,泡烂了人家的东西,被人冷着脸问“你怎么这样”;找段子说书逗人开心,被嫌聒噪;亲了人一口,人家一脸嫌弃,恨不能立马掏纸巾擦嘴……
可是,她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啊!喜欢就喊,讨厌就骂,开心就笑,不爽就打。从来都是直来直往的啊!
没有人教过她要怎么爱一个人,没人教她爱一个人要怎么端着,不能太放肆,要懂分寸,知进退。也没人告诫过她,对谁都不能毫无保留,更不可飞蛾扑火,两眼一抹黑。
她生来不懂规则,条条框框自己定,一切全凭喜好,到头来,伤了自个儿连个问责的都找不到。
就在那天晚上,她冲了个冷水澡。冷水侵身,冰刀刺骨,出来时牙齿打颤,他却已经不见了身影。
告别的话已经说了,他怕再睡一屋会尴尬。更怕她哭,自己去找了个宾馆住下。
她连睡衣也懒得穿,就这么光着往床上一倒,天旋地转。
苦笑。怎么连个分手炮都不打?然后开始哭,一直哭到半夜。
醒来就喉咙痛,心痛,眼痛,哪哪儿都痛。
4
后天早晨,她已经烧得爬不起来。酒吧一姐们儿打来电话,说王奎他们今儿要动杨涛。都知道他俩掰了,还知道他要走,打算在车站截他,狠削他一顿。
但那天,杨涛安然到站,买票、检票、过安检、上车,全程无碍。
他不知道的是,在距车站十几公里外的路上,顶着40度高烧的申小玲骑着摩托狂撵了王奎一路,一边撵一边给前方小汽车里的王奎打电话,操遍了他祖宗十八代。
电话来不及收,车轮一拐,眼前一黑,申小玲连人带摩托撞到路边的树上,头盔都裂了。
送医抢救,浑身好几处骨折。另外,流产了。
王奎红着眼睛捏着诊单难以置信,嫉恨使他面目全非。他咆哮一声冲出去,哐啷一拳砸了洗手间的镜子,吓得几个病人哇哇乱跳。
申小玲的脑袋支棱在塑胶脖套里,一动不动。
她例假向来不准,三个月没来也没在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怀上的,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半个月后胳膊能活动了,她给杨涛打了个电话。才接通,那边传来一个女音,在问杨涛谁呀。杨涛没吭声。
申小玲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脑中飞速运转,最后只说了句:“酒吧又来了个唱歌的,没你高,没你白,没你好看,也没你唱得好,唱完也没人喊‘安可’……”
“十八床量血压!”护士清脆的嗓音忽然闯入。
那头杨涛显然听到了,意外又警觉地问:“你在医院?怎么了?”
“陪小圆治病呢!咱们餐厅的小圆,记得不?她给他丈夫打了。”
好心前来探望伤员的小圆瞪大眼睛:“你说啥呢?烧糊涂了吧。”
5
杨涛再回小镇已是三年后。
他离了婚。这三年里,他跟妻子的相处,与复合前并无两样,就连争执的内容都丝毫未变。工作枯燥,百无聊赖,闲暇时候弹唱遭妻子数落不思进取。岳父再不提给他引荐某某音乐人的事,倒是常敦促他要多跟领导搞好关系,以后才好晋升。
一次他去酒吧喝酒,有个驻唱的男歌手唱了几首民谣。他坐在角落里一边喝啤酒一边嗑花生米。另一边的角落里不时有人拍手叫好吹口哨,间或爆出一两句高调的“老公我爱你”。
他忽然泪流满面。临走,喊服务员递了一百元小费上去。
杨涛坐了三小时的动车到省,再转两小时大巴到县。下车时心砰砰乱跳,到了那条熟悉的街道,已是百感交集,手心里直冒汗。
明明不是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却近之情怯。
酒吧还开着,对门儿的西餐厅也在。一脚踏进酒吧,全是生面孔。台上无人唱歌,台下也无人喝彩。除了老板和吧台小张,只有年长的两个阿姨还在。
他们把杨涛围着问长问短,小张给他调了一杯鸡尾酒。
一番寒暄之后,他问:“申小玲还在对面吗?”
老板笑得意味不明:“在,在。”
他又问:“龙哥他们呢?”
老板的笑意更深:“你是想问王奎吧?你走后,王奎成天跟在小玲屁股后头转。小玲也没给人好脸色。小玲这人哪,她认准了的,能扒心扒肺地对你。她看不入眼的,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要不怎么那会儿宁可自个儿掏钱请护工,也不让王奎伺候呢!”
“护工?”
“你走的那天……哎呀我忘了这事儿你不知道!”
“什么事?”
“就你走的那天吧,王奎他们要去车站堵你。小玲顶着高烧骑摩托追了一路,半路栽了,好几处骨折,在医院躺了俩月。还……流了产。”老板把头偏过来,跟他咬耳朵:“那孩子,是你的吧?那天要不是小玲,你少不了挨顿削。我看哪,还不如你挨那一顿呢,总好过她差点送了命……”
6
杨涛不记得是怎么从酒吧走出去的,出了那门儿,眼睛酸胀得厉害。他在茶餐厅对面儿的一片树荫下站了很久,迟迟不敢上前。
“茉莉茶餐厅”,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给太阳光照得晃眼。
直到傍晚,餐厅的门帘一掀,一个大肚子女人从里头缓缓走出。
她捧着肚子,步履蹒跚。身后跟着个左腿微瘸的矮胖男人,小心地扶着她。
女人是申小玲,男的是餐厅老板。
杨涛知道他离过一次婚,以前就挺惯着小玲,经常预支工资给她。她为了晚上赶他的场,不想上夜班,老板也依了她。
小张说:“小玲住院那阵儿,他每天拎着饭煲往医院跑。早出晚归的,一待就是一整天,店里也不管了。小玲的心就是那会儿软的。”
小张还说,他问过餐厅老板是不是一早就喜欢小玲。老板说:“不喜欢还能那么惯着?我这老板当得也忒憋屈了。”
只是那会儿她心里有人,性子又野,他一条腿不利索,离过婚,年纪大,不帅,兜里有俩小钱,可也不多,表白的话都不敢讲。
眼看两人要看过来,杨涛迅速背过身去。待那两人齐齐向前走,才用目光追过去。眼前一片水雾,他急急抹了把泪才将她看清。
她穿一件淡蓝底子碎花孕妇裙,脚上板鞋还是三年前那双。头发烫了,随意地散在肩上。她丈夫一手环住她的腰,一手替她撑伞。伞棚全偏向她那边,太阳光全照在自己背上。
她走得缓而沉,完全不像当初那般蹦蹦跳跳,好像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没有了流光溢彩,却沉淀了岁月静好。
他眼看那两人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入了奔涌的人流中。
申小玲没察觉身后有目光追了她一路,正如三年前,她的目光也无时无刻不在追随着某人,那样深情,那样专注。
可最终那目光落了空。
人心若是空空,怎么样都行。不再执着于曾经,不再飞蛾扑火,不惜一切。当全部的热情消耗殆尽,便只剩下最平和实际的索求。
他终究是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