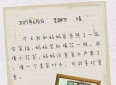小时候,特别盼着能跟父母去割草。那时候家家种地都需要农家肥,而制造农家肥的方法就是往猪圈里放草,然后让草和猪粪一起发酵,草放得越多,肥就越多。
于是,闲暇时去山里割草,成了每家的必修课,许多小孩子都跟大人们一起去,看着他们从山里带回来的藤条、绿松塔、苔藓、各种花,甚至还有野鸡蛋,我真是羡慕极了。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吵着要去,母亲都是冷冰冰的两个字:不行!她说山里有蛇,还有狼。有蛇我知道,我家菜园里就有,有狼,就纯粹是骗小孩了。
终于有一次,父母又要去割草了,临走前母亲突然被人喊走,说是田婶要生孩子了,请她去帮忙。母亲急急忙忙地走了,我爬到父亲借来的毛驴车上,对父亲说,我跟你去。
父亲看着母亲越走越远的背影,想了一会儿,同意了。他把弟弟妹妹送到邻居周奶奶家,就带着我出发了。
小毛驴欢快地跑在乡村的林荫小道上。父亲哼着二人转小调。我躺在光秃秃的车厢木板上,看天上的云。路旁一片一片的槐树林、杨树林、落叶松林,还有我不认识的很多很多的树,小毛驴每跑过一片树林,就会惊起一群小鸟,呼啦啦从这片林子飞到那片林子里去。
高大浓密的树冠把整条路都遮盖起来,天空成了碎块的蓝。不时有鸟叫声响起,父亲就告诉我这是画眉,这是鸟鹰,这是沙鸡……有一种很难听的鸟叫,像被人使劲掐住了脖子,用尽力气才挤出来的声音,沙哑又短促,父亲说那是鬼鸟子,一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鸟,谁也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
近处的草都被人割完了,父亲赶着毛驴车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在一片方方正正的空地边停下来。我很奇怪,山里怎么会有这么规矩的方形空地。
这里的草又高又密,比我几乎高了一个头,整整齐齐得像种的一样。我不敢往里走,父亲递给我一根棍子,让我不停地打蒿草的根部,他说这样能吓走草丛里的蛇。
我认真地敲打着,嘴里不停地嘟囔:“蛇啊蛇啊,快躲开,我爸爸来割草了……”,突然一只大鸟飞起来,那巨大的“噗啦”声把我和父亲都吓了一跳。
这只大鸟很大,头是红的,脖子一圈蓝色羽毛,身上是和大红公鸡差不多的颜色,长长的大尾巴尤其漂亮,那两根尾羽像唱戏的穆桂英头上戴的翎子。父亲说这是野鸡,附近应该有它的窝。
果然,在大鸟飞起不远的地方,一个圆圆的窝里放着十几枚蛋,跟鸡蛋一样大,比鸡蛋圆。这时,又一只野鸡从草里钻出来,它没有飞,而是歪歪斜斜的向前跑着,好像脚和翅膀都受了伤。
父亲看着它的蠢样子,笑了,说走,咱们去别处割。我问为啥?这草这么多。父亲扒开一堆草让我看,原来又是一个放满蛋的鸟窝,父亲说那面还有,这里是野鸡们的家,咱们不能打扰它们。
父亲把割下来的几捆草装好,带着我悄悄地退出了野鸡的地盘。父亲不许我回村里说这个地方。他怕二栓子他们把这里祸害了。
我说那他们自己找来呢?父亲说不会,他们不敢来。我问为啥,父亲却不回答了。那只受伤的鸟怎么办啊?我问父亲。
父亲又笑起来,说我被那鸟骗了,它根本没有受伤,它那样子是吸引咱们去抓它,把咱们从它的窝边引开。哦,我恍然大悟,想不到这野鸡这么聪明,装的那么像。
夕阳西下,斜斜的的太阳把树林照得一片金黄。我和父亲拉着满满一车的青草,走在到处都弥漫着甜甜的草香的小路上。归巢的鸟叽叽喳喳,好像在互相说着自己一天的见闻。一缕缕炊烟从村子里飘起,那炊烟里裹着的是妈妈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