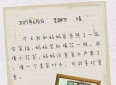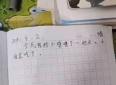冬哥在炕上打腻已经是第四天了,打腻的原因是冬嫂又问那18万元还剩多少钱,其涉嫌查账。冬嫂怀疑冬哥用这钱在外面靠人,其实冬哥还真动用这笔钱在外面靠人,只是很羞迷,冬嫂怀疑,但没抓着把柄。冬哥打腻就是装出一副提起裤子不认帐的铁性。
冬哥平时也是这样左右冬嫂的,只要不高兴就炕上打腻,一腻就是一集,五天;冬嫂为了扳冬哥这个臭脾气 ,曾经跳过坑塘,砸过锅,烧过冬哥捂着的被子,但都无济于事。这样搭伙,你说要是夫妻“天天快乐”,那不是骗鬼吗。

叫冬嫂更绞心的是,今年春上,村上又下来了5亩地30万元的天额补偿款,但这30万元冬嫂还没听到信,就叫儿子子寒给领走了,冬哥也不知道。子寒偷偷领走这30万元的原因,就是他爸爸领走了那18万元钱在先,而且一分也没给儿子和儿媳。要说冬嫂冬哥对此 不生气,那是假话。可恨的是这卖地的收入不消半年就叫儿子子寒给鼓捣没了,其主要用于赌场下注、炒股,小部分和盟兄弟们喝了小酒,洗了“荤”澡,因此,媳妇也因散了,甩下四岁的小孩子,冬嫂还得天天负责送幼儿园。
这样糟糕的日子,这样叫人不省心的儿子,冬嫂和冬哥毫无办法,就这么一个儿,你能把它吃掉吗。但,有了这一劫,冬嫂和冬哥都像霜打的茄子似的,完全没了精气神,冬哥用18万元悄悄在外面靠人,偷着乐。冬嫂就不行了,儿子扔钱丢妻,老爷们不干人事,她的肚子整天鼓鼓的,就像种上一颗炸弹,她感到随时都可以爆炸。
地没了,冬哥也就用不着下地干活了,有18万元消费呢。其实冬哥有瓦工手艺,活还不错呢,经常有人喊,但自从卖地有了钱,他就一下子变懒了。干那受累活干嘛,有钱花就得了。所以,冬哥大部分时间在家窝着、糗磨着,一个人整天炝毛炝刺,看着就憋糗可怜,偶尔精神会,那是“扔钱去了”。
冬哥打腻四天了,按习惯今天第五天该下炕,冬嫂催促说,还嫌害臊吧?该结束了,我可告诉你,你要老这样,我心里这颗炸弹不知哪时就得炸了,到时你可别后悔!冬哥说,我的事你以后少管,别脏心乱肺。冬嫂说,好!好!我是神经病。咱说点过日子的事,行不?你看,院子里的草都过了膝盖,蚊子嗡嗡的,你看不见呀?你不觉得出来进去堵得慌吗?你有空拔拔,地不种了,草也不会拔了!?
冬嫂满以为冬哥会听进去自己的话,用手、镰刀清除草,依此也活动一下筋骨,谁知,冬哥到集上买来一瓶除草剂“百草枯”。这不是懒汉的作法吗?又花钱,又在家里放毒。冬嫂当然要抱怨几句,免不了说些不好听的话,更免不了把话又扯到儿子子寒无端挥霍掉那30万元的补偿款上,还有,那18万元的“醋意”也自然泛起。冬嫂的话是这样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有败家的儿,就因为有一个不过日子,不干好事的爹!话说得不算不狠,够解气。
好!一切因此全都打住,听了这话,冬哥背着装满百草枯农药的喷雾器,仅喷到一半,就两把摞下来,叭家伙扔到了门洞子的一侧,正好砸在刚倒出几滴药液的“百草枯”的小瓶子上。其一改上炕打腻的习性,瞬间暴怒,接下来回头走人,出门咣地一声把门带上。冬嫂见此,心里装着的炸弹霎时提到了桑眼,但她把它咽了下去,冬嫂竟鬼使神差,上炕打起炕腻来,其暴躁的性格令人不可思议地滑进冬哥的行为轨道,但冬嫂在炕上全没有冬哥的忍耐和对自虐般折磨的忍受,她就感到肚子里的炸弹已经无声地引爆了,因为她感到一点气力都不存在了,其眼神就像离水很久的鱼迷离而又黯淡无光。
时至下午四点多,冬哥回来,可能他觉得应该吃点东西了,他踏进外屋,其举止没有一点理会冬嫂的意思,其直接奔向锅灶,但等他做上水,再去打开那液化气灶时,他竟发现没气了,他将炒勺端离灶台,啪地摔在地上,转身又走了。这一摔,冬嫂听见了,这哪里是摔在地上,这吭哧一声是砸在冬嫂的心上啊,它真正砸响引爆的是冬嫂心中那颗积温已久的炸弹,炸碎的是冬嫂活下去的那棵早已无水滋润的禾苗。
天黑时,冬哥回家来,炕上已不见了冬嫂,他打开门灯,里外喊找,皆无回声,他奔向大门,试图到外面寻找,但刚要开门时,他猛然发现,冬嫂歪躺在门洞子的一侧的角落里,她手扶着的是那歪斜的喷雾器,其脚底下是冬哥没用完的那瓶除草剂“百草枯”……
到秋后,冬哥用那18万元的剩余部分又说一个老伴,据说就是他搞得“破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