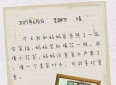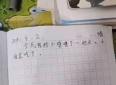昨天收到妹妹一条短信,“家里那只膘肥体壮的老母鸡死了。”
看完这条短信,我喉咙发哽,鼻子发酸,心脏隐隐发痛,仿佛有一根银针搁在里面似的,视线愈来愈模糊不清,那段封藏在心底最深处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瓦解我曾经想方设法堆砌的堡垒,缓缓地、井然有序地漂浮而出,母亲那副悲怆、痛苦、无奈、苍老的面容像特写镜头不断在脑海里重播……
小学五年级那个暑假,夏日炎炎,骄阳似火,屋里俨然是一个大型的蒸笼。院子里的树叶纹丝不动,连一丝风儿也没有,空气好像凝滞了似的。
那天,我穿着短裤短袖,拿着一把芭蕉扇坐在杨桃树下,两手不停地扇风,可是光洁的额头上还是连绵不断地冒出豆大的汗珠。时不时一两句咒骂声从矮矮的围墙外传进来,“什么鬼天气啊?闷得要死,热得要死,简直要人命……”母亲不停地往院子里、屋里洒水,特别是母鸡栖身之处, 不停地洒水、或把母鸡赶在树荫下、或往鸡棚上放几根叶子茂密的树枝,等等。我心里有点嫉妒,觉得母亲爱母鸡甚于爱自己的孩子,真不明白她到底在想什么?或许是为了那几个可怜巴巴的鸡蛋吧!说起鸡蛋我越发来气,顿时气得胸脯微微起伏,不知母亲从哪儿听来一句话,说什么小孩多吃鸡蛋会变聪明。
从我有记忆以来,每天早上餐桌上必定有几个鸡蛋,一开始还是挺喜欢吃的,后来吃多了,看到鸡蛋就宛如看到中药,一年365天天天吃鸡蛋,就算是鲍鱼海参天天吃也会厌倦,何况是鸡蛋。我和妹妹提出无数次抗议,可是,母亲充耳不闻,固执得如一块顽固的石头,每天餐桌上照旧摆上几个鸡蛋,更离谱的是眼睛直勾勾地监视着我和妹妹,每人至少要吃一个鸡蛋。我和妹妹曾经一度怀疑自己会不会变成傻蛋。
一次考试我故意考差了,就是为了向母亲证明,她那句不知从哪儿听来的话是错的,毫无根据,纯属于胡说八道。天天吃鸡蛋未必会变聪明,未必考试就得高分。当我把考试卷交给母亲签名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时,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考试卷,握笔的那支手微微颤动,嗫嚅着嘴唇,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屋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忽然我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了,我低着头咬着嘴唇,不敢再看母亲。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突然开口了,“明天开始,你每天至少吃两个鸡蛋,就这么定。”母亲语气坚决,不容置喙。我目瞪口呆站在哪里,如一块木头,这算自掘坟墓吗?我在心里问自己。
母亲往鸡棚上放树枝时看见了一只鸡蛋,黄蜡的脸上即刻浮现出一抹微笑,笑呵呵地捡起鸡蛋进屋去。我一看见鸡蛋、母鸡眼晴里就不自觉地流露出仇恨的眼神。突然,一个念头从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天气那么闷热,如果把家里几只母鸡闷死就好了,这样有鸡腿吃,又不用吃鸡蛋了,如果这样,那该多好啊,”我心里暗暗想。
不知是不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心愿,还是今天下蛋那只母鸡命该绝。傍晚时分,太阳渐渐落山了,可空气仍然沉闷,土地仍然冒着一股热气,好像刚刚发生了一场火灾似的。那只母鸡果然被闷死了,躺在鸡棚旁边一动不动。我内心激动不已,差点兴奋地一蹦三尺高。而母亲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捧着母鸡,好像捧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那么小心翼翼。后来母亲红着眼睛烧水、杀鸡、拔鸡毛等等,至始至终一声不吭,耷拉着脑袋不停忙这忙那。当一股香喷喷的白切鸡味从厨房里飘出来,我和妹妹不停地吸着鼻子,肚子开始唱空城计,馋涎欲垂。母亲从锅里掏出那只膘肥的母鸡放在砧板上,当那把锋利的菜刀斩断鸡脖子时,两颗晶莹剔透的泪珠从母亲眼里滴落,每斩下一刀,母亲握着刀柄的那只手就轻微抖一抖,好像那把刀是斩在她自己身上。母亲斩完这鸡后,彷佛全身力气都被抽光了,腮帮两边微微下垂,佝偻着脊梁,步履蹒跚地端着那碟白切鸡走向餐桌,然后默默不语地转身进房间。
那晚,当我和妹妹进屋叫母亲吃饭时,看见母亲慌慌张张地拭擦着眼泪,手里握着几张湿漉漉的纸巾,看见我和妹妹时急匆匆转身,声音嘶哑地说“你们快去吃饭吧,我不饿。”我和妹妹站在哪里手足无措,更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悄悄地走出房间,心想先让母亲静一静吧,待会再来叫。可是,我们后脚跟刚迈出门槛,母亲就把门反锁了。我和妹妹面面相觑,然后望着那扇漆黑的门发呆。
第二天,母亲像平常一样干家务,煮饭、洗衣服、喂鸡、扫地等等,动作敏捷、做事干脆,彷佛昨天什么也没发生。可是,那双红肿着跟核桃般的眼睛出卖了她,房间里那满满一篓的纸巾出卖了她,嘶哑的嗓子出卖不了她。
上初中时,学校离家里有点远,母亲叫我在学校里住宿。我有点犹豫不决,如果住宿学费要多交一些,还有每个星期的生活费,家里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太高,但想到以后不用天天吃鸡蛋,我就欣然同意了。
开学前一天,我准备去学校时,母亲为我包了5个盐局鸡蛋,出门时握着我的手背反反复复叮咛我,“每天一定要记得吃一个鸡蛋,这里几个不够一个星期的量,记得早上在学校饭堂里买,我会多给你一些生活费的。”我心想怎么会不够呢?还嫌多呢。但嘴上还是敷衍应答,“好的,知道了。”转身我就把鸡蛋送给新舍友们吃了,他们一边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夸我母亲的厨艺不错,我心里也涌起一丝自豪感和轻松感。心想终于可以摆脱鸡蛋的厄运了,想想心情就舒畅、愉快。不料,母亲隔三岔五到学校找我,每次只是为了送鸡蛋,或者叫与我同校的邻居伙伴帮忙带几个鸡蛋。一次我跟母亲说:“学校什么都有得卖,根本不用你老人家大老远专门跑来送鸡蛋的。”但母亲非常固执,说:“学校里卖的那些鸡蛋没有自家鸡蛋好。”我简直无语,只好闷闷不乐地拎着几个鸡蛋给舍友们吃。但吃多了,人家也很讨厌。最后只能拎回放在宿舍角落里,过两天直接拿出去扔了。
一天傍晚,母亲又来到学校门口最左边一个角落里,站在一颗枝繁叶茂的杨树下,晚风徐徐,吹拂着母亲灰色的上衣簌簌发抖。我有力无气地接过母亲手中的鸡蛋,耷拉着脑袋缓缓地往校门走,她似乎在我耳边唠叨了什么,但我一句都听不到,只觉得耳膜嗡嗡作响,我脑子不停地转动,手中的我鸡蛋怎么办,难道像往常一样拎回宿舍放几天再扔掉,不行,如果刘伟看见了,肯定又要打趣我。母亲简直是吃饱撑着没事干,隔三岔五来送鸡蛋,要不就叫邻居伙伴们带,搞得那几个舍友和伙伴都拿我开玩笑。愈想愈生气,愈看手里的鸡蛋愈不顺眼,好像手里拎着几只死老鼠。刚好看见学校门口那只垃圾桶,我直接把它甩进垃圾桶,听到鸡蛋坠落后发出叮咚声,心里十分痛快,好像一直积压的不快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发泄了。
晚上下自习课后,妹妹发来一个短信,“哥,我太佩服你了,你这次怎么说服妈妈把鸡蛋原封不动地带回的。”看到这条信息我震惊不已,好像被高压电电了一样。陡然一个可怕的想法从我脑里冒出来,我拔腿往学校门口那个垃圾桶奔去,气喘吁吁地站在垃圾桶旁边,借着昏暗的路灯,弯着腰把垃圾桶翻了个低朝天,那些又脏又臭的垃圾被我翻过来覆过去,希望找到那几个盐局鸡蛋。可是!垃圾箱里什么都有,臭鞋子、奶茶杯、烟蒂、塑料袋、纸巾……应有尽有,除了盐局鸡蛋,我失魂落魄地往回走,经过校门门卫室时,听到一位大叔喃喃自语:“真奇怪了,那只垃圾桶香吗?今天一个两个跑去翻,傍晚时分,那个穿灰色衣服的妇女翻,晚间又来个……”当我听到穿灰色衣服的妇女这几个字时,呼吸困难,心脏好像一朵红花瓣,正在被一只恶毒的手撕裂着,很痛,真的很痛,撕心裂肺般的疼痛,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好像决堤的洪水……
嘟嘟——嘟嘟,手机震动,妹妹又发来一条短信,“哥,今天妈妈带给你的那几个鸡蛋是家里最后几个了,因为今天下午突然死了两只老母鸡,今晚妈妈又不吃饭,不过吃了那几个带回来的鸡蛋……
“啊——啊——”我万般痛苦地大叫几声,颓然坐在漆黑、冰凉的墙角下,一会儿想象着母亲捡鸡蛋的情景,一会儿想象着母亲杀鸡的情景,一会儿想象着母亲吃鸡蛋的情景,自责、痛苦、后悔、伤心……如波涛汹涌的潮水般冲击着我,一次比一次激烈、凶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