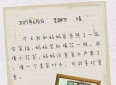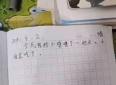那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干涸的大地,楼顶上的地板可以煎熟一个鸡蛋。傍晚时分,虽然太阳落山了,但地上依然有一股热气不断往外冒,像刚刚扑灭了一场大火似的。
暑假期间,苏妮和苏温整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虽是对着风扇坐,但额头的汗水还是源源不断往下淌。有时,为了让屋子降温,苏妮和苏温姐妹俩会一起抬水浇在楼顶上,可夜间依然热得难以入眠,起夜时常常发现衣服是湿漉漉的。
这一天傍晚,苏妮和苏温抬水浇完楼顶后,像往常一样赤着脚丫站在楼顶吹风。
“温温,今晚居然一点风儿都没有,闷得要死,如果住在乡下就好了,可以坐在村子西部的湖边乘凉,那儿常年绿树成荫,有古老参天的老槐树,苍翠欲滴的樟树,笔直挺拔的棕榈,顽强不屈的小草,等等。一阵阵清凉的风儿从湖面吹过来,抚摸着我们的脸颊,再从敞开的衣襟流入体内,那股清凉气息即刻传遍身体每个角落。啊!那一定会非常凉爽、舒适。”
“是啊!还可以光着脚丫在湖边戏水,冰凉清澈的湖水轻轻地亲吻着我们脚趾、脚踝,真是惬意极了。”温温忽然转过头看着妮妮,“你说此时此刻婷婷是不是就在湖边?跟小胖一块坐在我们常坐的那块灰色的岩石上。”
妮妮看了看西边,发现太阳已经落在了地平线之下,晚霞正逐渐褪去绚丽的色彩“太阳下山了,婷婷应该早在家烧饭了,此刻正拿着那把破旧不堪的芭蕉扇对着锅灶扇风呢,否则准少不了被那老巫婆折磨。”
“也是,妮妮,我曾经听小胖说她刚出生时,那个老巫婆就打算把她丢掉,是婷婷的妈妈跪地拽着那个巫婆袖子苦苦哀求才作罢,现在一有不顺心的事儿就拿这事出来发泄,简直就是一个出气筒。有一年,算命先生说婷婷的哥哥今年可能会有点小灾小难,比如磕磕碰碰,出门时一定要小心注意,不要到水边或山上玩耍,没想到那个老巫婆居然说婷婷就是一个扫把星,连累周围人也倒霉,搞得家里上上下下鸡犬不宁,当初刚出生时就该活活掐死,免得祸害他人。”
“我也听说了,婷婷出生那时,她爸爸在外工作,那晚凌晨时分柳若阿姨肚子开始剧烈疼痛起来,是那个巫婆陪***妈到医院生产,孩子出生后一听说是女孩,气得满脸通红,怒发冲冠,当即露出尖利的嘴角在医院里对婷婷妈妈恶语相向,破口大骂,还疑神疑鬼怀疑小孩被掉包了。大家都把她当成一个疯子,怀疑是刚从哪个精神医院里逃出来的。骂累了,骂完了。三更半夜,她居然狠心撇下柳若阿姨一人留在医院。当时情景的可想而知,一名产后虚弱、肌饿、疲劳的产妇孤零零地躺在冰凉的病榻上,望着哭天喊地的婴儿却无能为力,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凄凉、无助的眼神,脸色苍白得如一张白纸,单薄的身躯拼命挣扎着起来,一次,又一次倒回病榻上,滚烫的泪水在眼眶慢慢地、慢慢地酝酿,终于夺眶而出,顺着眼角的沟壑缓缓地滑过太阳穴,轻轻地、无声地滴落在枕头上……更过分的是那个巫婆第二天在村里说三道四,跟所有人说……”
“妮妮、温温下来吃饭了。”于淑秋的声音在楼下响起,打断了她们的谈话。
“来了,妈妈。”温温弯着小腰对着楼下喊。
这晚饭桌上似乎笼罩着一层无形的压抑的气氛,隐隐约约让人透不气,好像一块小石头堵塞在胸口。苏妮和苏温也不像平时一样嘻嘻哈哈,整顿饭下来大家都缄默不言,只有筷子和饭碗、盘子碰撞时发出的声音。
吃完饭时,于秋突然开口了,“妮妮,温温,今晚各自收拾自己的行李,明天全家人一起回乡下住段时间。”
“真的吗?太好了。”妮妮和温温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屋里转圈圈。
“妈妈,我们这个暑假在乡下过吗”?妮妮眨着亮晶晶的眼睛,笑容可掬地问。
“是的,也……”
“太好了!太好了……”妮妮和温温异口同声地呼喊,高兴地鼓起掌来。
于淑秋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她俩硬生生地打断了,她站在那儿沉思该不该把后面的话说完呢。当眼睛触到孩子们天真烂漫、单纯可爱、无忧无虑的样子时,她终究开不了这个口,只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句:孩子们!也许以后我们都要在乡下过了。于淑秋一想到以后孩子们可能会过上朝不保夕的日子就痛苦不已,自责不已,她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有文化、有理想、有气质的城市人,希望孩子能在城市里长大,在最好的环境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可天有不测风云,计划赶不上变化。
天真的妮妮和温温依然在客厅里开怀大笑,她们并不知道,她家已经破产了,并背负着沉沉的债务。一场噩梦已经降临到这个家,她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天夜里妮妮和温温激动得睡不着,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不知疲倦,直到凌晨过后才迷迷糊糊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客厅就响起咣咣当当的声音,还有忽高忽低的讲话声,那声音十分陌生从来没听见过。妮妮和温温好奇不已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急忙忙的起床穿衣、穿鞋、洗漱出门看看,原来是爸妈和几位身强力壮的叔叔在搬家具,为什么要搬这么多家具呢?以前回乡下只需带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就可以了,何况这些家具乡下一应俱全,何必多此一举呢,对此妮妮和温温感到疑惑不解,难道是搬家?可是昨晚妈妈并没有说。
“妈妈,我们搬家吗?”妮妮歪着脑袋问于淑秋。
“是的,奶奶想你们了,所以我们搬回乡下长住一段时间。”
“好呀,好呀。”妮妮和温温再次鼓掌叫好,开心地活蹦乱跳。
大概十一点钟左右才装好车,一辆大货车装着满满的,几乎不留一丝空隙。这期间,妮妮和温温心急不可待,不停地追问爸妈还要多久,感觉比等待下课的铃声还要煎熬无数倍。装好车后,妮妮和温温背上书包,戴着宽大的草帽各自坐在爸妈的摩托车后面。于淑秋和老公苏晨各自开着一辆摩托车对大货车穷追不舍。
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路边的花草耷拉着脑袋,一副精神萎靡的样子。而坐在后座的妮妮和温温却扬着灿烂的笑容,嘴角的弧度像一轮弯弯的月儿。她们感觉自己像一只即将飞出笼子的小鸟,期待着与伙伴团聚和亲吻着自然。脑海里控住不住浮现出小伙伴们在老槐树下玩耍的情景,小胖是不是又在湖边跟瘦猴红耳赤地争吵?华军是不是又在那颗老槐树下制作一些稀奇古怪的木玩具?应林是不是又跟他爷爷在肥沃的土壤草丛边挖蚯蚓……啊!想到这些妮妮和温温就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内心不停地呼喊:快点,快点到家,再快点吧。
一路风尘仆仆,身后的尘土漫天飞扬、空中旋转。
下午3点钟终于到家了,于淑秋和苏晨忙于卸货而无暇顾及妮妮和温温,叫她们自个儿玩去,这正好符合她们心意。此刻她们内心非常渴望见到婷婷、建潘和其他伙伴们,急于分享自己的玩具和听他们讲讲平时发生的小趣事。妮妮和温温急匆匆地背着书包往老槐树那边狂奔,背后的书包跟随着脚步的节奏忽高忽低,叮咚叮咚作响,声音悦耳动听,仿佛一股清凉的泉水涌动。
“瘦猴,快,快点把沙包丢过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建潘的声音从湖对面的老槐树那边传过来。建潘长得胖乎乎的,人们习惯称呼他眫子抑或建眫,几乎不叫他名字,除非在***妈面前。有时稍不留意在***妈面前常常会叫漏嘴,***妈立即横眉竖眼,这时大家赶紧改口。***妈最忌讳别人叫建潘作小胖,她说这样会把他叫瘦的。小胖的眼睛非常小,眉毛却又浓又黑,每次笑起来只见眉毛不见眼睛,脖子有点短,每次说话时总喜欢梗着脖子。大家一起玩耍时他特别喜欢大声说话,希望别人多注意他或服从他,把自己当作一位领导者,恰恰瘦猴最无法容忍这点,经常跟他发生争执。
妮妮和温温一口气跑至湖边,站在岸上扶着一颗柳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远远望见湖对面老槐树下建潘和几个小伙伴在丢沙包,嘻嘻哈哈的笑,玩的不亦乐乎。
“小眫,小眫,小胖,小胖……”妮妮和温温异口同声地对着小溪对面呼喊。
建潘恍惚中听到似乎有人在呼喊他,于是举目四望,当看见是妮妮和温温时高兴地跳起来,连忙挥手回应,并向她们疾奔而去。
“妮妮、温温,你们可回来了,昨日聊天时我还和婷婷提起过你们,还以为你们今年不回乡下过暑假了呢。”
“我妈妈说这次全家人会在乡下长住一段时间。”温温应答。
“那太好了,以前你们都是回乡下住几天就要回城里了,许多话还没来得及说玩,许许多多有趣的事还没来得及去做就要匆匆忙忙与你们告别,那滋味真不好受。”
“是呀,是呀,一点都不好受。城里一点都不自由,小区里玩耍的小朋友也很拘束,好像拴着缰绳的小马。
“哦!对了,前几天我发现了一只马蜂窝,里面蕴含了相当多蜂蛹、蜂蜡、蜂胶,等等。要不明天我们去捅了它”
“呵呵!小胖,你果然好了伤疤忘了疼,上次我和妮妮回来听婷婷说,有一次,你捅马蜂窝被黄蜂蛰着惨不忍赌,鼻子、腮帮、眼睛都中招了,比打肿脸充胖子的胖子还要臃肿。第二天上学时,班里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更在学校里传的沸沸扬扬,其他班同学纷纷前来围观,被笑话了整整一个星期。哈哈……哈哈……特别是那双眼睛,肿得可以跟家里的灯泡一决雌雄了,哈哈……真好笑,那时我问婷婷,你怎么不戴一副眼镜和一副口罩上课呢?婷婷说你脸太臃肿了,实在戴不下,哈哈……”
“意外,意外,不准笑,不准笑,也不准提了,不然我跟你们翻脸,再说了人生那么漫长,日常生活中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是在所难免的。”建胖气急败坏说。
“好,好,好,我不提了,唔,婷婷呢?今天怎么不见她?”温温和妮妮拉长脖子向湖对面张望。
“别看了,婷婷不在那儿,今天早上我经过她家院子时听见激烈的争吵声,好像是她和她哥哥在吵架,所以没敢叫她。”
“婷婷怎么那么傻,至今仍不懂得吃一堑长一智呢,怎么还不明白在家里不管她有没有理,错的永远是她,要不我们去看看婷婷吧,好久不见了,有点想念她。”妮妮对着小胖、温温提议。
“没有问题,刚好我们有礼物要送给婷婷,随便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小胖,你猜猜看,我和妮妮会送什么礼物给她?如果猜对了,有奖励哦!嘻嘻。”温温兴奋地看着小胖。
“嗯。”小胖黑白的眼珠在小眼眶里转来转去,一只手摩挲下巴,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嗯,大大的惊喜,不会是唐老鸭娃娃吧?”说到后半句话时,小胖忽然提高了声音。
“宾果,答对了,想不到平时呆头呆脑的你,突然间变机智了。”
小胖听到温温夸奖自己,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右手摸了摸后脑勺,腼腆地嘿嘿笑了几下。
“还不是因为有奖励,有动力就是不一样!哈哈……”妮妮笑着揶揄小胖。
“当当当,看看这是什么?奖励你的,小胖。”温温从书包里掏出礼品。
“Oh my gad,居然是水枪,水枪啊,太好了!太棒了!温温、妮妮你们最好了。哇塞!还比瘦猴他爸买的那把好看多了、先进多了。你不知道,上次他拿着一把水枪到处炫耀,逢人就说他有一把水枪,那嘚瑟样子别提多欠揍。对了,上个星期,华军用树枝制作了一把很精致的“Y”字形弹弓,配上他高超的技术在树林里打了一只小鸟,所有伙伴都羡慕嫉妒恨,许多人想拜他为师。他还擅长制作陀螺,玩具枪, 线轴车,等等。你知道的他父亲就是一名出色的木匠工。应林昨天……”
妮妮、温温、建潘三人一路有说有笑地往婷婷家走去,几乎都是建潘在说,每次他见了妮妮和温温就口若悬和,一时半会停不下来,妮妮和温温也津津有味地听着,她们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很感兴趣。不知不觉已到婷婷家后院。
“打死这个贱婢,真是胆大包天了,既然同哥哥打架,谁给她胆子的,吃里扒外、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停停,小胖你先不要说话,你们快听听,又是那个可恶的巫婆的声音,婷婷可能又挨骂了,唉……”妮妮秀气的眉毛不由地拧成一块,樱唇小嘴叹出一声气。
“怎么办呢?”温温也焦急地问。
“要不我们爬到树上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
于是,三人身手敏捷地爬到树上,动如脱兔,建潘虽然有点胖,但天天爬树,身手一样敏捷。三人在树桠上站稳后,各各把脖子拉着长长,如一只只长颈鹿。婷婷家的围墙不高,里面的情景尽收眼底,一副悲惨的画面扎着他们心脏隐隐刺痛,如一根鱼刺在那儿。婷婷赤脚站在长满青苔的墙角边,两手向下垂着,耷拉着脑袋,披散着头发,眼泪源源不断地往下流,脚趾头那块土地早已被眼泪浇灌着湿漉漉,没有哭声只是流不完的眼泪。她爸爸拿着棍子拼命往她身上抽,仿佛一只庞大魁梧的凶兽,用它锋利的爪子向婷婷抓去。他面部狰狞,对着婷婷大声地呵斥:“知道错了吗?还敢打哥哥吗?出声啊?出声啊……”柳若阿姨夹在婷婷和她爸爸之间,好像一块夹心饼,左右为难。她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几缕头发散落在额前,看起来狼狈不堪,依稀可见手臂上的几条伤痕,显然易见是替婷婷挨的。她不断地推搡着婷婷,对她嘶喊“赶紧跑啊,跑啊,赶紧跑出去,傻愣着干嘛?快跑啊,婷婷。”看见婷婷依旧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如一蹲雕塑,柳若心急如焚。显然这一列动作刺激到她爸爸了,手中的棍子越发用劲和狠毒,或许是抽打太久了,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重、呼吸急促。她奶奶端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右手拄着拐杖,眼里迸发出恶毒的眼神,铁青着满是沧桑的老脸,如一只千年老妖怪,又如一名拉拉队的队员,她扯着嘶哑的嗓子在一边助威:“对,打死她,打死这个死丫头,打死她,贱婢一枚,当初应该听我的话,把她送人或丢在路边活生生饿死,该死的贱婢……”***妈愈发心急火燎,一边阻拦,一边苦苦哀求:“别打了,别打了,婷婷快跑啊,快跑啊!”由于柳若阿姨的阻拦和对婷婷的掩护,她手臂上的伤痕又增加了几条。
此刻站在树上的三个小朋友同样心急如火,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不停在心里呼喊:快跑啊,婷婷,快跑啊,快跑啊,你怎么那么傻。妮妮和温温用手捂着嘴巴,担心一时控住不住呐喊出来,眼泪如决堤的洪水不断涌出,硕大硕大的泪珠挂满了脸颊。建潘眼眶泛红,双手握拳死死地克制着自己。如果被那个老巫婆发现她们站在这里,准没好果子吃,少不了一顿挨骂或拿水泼她们。
陡然!***妈不知哪里来的大力气,咬唇一把又一把将婷婷往门外推。婷婷踉跄了好几步,身子摇摇晃晃差点跌到,原本散乱的头发愈加凌乱不堪,如一名失魂落魄、了无生气的疯子,站稳脚后慢慢地往门口走去,两眼空洞无神。她爸爸然要穷追不舍,被柳若阿姨死死地抱住了他一条腿,此刻柳若阿姨早已泪流满面,头发也更加凌乱了,不停地苦苦哀求:“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要打就打我吧。”她奶奶仍然不善罢甘休,对着婷婷背影破口大骂:“出去了就不要回来,死丫头,你怎么不***呢……”
树上三人被残酷的、真实的画面深深震惊了,心情久久无法平复,风中凌乱了,直到婷婷的背影消失不见。最先回过神来的是婷婷,她急匆匆拭去泪水,声音有点嘶哑地问:“现在怎么办?”温温和建潘也回过神来了,有些尴尬地抹了抹残留在眼角的眼泪。“要不咱们悄悄追上去看看吧!我担心婷婷会出事。”妮妮又出声提议。
“好的,好的。”温温和建潘不约而同地答。
于是!三人赶紧小跑去追,终于在一个狭窄的胡同里看见了婷婷的背影,三人轻轻地放慢了脚步,鬼鬼祟祟地跟在后头。看见婷婷再次拐进一个胡同,这个胡同比之前那个更加狭窄,而且周围房子破烂简陋,或断壁残垣,脚下的地坑坑洼洼,一不小会崴到脚。这里都是很久以前的老房子,很久很久没人住了。妮妮、温温、建潘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脚下,如同沾上了110胶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前行。终于出了胡同,三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次路有点宽敞,到处是杂草丛生,有些不知名的杂草长地比她们还要高,附件没有一栋房子,这里一片荒无人烟,婷婷为什么会来这里呢?三人百思不解。婷婷仍然继续往前走,如同一具没有思想的僵尸,仿佛前方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召唤她。不久,隐隐约约见到前面有一座大老宅,婷婷轻车熟路地找到门口并走进去。三人见了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目瞪口呆站在哪里。她们怎么也想不到婷婷会来这里,是啊!怎么也想不到,这里可是村里的禁地——鬼宅子,村里传得家喻户晓。
“嘎嘎——嘎嘎”一只乌鸦的叫声从老宅处传出,三人被吓得尖叫起来。
“怎么办?我有点害怕。”温温的声音颤抖地说。
“要不咱们回去吧。”建潘的声音同样在颤抖,他肥胖的双腿还微微地抖动了几下。
“可是……婷婷还在那里。”妮妮犹豫不决地说。此刻她内心天人交战,她既担心婷婷出事,又不敢往前走。
“那你敢进去吗?妮妮。”建潘问。妮妮摇了摇头。建潘趁机进言:“那不就得了,既然你不敢进去,站在这儿也不济其事,还不如回去吧,再说这事如果被你爸妈知道你了,八成还要挨棍子。”
妮妮沉思了片刻,还是被内心那个胆小的小人打败了,“那好吧。”
于是!三人默默地往回走,一路沉默寡言,大家情绪都有点低落,特别是妮妮。她内心中的天人交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反而更加激烈,如火如荼。从小听到大的鬼宅故事像特写镜头在她脑海里一次、一次重播,挥之不去。
大概70年前,这座大宅人家还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过着有上一顿没下一顿的生活,家境十分穷困。一天,这户人家的家祖急匆匆地回来,安排全家上下老小迁徙,他们搬去哪里?去做什么工作?村里无人知晓,逢年过节也不回家。从此这里一片荒废破败的景象,杂草丛生,成了飞禽走兽栖息之地,人们一度以为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猜测她们在外头发财买大房子了。谁知,10年后,竟然举家搬回来,人人十分好奇,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这户家人不论老老小小个个都容光焕发,春风得意,西装革履,衣着华丽。村里人人羡慕不已,常常以他家为教材教训家里一些庸碌者。那年他家搬回来,马上买地扩大旧房面积,重新规划建造一座大豪宅,工人日夜兼程,快马加鞭。那段时间村里人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都听到施工嘈杂声,扰得无法安稳入睡,特别是一些睡眠比较浅者,对此大家纷纷感到愤怒不已,但也只能忍气吐声,不敢明目张胆说过一字半句。大家都知道他有强硬的后台,人际关系特别广泛,与村里或镇上当官者情同手足,关系密切。
2个月后,一座富丽堂皇的大豪宅拔地而起,建筑雕梁画栋,家具高端,做工精致,架子上摆满琳琅满目的花瓶,门庭百花争艳、繁花似锦,台阶光滑如玉。村里人从没见过如此金碧辉煌的大豪宅,纷纷对他赞不绝口,他也笑得合不拢嘴。
从此大豪宅门庭若市,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访。白天笑声此起彼落,晚上歌声绕梁,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10年后某一天,夜里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大雨整整下了三天三夜。村里的庄稼被淹没了,破旧的房子挡不住气势磅礴的大雨、狂风,屋里上湿下漏,上雨旁风,大家叫苦连天,怨声载道。村里人一致以为只有那户大豪宅人家幸免此次遭遇。
谁知,7天后,不知从哪里滋生出来一段传言,说这座宅子一家老小得了一种怪病,头昏眼花,吐口白沫,浑身出现痉挛和抽搐,嘴里呜呜个不停,但就是说不出一个字,好像无形中有一把钳子掐住了他们的喉咙。每天形形色色的大夫进进出出,都诊断不出病症,只说是得了不治之症。村里人都说得了瘟疫症,大家纷纷退避三舍,绕道而行。平时那些来访的达官贵人,也消失的无影无踪,门可罗雀。
一个星期之后,病入膏肓、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宅子里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死亡,大家对此惊慌不已。那段时间宅子里每天每夜都传出凄惨、痛楚、悲哀的哭声,那声音惊天地泣鬼神,人人感到惶恐不安,担心病魔会找上他们。
天空总是阴沉沉、黑压压一片,蒙蒙细雨没间断过,到处灰蒙蒙一片。一个月后天空渐渐地转晴了,久违的太阳公公终于露出了笑脸,村里人为此欢呼不已。不料,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那座宅子里的人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名一岁多的孤儿和一名寡妇。那个寡妇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精神出了问题,神情恍惚,有时抱着那个孤儿在自言自语,有时拼命抽打那个孤儿,有时如一只疯狗在乱喊乱叫,人们经常听到几个字眼不断重复,“报应啊,报应啊……”
一位好心邻居打算把那个小孩抱过来帮她照顾一段时间,不料,那个疯子以为人家要抢走她孩子,拿着菜刀追着那位好心人满村里跑,吓得尿水直流,上汽不接下气。此后村里人对那个疯女更是望而生畏、远远避之。
三更半夜经常传出那个孤儿的嚎啕大哭声和疯子的尖叫声。一些胆小的小孩吓得胆颤心惊、噩梦连连。宅子附近人家陆陆续续搬离,谁不知她什么时候正常什么发疯。人人自危,每天提心吊胆,害怕小命随时不保,身首异处。
她正常时候见人就打招呼甚至喊你名字,不正常时候拿着菜刀、斧头在花园砍这砍那,嘴里咒骂:“砍死你这个阴魂不散的,砍死你,砍死你,阴魂不散,***吧,***吧,***吧……”某天村里妇女们在庄稼里干活闲聊时,一名妇女突然说了句:“真担心,哪天她连那个可怜的孤儿也砍了。”另一名妇女说:“有可能,那个疯子连侄儿和儿子都分不清,一直把那个孤儿当作自己儿子,都是叫他儿子名字。”不料,一语成谶。
一天夜里,一场大火熊熊地燃烧着这座大宅,把夜空映照一片通红。火焰如一条庞大的、长长的蟒蛇,在大宅里蜿蜒地爬行,肆无忌惮地吞噬一切,所过之地便是一片废墟。消防队员用了半个钟头才把大火扑灭,一名消防员感概:幸好附近无人居住,不然会连累大批无辜村民。警方调查了起火原因,原因是:“那个疯子自己纵火,因为她食指和拇指还残留这一点点石蜡。警方猜测可能是那个孤儿又在哭天喊地,刺激到了她神经大脑,然后发起疯来把那个可怜的小孩砍了,杀死后依然不善罢甘休,把小孩搬到厨房的占板上,拿着大刀把小孩剁成肉碎,鲜血淋漓,手段残忍至极,令人发指。最后自己在一颗杨桃树下上吊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和刺鼻的烧焦味交集一起,在空气中弥漫、飘扬,一点一点向四面八方扩散和蔓延。
过了些时候,一段流言不知从那个犄角旮旯里繁衍出,如一道闪电迅速从村头传到了村尾。说这是报应啊,是老天爷对这户人家的惩罚,一场残酷、残忍的惩罚。说他家是爆发户,靠买毒品,走私烟酒发横财的,赚了一大笔钱违背良心的钱,然后就金盘洗手,回老家颐养天年。不料,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爷偏不如他所愿,并狠狠惩罚了他们一家上下。
这些是不是真的无从认证,只是不断在村头村尾流传,甚至传到隔壁村庄。到了后来,添油加醋,版本越来越多,情节愈加生动和精彩,一个胜过一个,仿佛从头到尾目睹了整件事。从此这里成了村里的禁地,大家都绕道而走,如同躲避瘟疫一样,害怕沾上邪气。几年后,一名乞丐死在宅子里,15天后才被村里人发现的,当时臭气熏天,半条村的人都能闻得到,那臭气让人几天的隔夜饭都吐得出来,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纷争,你说是我家猪屎味臭,我说是你牛屎味臭……众说纷纭,七嘴八舌。最后,还是村长出面,派几个年轻气壮的人彻底调查此事,才知道是那座老宅死人了。有人说是那个疯子灵魂回来索命了,有段时间有村民看见那名乞丐总是从宅子里进进出出,行为鬼鬼祟祟,还捡了破铜烂铁出去卖,有村民说肯定是一天夜里那个疯子回来看见了就杀了他,又有一些村民说一天夜里模模糊糊听见那个疯子的声音。这件事又加深了大家内心对这座宅子的恐惧感,这里彻底成了村里的禁地,家家户户提醒小孩千万不要靠近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