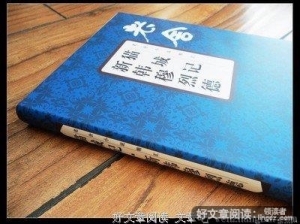母亲与2015年7月7日与世长辞了,她的突然离去让我一时无法接受。
母亲生于1932年,同许多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她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的种种运动。出生于江苏扬州小康之家的母亲集美丽、聪慧、善良与一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她写得一手令人羡慕的好字,可能正因为如此母亲特别喜欢写字,日记本、杂记本连绵不断,收纳盒、包装盒到处都留有母亲的笔迹,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一手好字是出自于她幼小的家庭严律。
和母亲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题、聊不完的事,每每回忆起她的小时候,她总是向我们描述着扬州老家那古老的胡同和美丽的天井,她在那里经历了日本人的侵略,母亲总是有声有色的描述着当时的情景:在日本人还没进来时,大家就传说日本人喜欢欺负花姑娘,于是当日本人进来时,家家都把大姑娘和少妇藏了起来,剩下老人和小孩,就让老人给小孩洗脚,这样日本人就不能欺负了。当时母亲和大她两岁的姐姐(我的大姨)就是被老祖母(我的曾祖母)压在洗脚盆中洗脚的,据母亲说日本人进到他们的房子,将长刀往桌上一扔,桌上的一个当时很新潮的收音机立刻跌落在地摔成两半,老祖母一声不吭的给她们洗脚,让她们躲过一劫。母亲说我的外公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八年抗战为保护银行财产,外公随银行在云贵高原和老挝泰国等边界地区流浪八年,当外公回到上海,她们全家到上海团聚时外婆已重病在身。
母亲总是记忆起她的小时候上学的情景,她说为了练字,早晨5点就要起床,写几篇楷书,不写完就不能吃早饭,开始握笔时,笔握好后要在上面放颗鸡蛋而不掉落以保证握笔姿势的正确。上学时每天都要经过一条僻静的巷子,曾有一天母亲手上戴着戒指走在这条巷子里而被人抢劫,虽然没有得逞,但母亲却被吓得不敢再带首饰。母亲学习甚好,上中学时进了著名的扬州中学,她常说她福气好,在扬中碰到几个好老师,让她的国文和数学都学的特别好。
据母亲说她参加大学考试曾考取了两所学校,本来想从事医学,但外公考虑母亲胆小还是让她选学了财经方面的学科,母亲在上海考学期间外婆病重了,母亲记忆说外婆是得的直肠癌,在当时的医疗水平外婆最后很痛,为了减轻外婆的痛苦,医生隔断了外婆的痛神经,外婆后来不能说话,她示意母亲到她身边为母亲梳了最后一次头。
上海解放前夕,外公让母亲回扬州老家拿东西,而那时基本没有客车能通行,于是母亲随一个父亲是国民党军官的女同学随军用火车回扬州,在上车的一刹那,一排子弹飞来,一个军人立刻扑向她俩,将她俩压倒才幸免于难。到扬州后,母亲与女同学道别,女同学就随家人去了台湾。五十二年后这位女同学找到了母亲,激动不已地告诉母亲,她一直在寻找母亲,那个离别的晚上她一直不放心母亲的安危,母亲很是激动,她说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她看淡了许多事,但还不知道会有一个人一直在找她。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勇敢而坚强的人,记得文革中在太钢工作的父亲被抓的那个夜晚,母亲披了一件外衣吩咐姐姐照顾好我和妹妹就随父亲而去,那个不眠之夜我们在清晨等到了母亲的归来,她进门就说你们的爸爸没有被打,我一直给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他们不敢动他。这天我去学校上学,在学校门口看到了父亲厂里的厂长(同父亲一起被抓去的)被活活打死的照片,这时我才感到母亲的伟大,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母亲是怎样以她那多病的身躯监护着我们一家的安危。在父亲被批的日子里,经常有孩子来欺负我们,我是家里最调皮的孩子,那个时候经常因被别人欺负而惹是生非。记得一次我因为有一家的孩子欺负我们姐妹而用煤块将他家的门窗玻璃打碎,母亲下班回来我害怕的躲到一边等待着那家家长的告状和母亲的数落,等那家长告完状后,母亲立刻把玻璃钱陪给他并向他陪了不是,打发他离去后,母亲对我说:我们现在是受制的时候,要学会低头做人。在父亲被关押的日子里,母亲基本每周都带我们去探视父亲,记得我第一次去看父亲时,见父亲睡觉的地方是在粗糙的地面上铺的麦秆做的草垫,我不止眼含热泪,看守人员见状便告诉母亲:你二女儿好像在哭,母亲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要坚强,不要让人看见你哭,我便打着哈欠说我没哭,是困了。 (励志文章 www.lingdz.com)
母亲是一个非常聪慧的人,她在工作岗位上永远显现出她的果断和精干,以至被单位的同事尊称为阿庆嫂,她反应敏锐,能说会道,连当时被派往地方的军代表都折服于她。母亲并不在行家务事,在我的记忆中,生活在北方的我们,她不会和面,不大会做棉衣,所以当文革开始,家里保姆被赶走后,母亲是用怎样的坚毅把我们拉扯大就可想而知了。文革后,当母亲知道她们的老同事有多少家破人亡时常说:我们一家人能平安渡过那艰难的岁月实属不易。
母亲性格开朗喜欢热闹,家里亲朋好友总是不断,及时在她晚年也每逢节假日总要求全家亲人团聚吃饭,直到她身体不能承受才不甘罢休。记得小时候,经常有母亲单位的同事来家里做客,那时的母亲总是热情的请客人留下吃顿便饭,往往客人也在母亲的热情邀请下随意的和我们一起聚餐,随着母亲的热情我们总是非常希望能有客人来家里。
母亲非常仁慈和大方,每每有讨饭的来敲家门,母亲不但给零钱,还经常乘上一碗热饭加上菜给人家,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要饭的不绝,后来我们对母亲说要饭的不一定全是穷人,母亲却说来要饭总是有困难的。家里的亲戚无论谁家有难,只要一提,母亲马上慷慨解囊,不论家里多困难也寄钱去。
母亲总是为别人付出而不愿别人为她付出,她辛苦照顾了我们一辈子,当父亲生重病时,她依然担负起照顾父亲的责任而不愿多拖累我们,我常常对她说年纪大了要听儿女的,不要太累自己,她总是说妈妈可以的,这点事没问题。而当她身体虚弱到极限时仍然向正常人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她从不愿麻烦我们,在她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仍然坚持不让父亲给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她记忆力极强,及时在80多岁,仍然记得我们许多亲人的电话号码,任何时候打电话时号码都随口报来。她思路敏捷,常常关心着每个下代,她甚至关心到曾外甥的上学问题,她为我们操碎了心,而下代们却有时不理解,认为这老太太管的实在是多,她为我们操劳太多而对自己关心太少。母亲喋喋不休的话语常回荡在耳边,每每在睡梦中,总感觉母亲不曾离去。
我记忆中的母亲总是美丽的,她着装讲究,及时是在那动乱的年代,她也总是把我们打扮的清爽整洁,买来的现成服装总是能被她修改的特别贴身,以至我们姐妹的衣服着装总是很出众,而母亲自己更是美丽漂亮到最后,即使是80多岁的她仍然穿着考究而精神,所以当母亲逝去时,许多认识她的街坊邻居都不能相信,那样一位精干的老太太怎么会走了呢。
母亲美丽的离去了,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思念,母亲啊母亲,我仅以此文寄托我永远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