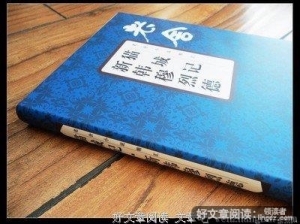阳光暖暖地射进窗棂,暖暖地撒在印花的床单上。斜斜地靠在椅子上,手上拿着本散文细细地读着,忽地听到外门“砰砰”地响起。起身,打开门,外公(丈夫的外公)正拄着拐杖,一手拎着一瓦罐,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我急忙接过瓦罐,搀扶着老态龙钟的外公进屋,却听见外公急急地说:“还热的,快趁热吃吧。”我懵了,疑惑地看着老太爷:难道瓦罐里是送给我吃的东西?外公见我满脸疑惑,又开口了:“早上去菜市买了只鸡,熬了罐鸡汤给你吃。你家不在此地,送罐鸡汤给你补补吧。”望着眼前须发全白的八十开外的老外公,我不禁眼眶湿润了。是的,怀孕已六个多月了,还没舍得买鸡熬汤喝呢,可这个我没喊过几次外公的老人,居然会拄着拐杖,拎着不轻的瓦罐,穿过几条街,把心灵鸡汤送给他的孙媳妇。这仅仅是长辈的鸡汤吗?恐怕不是这么简单的理解吧,送的应该是温暖,送的是亲情啊。
想象着老外公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向菜市,挑鸡、买鸡、杀鸡、熬鸡汤。我的天哪,他可是八十二岁的老翁啊。这每一口汤里应该是老人那至诚至暖的心吧,是血缘亲情吧。
外公可算得上知识分子了。据说年轻时是小学校长呢。在校长位置上一干就是几十年。解放了,一个小学校长一下子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回家吃老米干饭了。
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变成了寄人篱下乞讨翁了,那时怎样的一种无奈啊。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有七十多岁了。每次见到他,总见他坐在小小的木头椅子上,手拿张报纸,鼻子上架着老花镜,在暖暖的、充满甜味的阳光里,细细地看着报上的每篇文章。老人清癯的脸上充满着平淡、随和,早已没了昔日校长的威严。
我们要结婚了,外公听了很兴奋,那可是老人唯一的第三代大学生的外孙结婚啊。他急忙拉起外孙直奔新华书店,花了七元钱,挑了本《康熙字典》,双手递给外孙,说是送给外孙的结婚礼物。外孙被老人的神圣深深感动了。要知道,这是老人对外孙的厚望哪。对于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来说,七元钱可是一笔巨款哪。(关于励志的文章阅读 www.lingdz.com)
此后,每次备课,我们都要用到这本散发着亲情馨香的《康熙词典》,外公那充满期望之情的眼神总会浮现在我眼前。一个人老心不老的长辈啊。
上个世纪,七九年,外公接到单位通知,平反了,那顶戴了多年的历史反革命的铁盔终于被卸下了。接着,恢复公职,恢复工资。老人的脸一下子仿佛展开了,皱褶也好像被熨平了似的。老人从心里年轻了:腰挺直了;老花眼居然闪动着亮闪闪的光,转老返童了。
再次见到外公时,已不再是那个满脸无奈的老人了。近八十岁的年纪,还拿起了多年未摸的毛笔,有滋有味地练起了毛笔字呢。
外婆去世后,外公自个单起炉灶,买菜、烧饭。说要体会生活的乐趣。真是一个懂得品味生活的老人啊。
尔后,每次看到他吃饭,观察他的食物,还真令我辈感叹不已:一张小小的方方的矮矮的几案上,放着四个精致的、透明的小蓝花碗(可能是景德镇细瓷的),每个小碗里盛着色泽不同的素菜,分量不多,大概都是小半碗吧。偶尔,也能看到一点荤菜(一个懂得养生之道的老人哪)。看着老人吃饭,简直是在欣赏一幅情趣盎然水墨画。只见老人白白净净手上,随意地端着一个小小的、底部尖尖的、四周呈透明镂空状的薄胎细瓷花碗,盛上小半碗白米饭,干树枝似的手指夹着筷子,缓慢且优雅、用筷子尖夹着菜,送进那已没了几颗牙的瘪嘴里,缓缓地挪动着。老人咀嚼起来没一点声响,更没七、八十岁老人吃饭时的鼻涕、口水糊满嘴角的惨状,永远是清清亮亮、干干净净。一小方桌;四个镂空的薄胎的蓝花碗;色彩明丽小菜(不是色彩艳丽);一老翁;平淡地、随和地咀嚼着生活给予的美味。看得出,外公过得恬淡且满足。
外公的离世也很平淡。前一天晚上还与儿子孙子谈心,第二天早上媳妇却发现老人已平静地、平淡地、无忧无虑、无怨无悔地去了。老人平静的脸上像睡着了一样,可以想象,老人在去那个未知世界的路上,走得很平淡、平和、满足。
阳光又一次缓缓地射进了窗棂,暖暖地撒在床单上。闻着阳光那清新的芬芳,好像又闻到了当年外公的香气四溢的鸡汤。这哪是一般的鸡汤哪,分明是外公的亲情鸡汤哪;是长辈关怀晚辈的至亲至爱的亲情鸡汤;是人间 最美的亲情鸡汤哪;是中华民族最高尚的传统鸡汤哪。愿这种鸡汤代代相传,万古流芳。
亲情永恒。
以此文献给至亲至敬的老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