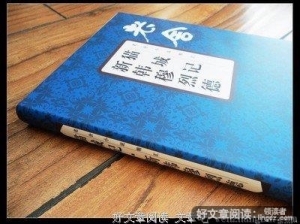好多年了,尽管我已忘掉了太多的过去,但对于我的三叔,特别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其实我与三叔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很多记忆是由一些零零碎碎的影像撮合而成。这些影像模模糊糊,飘飘忽忽,云里雾里,没有一个完整的事件可心证实我对三叔的认识,因此我至今并不知道他爱什么和不爱什么,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像我老爸一样爱喝酒——尽管我感觉他可能也是个好杯之人,因为我从他那张黑红的脸上很容易便联想到五加皮的颜色。听我老爸说,三叔曾经去过香港,那是1949年前的事情。那时候乡下山青水瘦,树多田少,围着几分薄地难有出头之日,因此就有那么一些眼光远大的青年,抱着各种梦想,背井离乡,到外地、到省城、甚至到香港打工谋生。当然,那个年代山是山、水是水,道路不通,水路不畅,出一趟省城,关山难逾,千辛万苦,若到香港打工,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规模涌入城市,留得一村空寂。
老爸比三叔先到香港多年,立稳脚根后,才介绍三叔去香港谋生。那时候的香港不设边界,任人去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港。所以乡下族人中,也有多人在香港安身立命,有的成了那里的永久居民并开枝散叶。但三叔似乎天生是个与泥巴有缘的本分农民,一旦离开生养他的那一片土地和大山,他就会患得患失,茫然不知所措。他在香港混得并不快乐,没有快乐当然也就没有了目标、没有了方向。因此他终于无法适应那里的喧嚣和尘浊,回到了乡下。
我对三叔的印象主要来自于我九岁的那一年。在我很小的时候,或者在我家中,或者在乡下,我是见过三叔的,但那时的我还未懂事,对于身边的事情,大都记住了那些深刻的片段,而对于往来的亲戚乡人,太多了,记不得了。但九岁的记忆至今仍如断断续续的流水,虽不满盈,却很清澈。为了躲避1966年那场血雨腥风,我和弟妹及栋哥、华哥一道,回到乡下。这样,三叔才给我留下了一些不大完整的印象和记忆。
八月的云敏村,绿色的山,绿色的田,给人一派安宁的感觉。三叔红黑的皮肤,敦实的身板,憨厚的笑容,是那样鲜活地印在了那间老屋的阴影里。老屋建在一个鱼塘边的高地上,青砖泥瓦,有点破旧。老爸在三个兄弟当中排行第二,爷爷给三个儿子各分了一所房子,这是属于老爸的一套,厅厨合一,一个房间,一个小阁楼,里面的大床、饭桌、木椅等一应家具,大都是我父母留下的。因为我父母已在广州安家,也因为三叔结婚时穷得叮当作响,所以这房子和这些家具,就给三叔使用了。在这乡下,贫穷是大家共同的拥有,而三叔的贫穷,更加惨不忍睹。按照三叔这身体魄,一家人的吃穿应当不成问题,但不知为什么他家会穷成那个样子。所以,屋里至今没有增添一件像样的家具。
我们在乡下的那段日子十分快活。因此在城里受到的种种郁闷和约束,都在这乡村的山山水水中得有释放。野地、山风和湍流唤起了我们的野性,家乡亲人的热情,更令我们肆无忌惮。山里尽管贫瘠,但我们一日三餐不成问题。白米饭基本得到保障,菜式并不逊于城里。因为城里的好日子已成昨日记忆,买个鱼呀、肉呀都得凭票供应。乡下满地里都是食材:水田里有田鸡、田螺;溪河中有蚬、䂜、泥鳅、塘鲺;水塘里有鱼儿、虾儿、石螺;山中有飞鸟、蟒蛇……只要你想吃,没有吃不到嘴里的。就说那个月明星疏的晚上,我们嘴馋了,就搞了一锅蜂巢山雀粥。那个蜂巢是白天在山上经过细密侦察定位的,因为白天怕被蜂螫不好下手,所以等到晚上才摸黑上山,只有一枝烟功夫,就把它拿下了,人却毫发无损。听说蜂巢可是个好东西,特别是蜂巢里那些蜂虫,一个个挑出来,放到米粥里熬,既营养又美味。这还不算,那天晚上还抓了好些山雀。这些山雀我都说不出名字,有的羽毛好漂亮,有的羽毛灰灰的。只要被电筒光照住,也就基本束手就擒了:有的逮在树梢上,有的逮在屋檐下。山雀和着蜂虫一块下锅,那米粥自然美不可言。
乡下真的什么都不缺,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吃货,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听说老爸每月还寄了些钱回乡下,交由华哥支配,主要是用于支付日常伙食,因此我们真是三餐无忧。乡下的至亲是大伯爷和三叔,一个是我老爸的兄,一个是我老爸的弟;然后是隔代的二伯爷和三伯爷。我们的吃饭问题就在他们之间轮流解决。这样一来,既减轻了亲人接待的压力,也让我们均衡地享受着亲人的关爱。但这种均衡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因为我们似乎都习惯于在大伯爷、二伯爷和三伯爷之间轮流就餐,而对于三叔,我们总是尽量不去给他添麻烦。三叔的穷困在村里尽人皆知,我们怎么可以将一顿饭的花费托付给一个经常透支的家庭。三叔是那样的热情和老实,他绝不会为接待几个侄儿的一顿吃喝而吝啬,他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接待你,甚至可以将心掏出来,让你看看他是多么坦诚。但三叔从来不会用嘴巴表述自己的情感,他老是低着头走路,显得心事重重,好像在思考着许多东西,又似乎总是找不到答案。如果他老早就有自己的远大目标,他大概现在就不应扛着锄头,把皮肤晒得黑红。他与我老爸和大伯爷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一股蛮劲和一大堆肌肉,而且随时可以冲锋陷阵而不需要做预备动作。可惜他这无穷的力量得不到合理释放。三婶跟三叔一样没有文化,而且比三叔更没文化,所以她缺乏那种调配男人能量的气场,更没有能力支撑一个男人奋发向上。她为三叔生了4个孩子,但一个个都被三叔修理得没了个性。但三婶却很有个性,并很能给这个家庭添乱子,她不但看不透三叔的内心世界,而且还不时往三叔流血的伤口上撒盐巴。所以每当三叔遇到天大的难事,总是找不到一个倾吐苦闷的地方,于是只能把郁闷吞进肚里,自己独自咀嚼。三叔一身的牛力就是这样消耗在家庭的重压中,没有目标、没有思想、亦步亦趋、期期艾艾、心惊胆战……直至穷愁潦倒。 (哲理日志 www.lingdz.com)
可是我们当侄儿的都是小小年纪,不懂人情世故,满以为少吃三叔一顿饭,就是对三叔莫大的尊敬。但这对于内向的三叔,可能是一种伤害。那段日子,他总是为了约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一顿饭而努力着,每次见到我,他那张黝黑而满布皱纹的脸上便露出憨厚的笑容,说:“雄仔,今天到我家吃饭吧!”而我总是显得并不在乎,把头一摇:“今天说好了,在二伯爷家里吃。”三叔于是很失落的样子,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哦哦。”步履有点沉重地走了。
其实我们也并非没有到过三叔家里吃饭,只是没有把三叔放在管饭的亲人队列里。在那个队列中,每天到那一家吃饭,都有预先安排。比如今天早上到大伯爷家吃早餐,昨晚上就要提前说好。到了早上,就要说好中午和晚上到哪一家吃饭,这样才不会亏待自己的肚子。否则,大家都以为你要到哪一家吃去了,都没有为你准备,那结果是可想而知。但无论怎么安排,总是没有留给三叔的位置。一个多月的乡下生活,我们在三叔家中吃饭总计不过三次。三叔的家实在是太窄小了,那个厅堂被烟火熏得黑黑的,中间摆一张小饭桌,哪里还有地方立脚,吃饭时候,有的人必须坐到屋门外。而且三叔那四个孩子特别爱闹,大的跟我差不多,小的在吃奶,脏兮兮的,吃饭时很不守规矩。我们这些在城里被宠惯的孩子,如何能够忍受这样的氛围。记不清那一次是三叔家里杀猪还是三叔帮人家杀猪,他特意把我们侄儿仨人叫去他家里吃饭,说是有好肉吃。乡下吃猪肉也是难得,何况是大块的吃,很有吸引力,而且华哥说了跟我们一块去吃,于是就去了。虽然必须挤在一起肩靠肩的吃,屋子还是那样的昏暗、潮湿,我那几个堂姐弟仍是不守规矩胡胡闹闹,但猪肉和猪内脏的熟香使人无法抗拒。三叔看着我们侄儿几个吃得滋味,心里很爽,笑咪咪的,两边的眼角尾纹兴奋地扯动着。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幸福、最快活的三叔。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的有点对不住三叔。
是的,如果我们都无所顾忌,如果我们都多一点亲近三叔,带给他多一点的快乐和笑容,或许他的寂寞会得到多一点消解。他并不需要你给予他什么,你只要给他多一点点的理解,那就足够了。在乡下只呆了一个多月,我们就回城了。再没有机会对三叔说一句抱歉的话。
城里依然是那个形势和那个节奏,并不喧嚣却仍潜伏着许多惊恐。登赢路口的栅栏还没有拆除,到了晚上,栅栏的大门仍然紧锁,各家各户仍需把铜盆和木棍放在得心应手的地方,以备随时敲打,随时追拿那些传说中的逃犯和盗贼。到了第二年,这种令全城人心悸的日子好像有所缓和了。初春的日子,并没有给路口那棵老榕树带来新意。它并未衰老,却撒落了一地叶子。很多落叶是在春天完成的,而嫩芽恰恰在这时取代了落叶的位置。到了5月初夏,树上结满一串串似花非花的小卵果,又像点点滴滴的秋雨一样撒下来。这使我想起了云敏村后山那棵又老又高的荔枝树,在小河边长得蓊蓊郁郁;还有后山的芒草、松果、野花、山埝……
那个夏天的中午,是个很平常的休息日。天空十分光亮,但没有太阳。我们一家子围坐在厅里吃午饭。我们住的屋子是平房,一室一厅,厅门敞开,正对外面的小路。吃着饭,门外陡然出现了一个邮递员,把一封家信递了进来。是老爸接的信。他慢慢把信拆开,慢慢地看下去。然后,我就看到他用手擦着眼睛。他流泪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老爸流泪,也是只此一次。
这封信来自乡下,报告了三叔的死讯。但我始终没有看过这封信,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看到这封信。相信老爸看过这封信后,就把它销毁了,就如同当年必须销毁孔子和莎士比亚一样。
三叔走了,真的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居然也跟那些在财产上、或思想上、或精神上曾经富有过的专政对象一样,匆匆地走了。他走得一点也不壮烈,但却充满了悲情。他在大山里为自己掘了一个竖坑,然后吃了大山里生长的“苦蛮公”(大茶药),便一头栽进竖坑里。没有挣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这样融进了他所厮守了几十年的大山。据说有人揭发三叔私藏了一条枪,说他曾经在山里当过土匪,后来不干了,返回乡下,并把那条枪藏了起来。我相信三叔跟这事儿不拉搭,他老实巴交的像个木桩,也有玩枪的潇洒和藏枪的睿智?所以他被村里那几个风云人物一阵冤棍,自觉无处申冤,只好以身自证清白,可是身后却留下了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子女。
好多年了,我每每想起三叔,想起老爸为三叔的落泪,心情总是难以平伏。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死了,全国上下一片欢呼;而乡下一个憨厚平凡的三叔走了,却在我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乡下那边传来了消息,说是要为三叔平反了。因为三叔当土匪的事儿纯属误传,其实他当年是西江支队的一名战士,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和队伍失去了联系。三叔从此解甲归田。
听到消息的那一天,空中灰蒙蒙的,下起了丝丝小雨。不知为什么,从此以后,我每每经过西江,我都会透过车窗多看她几眼。西江有时裹在夕阳中,有时浸在雨雾里,波澜壮阔,浩浩荡荡。她让我想起了儿时回乡路经这里的情景:一艘渡轮载着我们,在迷茫的江面上缓缓行进,那一声凄怆的长笛,惊破了深空的寂寥。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