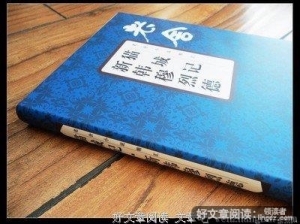家里的磨盘越来越薄了,磨出来的面粉越来越差,粗糙、多糠皮,磨出来的大米里面掺着大半谷粒。母亲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身体双手把握着篾筛边沿,不停地旋转着篾筛,利用密度和重力分选的原理,一遍一遍的将谷粒团聚到米粒上面,然后捧起未研磨好的谷粒,将谷粒和米粒分选开,分选后留下一小部分大米,剩下大部分稻谷粒,再次被送进磨盘进行二次、三次脱皮处理。石磨,这个上一辈分家时留下来的家里最主要的家当,随着岁月的转动逐步衰老、退化,它的躯体已经不能再研磨出精致米面了。变薄的石磨让我们兄弟姐妹很喜欢,轻轻一用力,石磨便呼呼直转,好玩极了。可是,这却害苦了母亲,一日三餐全家人的主副食大多都要从这台石磨里进行粗加工。石磨极低的工作效益,使母亲不得不一遍又一遍的拿起篾筛,一边又一遍的分选,再分选。每一次转动的米筛面筛总是将母亲累得呼呼直喘气,她不得不筛一会儿停下来再继续筛选。
母亲是个身材娇小的农村妇女,她是一个孤儿,我从小没有姥姥,没有舅舅。她个头不到1米六,多子多女使她40多岁就疾病缠身,贫穷的家庭,没法给她提供就医条件。哮喘,咳嗽无穷无尽的折磨着她孱弱的躯体;多子多女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幸福,轻者不听话,不理睬,重者顶嘴顶撞,年纪大了的哥哥姐姐由于变成了家庭主要劳动力常常对母亲大声吼叫,守在灶台前的她泪水常常在眼眶里打转……
与当时其他农村妇女不同的是母亲除了围着灶台转,还伴随着磨盘的转动,一天不停的连轴转动。在那个没有动力机械的年代里,石磨,是家里的唯一“核动力航母”,每个家庭吃的是精米细面还是粗粮糙米,完全取决于是否有一副好磨。石磨,是所有食物一次加工的秘密武器,很多家庭因为有一副大磨盘,一副好磨盘而被村里人羡慕。我们是家是大家人户,全家10口人,都是靠石磨粉碎玉米、水稻和小麦,将他们磨成面粉和米粒,然后做出各种主食。母亲是家里的操持者,所有的吃喝都出自她的双手,在石磨一天天呼呼的转动声中,母亲的青春、容颜也被岁月转走了……
越来越薄的石磨不但耗费母亲大量的体力,而且磨不出细面粉了,主食质量大幅度下降,必须得换新磨盘了。请石匠,找上好的绿豆色的硬石,经过开挖、粗加工,两个磨扇成型了,请人系上红布,抬回家,二尺多的盘面,一尺八的高度,每个人都啧啧称赞“好一副大磨”,全家人站在门口迎接,仿佛在对外宣布“我们家有航空母舰了”。石磨承载着我们的希望,白花花的面粉在飞扬,雪白的米粒儿在招手。
经过5、6天的工作,石磨在石匠师傅叮叮当当的钻斧锤的合奏声中安装完毕。开始试用了,哥哥站立成弓箭步,首先向怀里拉转石磨,再依靠惯性向前推动把手,石磨就在随着哥哥上身躯体的前俯后仰中缓缓转动,麦粒儿从磨盘面经过磨眼,被两扇磨盘咬合碾压,细细的面粉从磨盘周边纷扬落下,散发出阵阵麦香味。看着厚厚的磨盘,全家人都显得很欣慰,在那个粗粮为主的年代里,吃上一顿精米细面那是多么的奢侈的渴望啊!
母亲是家里每天起的最早的。她从屋外抱进柴火,给家人烧温水洗脸、烧开水饮用,打扫卫生,然后开始备菜,做早饭,洗碗,喂猪;再准备午饭、晚饭,一日三餐,全家10口人,每日三餐的计划、调配全部靠着她;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母亲拖着她瘦弱的身躯,克服着无穷无尽病魔的折磨,没有落下一顿饭;夜深了,我们都酣然入睡了,母亲还在张罗着第二天的生计。天空刚刚现出鱼肚白,母亲已经为我们温好了洗脸水,太阳照进了窗户睡眼惺忪中我们才被叫起床,温热的水、温热的毛巾把我们兄弟姐妹从梦乡拉进现实。 (美文摘抄 www.lingdz.com)
“航空母舰”给我们家生活精细化带来了改变,可是这艘巨无霸并没有减轻母亲的负担。原来的石磨虽然效益低,一个人就可以推着呼呼直转,现在新的石磨需要两个人合力才能推动,每次推磨由原来的两人一组增加到了三人一组,家庭户外劳动力自然最是重要,人员不能减,母亲成了“三人小组”的成员,推磨时负责向磨盘里添加谷物,推完磨,她又得开始筛米筛面,劳动时间和任务更重了。我们推磨时总希望母亲每次多向磨眼里多灌些谷物,这样可以很快完成任务去玩,可是母亲总是均匀的不多不少准确的将谷物灌进磨眼,这样磨出来的面更细腻,出面率更高,口感更好。为此我们每每都会表达对母亲的不满,母亲总是默默的忍受着我们的唠叨与不满。那时的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母亲即节俭而又为生计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母亲就是这样永远是家里那个承受着委屈,承受着指责,在儿女的不理解和抱怨中,仍旧孜孜辛勤劳作,不计任何回报,将家庭、子女利益永远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人。
母亲就像石磨上面转动的磨盘,围绕家庭这根轴。默默的消耗着自己,燃烧着自己的青春,消耗着自己的体力,透支着自己的健康。只要她手足还能动,总是不停歇的为家庭付出和奉献,将怨言、委屈深深的隐藏在内心最深处。她每天围着灶台,围着磨盘不停的连轴转,从没有叫过一声苦和累。她没有走出过家门,没有在餐桌上和大家吃过一次完整的饭,即使是最重要的年夜饭;每次我们硬拽着她到餐桌上就餐,她总是以“再炒一个菜”“菜凉了,我去热热”等等各种借口刚到桌子上,又溜进了厨房。为了让我们吃的好一些,她总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吃完后将我们吃过的剩菜、汤水就着在灶台前囫囵吃点又开始料理家务。春节时节是全家休息团聚的日子,可是母亲不管节前节后还是三天年,母亲却是最忙的日子,给每个人做一双新布鞋,准备各种小吃等等。经常熬到深夜,甚至是通宵不睡觉的赶着张罗;初一到初三,母亲总是变着花样把最简单的食材加工成各式各样独具特色的精美小吃。新年的走亲访友,母亲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走过一次亲戚,离开过家门一步;她总是默默的把饭菜做的热气腾腾,让家人吃的开开心心,让来的客人吃的高高兴兴。
母亲很穷,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不光鲜去很干净,留着刘胡兰式的发型,浑身透着一股凛然正气。一次同学看我很穷,将自己哥哥的衣服送了我两套,母亲发现了,一定要我说出是谁给的,并告诉我说要是说不出是谁给的就认定是我偷的。委屈的泪水汹涌而至,母亲进一步教育我说:“人要知道感恩,要懂得感恩。谁帮了你,不光你要知恩图报,我们全家都要感恩戴德!”
长期积劳成疾,母亲不到60岁就离我而去了。离开前她浑身浮肿的像是被水浸泡过似的,看着她苍白的而浮肿的身躯,我的心寒颤着,仿佛有血在一滴一滴地滴下。母亲的一生没有见到宽广的马路,明亮的电灯,喧闹的城市,拥挤的车辆,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母亲离开我们那天天空倾洒着大雨,像是老天也在哭泣、暴涨的河水也呜咽为这位普通的妇女送行。石块、黄土将她和我们分隔成了两个世界……
母亲的一生与锅台相伴,与磨盘同转,没有转出自己的幸福,但转出了全家人的幸福。她没有转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就像石磨一样紧紧围绕家庭这个轴心,以全家的生计为半径,将自己的子女紧紧拥抱在自己怀里关心着、爱护着,又给予适当的碾压、磨砺。母亲就是一副简单而坚韧,厚重而朴实的大石磨,日复一日的画出简单而又坚韧的音符,却是我内心永不消沉的“航空母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