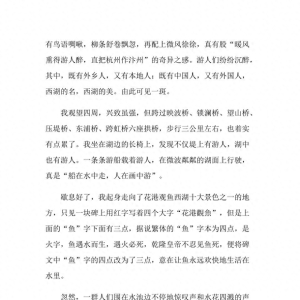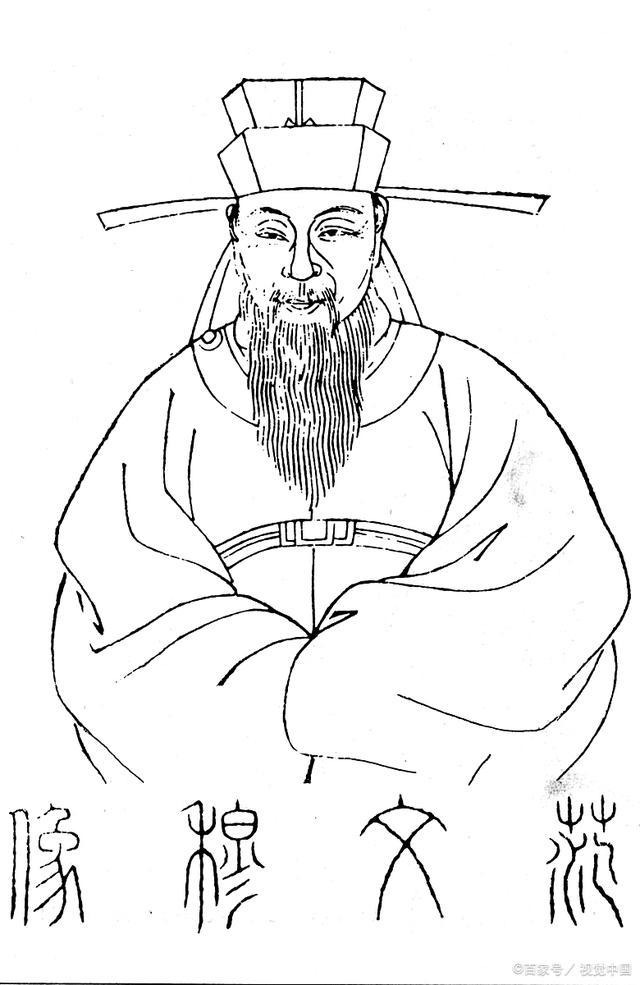
范成大描像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这话是清人张潮说的,很透彻。如斯,山水之于艺术家,犹山水之于诗文,辉焕相华,两相宜也。
南宋诗人范成大(字石湖)《吴船录》是一部山水记游的日记,也是一本读山水的文章。
此录是“石湖于淳熙丁酉由四川制置使召还,自五月戊辰离成都迄十月己已平江止,数千里水程,案日记载,于古迹形胜记之最详。
又载所见古画,多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载,亦可以补阙云。”也就是说,此录是部由成都水路至浙江平江一路山水的考察日志。
故而明人陈几亭士业题词云:“蜀中名胜,不遇石湖,鬼斧神工亦虚施其技巧耳。岂徒石湖之缘,抑亦山水之遭逢焉。”(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范成大船出成都,口吟杜子美诗:“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让我知道诗中“南京”,即是成都。“唐玄宗幸蜀,尝以成都为南京云。”
杜甫驻蜀,多有诗文留蜀,咏蜀中名胜佳迹。有杜甫草堂在成都,这个河南人也几成成都代名。杜甫《戎州》诗有句“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
由此,经由范成大实地实物考察,纠错了《全唐诗》中这一杜诗的舛误。其句中“拈”,实碑本为“粘”字。不过戎州,怎知此舛误。

范成大乘船走走停停,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一路考察,尤对文人印辙旅痕珍重,多“箕踞宴坐,名玩丹石”,一碑一碣,绝不放过。觅得黄庭坚遗踪,“凡山中岩潭亭院之榜,皆山谷书。山谷贬戎州,今叙州也。”有作实地考察,论证:“唐开元中,浮屠海通识凿山为弥勒佛像以镇之,高三百六十尺,顶围十丈,目广二丈,为楼十三层。自头面以及其足,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佛足去江数步,惊涛怒号,汹涌过前,不可安立正视,今谓之佛头滩。佛阁正面三峨,余三面皆佳山。众江错流诸山间,登临之胜,自西州来,始见此耳。
东坡诗:‘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常作凌云游。’”范成大人实诚,在湖北黄州遇苏东坡旧迹,也字字凿实,太过迂腐了。“赤壁,小赤土山也。未见所谓‘乱石穿空’及‘蒙茸’、‘巉岩’之境,东坡词赋微誇也。”访至东坡雪堂,及东坡名之由来之地,也独具只眼:“东坡卜居时,是亦有取于风水之说。前守鸠材欲作设厅,已而辍作雪堂,故稍宏壮。堂东小屋,榜曰东坡,堂前桥亭曰小桥,皆后人旁缘命之。对面高坡上,新作小亭曰‘高寒’姑取《水调》中语,非当时故实。”有遇岩壁刻石“坡、谷皆有之。坡书殊不类,非其亲迹。”
固然,范成大也有谐趣,“至广福院。中有水洞,静听洞中,时有金玉声,琅然清越,不知谁滴何许作此声也。旧名东丁水,寺亦因名东丁院,山谷更名‘仿响洞’,题诗云:‘古人名此东丁水,自古东丁直到今。我为更名方响洞,要知山水有清音。’”在古戎州,也有记“山谷谪居在小寺,号大死庵。后人就作祠堂,并裒墨迹刻其中。方山谷谪居时,屡有《锁江亭》诗,今江上旧基,别作新亭,颇如法《锁江》者。”至于郑文提到“所见古画,多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载,亦可以补阙云。”是指《录》中所记:“观张僧繇画佛像、梁武帝蹙锦绣锦囊,因题欧阳公譔永公碑阴。”并对一不著姓名的书法,作出独到之判断:“笔意清润,微有骨,酷似虞永兴,然结字之体,则全是率更法。疑询在隋时作此体,入唐始加劲瘦刻削也。”

前数年,我读陆放翁《入蜀记》,范成大与陆放翁同为南宋人,一入蜀,一出蜀,一进一出,别有洞天,另饶诗意。不过,范成大《吴船录》绝然日记,陆放翁《入蜀记》貌似日记,却类小品文。那时,范成大为四川制置使,是陆放翁的上峰,陆放翁不过在范成大幕府任参议官。陆放翁在蜀九年,两人虽有文字之交,但往来并不热络。《入蜀记》是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一路“轻舟如叶桨如飞”,赴夔州上任,出任通判,沿途的旅行日记,详记山川风土,一并考订古迹。但两人文风绝然不同,陆放翁所记更像散文,文采斐然,范成大照实所录,行居确凿,俨然一本流水账的日记,目不暇接,随意而匆忙。两人遇同一景物,所记也大相径庭。比如过赤壁,陆放翁显然没有范成大的文字计较:“江平无风,挽船正自赤壁矶下过。多奇石,五色错杂,粲然可爱,东坡先生怪石供是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自己的山水,对于艺术家而言,游历山水文章,显然是滋润自己笔墨另一法门。艺术家应有两副笔墨,一为自然山水的浸润,一为纸上笔墨的浸润。清人张潮无意泄露山水文章之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