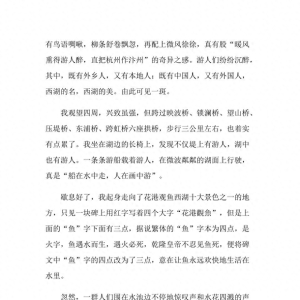《〈读书〉十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分日记四册和友朋书札一册。前四册文史俱佳,是扬之水与古为邻、转益多师、进学悟道的忠实记录。日记中有多处关乎如何写文章的记载。摘引数条,不求甚解,略微引申,作为虎兔交替之际的读书乐趣。

一
1987年1月13日
近由上海译文社出版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是一本在东西方理论界都引起强烈反响的书,其中收录了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加洛蒂关于毕加索、圣琼·佩斯和卡夫卡的三篇评论。作者认为,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
《无边的现实主义》,书名应该是《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出版社是上海文艺出版社。
二
1987年2月2日
在《文艺报》上读到汪曾祺的《林斤澜的矮凳桥》。
汪的小说,我是一向爱读的,未晓他的评论也是写得这般好,并未搬弄名词和概念,亦无不着边际的联想和引申,却将不大能读懂的斤澜小说析得深且透。

1995年秋,林斤澜和汪曾祺在温州
在文学创作中,汪曾祺极为看重语言。他认为语言要多方学习。语言的独创性,“不是离奇、生造,而是别人想说能说,但没有说或说不出来,你把它准确地说出来,别人一看,你把他的意思说出来了,并且感到新鲜、准确,独特,这就是独创性”(《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81页)。在《林斤澜的矮凳桥》一文里,汪曾祺直言读他老友的小说有些费事,没有把握写这篇评论。他“佩服”一些评论家“能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得作家自己目瞪口呆”。他抓住“桥”“幔”“人”“涩”四个点,指明了林斤澜小说的特征和意蕴。林斤澜把温州话熔入文学语言,汪曾祺以为是成功的,但又建议不妨把语言“稍为往回拉一点,更顺一点”,将“顺”和“涩”统一起来(《汪曾祺全集》第9卷,403-410页)。
汪曾祺还有一篇专门写林斤澜的文章,题目取得有特点——《林斤澜!哈哈哈哈……》。汪曾祺说斤澜的哈哈笑很有名,是他的保护色。在“反右”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成了“漏网右派”。但汪曾祺话锋一转,说斤澜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他认为萧军有骨头有侠气,真是一条汉子;“文革”后,文联作协批斗浩然,只有他忽然大叫“浩然是好人哪!”当场昏厥(《汪曾祺全集》第6卷,330页)。
三
1987年3月10日
……在信中,我往往读到他(陈志华),于是,我进一步明白了,他的文章所以为建筑以外的人所爱读,就因为他在谈建筑的时候,所着眼的并不仅仅是建筑。
陈志华先生已于去年初过世。秋鹭子(刘晨)自1997年7月1日起,入选清华大学建筑历史研究所乡土组,跟着陈志华、楼庆西和李秋香诸位老师做一年毕业设计。她说,“文章里的陈先生嬉笑怒骂,颇有几分狂狷之气”,“只是现实里的陈先生更沉稳淡定”。当年秋,一行人前去江西流坑村调研和测绘。陈先生不给学生讲干巴巴的理论和方法,“想让我们尽量深入而全面地了解这个村落,触摸它的过去和现在,它的丰富多元的建筑、里面的思想和生活”,其实这就是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志学者最根本的田野工作方式(《一起走过的日子——追忆陈志华先生》,“山水澄明”微信公众号,2023年1月20日)。秋鹭子的回忆,可以证明扬之水所言非虚。秋鹭子也写得一手好文章。
四
1987年9月24日
读《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此乃周作人三本小书的合集。页二八言及阳湖钱振锽著《谪星说诗》乃发议论曰:我读了这三十和十八篇文章(均指韩退之文)都不觉得好,至多是那送董邵南或李愿序还可一读,却总是看旧戏似的印象。不但论品概退之不及陶公,便是文章也何尝有一篇可以与孟嘉传相比。朱子说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是如此,韩文则归纳赞美者的话也只是吴云伟岸奇纵,金云曲折荡漾,我却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近来袁中郎又大为世俗诟病,有人以为还应读古文。中郎诚未足为文章模范,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
想日前读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第五节“骈文之论”有云:拿这种文章(指魏晋骈文)与所谓唐宋八大家相较,同一说理,却是风度大两样了。譬如演说,八大家(尤其是宋人)仿佛是揎拳掳袖指手划脚的演说,声音态度可以使人兴奋,然而久听之后,不免嫌他粗豪过甚,没有余味。如其不然,便是摇首摆尾,露出酸腐的神情。再不然,便是蹑手蹑脚吞吞吐吐一味的矫揉造作。
扬之水读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是岳麓书社版本。第一段出自《苦茶随笔》的《厂甸之二》,实际上截取了原文中一长段的后半部分。周作人抑韩扬陶袁的意思很明显,称韩愈的文章是“策士之文”。所谓的三十篇和十八篇,吴云、金云,指的是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吴闿生的《古文范》所选的韩文。周作人是有感而发。扬之水称“言及阳湖钱振锽著《谪星说诗》乃发议论”,其实周作人是据《谪星笔谈》卷二所云:“退之与时贵书,求进身,打抽丰,摆身分,卖才学,哄吓撞骗,无所不有,究竟是苏张游说习气变而出此者也。陶渊明穷至乞食,未尝有一句怨愤不平之语,未尝怪人不肯施济而使我至于此也。以其身分较之退之,真有霄壤之别。《释言》一首,患得患失之心活现纸上,馋之宰相便须作文一首,或馋之天子,要上万言书矣。”这一节话,周作人十分同意,于是有后面的议论(《苦茶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29-30页)。
第二段瞿兑之称唐宋八大家(尤其是宋人)的文章在风度上逊于魏晋,在意思上和前段相通。周作人引冯班《钝吟杂录》,认为宋人好作议论,是坏学风,会“教人胡说霸道地去论事”,还说“常怀疑中国人相信文学有用而实在只能说滥调风凉话其源盖出于韩退之,而其他七大家实辅成之”,所以“读六朝文要比读八大家好,即受害亦较轻,用旧话来说,不至害人心术也”(《风雨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34、36页)。后来周作人进一步发挥,将宋人好作议论与清末以来考试取士改用策论联系起来,直陈其中的弊病,即“只好以不知为知,后来也就居然自以为知,胡说乱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风雨谈》,53页)。扬之水在阅读中触类旁通,将两条笔记放在一块,是发人深省的。

五
1987年10月18日
梵澄先生对渐师很是心折,再三称誉其文章之美,当下让我与他并坐案前,为读其记散原一文。果然文气浩博,凡顿挫处皆有千钧之力,而叙事又多欣戚之感。
欧阳渐的《散原居士事略》有一句评价:“彻始彻终,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这是知己话,沉痛语。
六
1987年10月19日
与我谈及先生之挚友杜南星,欣慕之情溢于言表。道他乃极聪慧之人,不仅是诗人,而且就镇日生活于诗境之中。并说,世有三种人:其一为无诗亦不知诗者,即浑浑噩噩之芸芸众生;其二为知诗而未入诗者,此即有追求而未能免俗之士;其三则是化入诗中者。而杜氏南星,诚属此世之未可多得的第三境界中人。
杜南星即杜文成。张中行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过他。《流年碎影》中有这样一段话:“他青中年时期写了不少新诗和散文,到老年锐气减了,安于在柴门小院里与鸡兔为伴,由于我的劝说和催促,才译了两本书,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和辜鸿铭的《清流传》。我,怀抱我的偏见看他,有拔高的一面,是诗意多,有下降的一面,是应该顾及的也不管不顾。这下降的影响,可举的例很多,只举大小两个:大是应该写得更多而没有写得更多;小是经手的书不少,单说自己写的十几种,竟也丢得片纸无存。近来他记忆力减退,证明脑力差了,如果差到不宜于看书,那就片纸无存也关系不大了。”(《流年碎影》,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116-117页)比起日记中的“欣羡之情”,这番话更全面准确,兼有老来万事休之意。不问世事,不计得失,似乎就是晚年南星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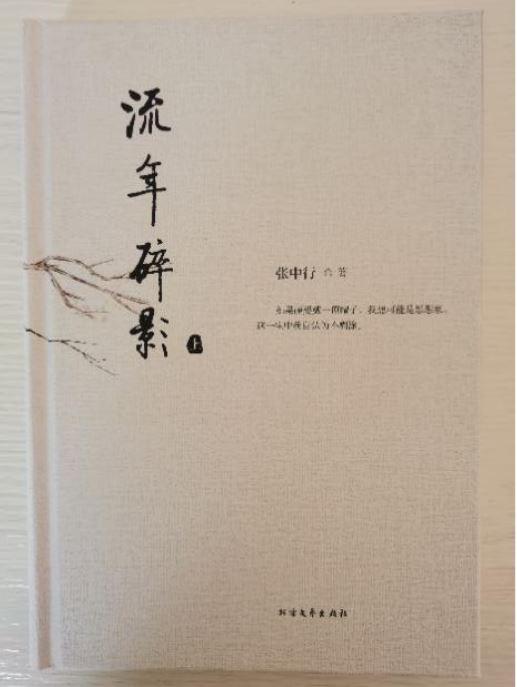
七
1987年10月25日
读《王季重十种》。昔读张宗子《琅嬛文集》中之《王谑庵先生传》,知其乃一不入流俗的骨鲠忠烈之士,颇为他的浩然之气所动。今读谑庵文集不数页,即为其文磅礴真气所夺,几回欲废卷长啸。最堪心折者,“杂序”也,“游唤”也,“历游记”也。“杂序”一门,多属为亲友旧交诗集文集所作,其笔锋老辣,文章纵横,又谐谑生色。每于开篇起突兀之笔,提一篇之气,而于终卷弄铿锵之音,使结响无尽,玩其辞意,真有唾空一世之慨。
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也收有《王谑庵先生传》。言其“五十年内,强半林居,乃遂沉湎曲蘖,放浪山水,且以暇日,闭户读书”。他的游记别开生面,博采众长,自称“吾何取焉,苏长公之疏畅,王履道之幽深,王元美之萧雅,李于鳞之生险,袁中郎之俏隽,始尽各记之妙,而千古之游,乃在目前”。又言其“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近代散文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65、202页)。他的“谐谑”,在于不怕得罪贵人,以至于“偃蹇宦途,三仕三黜”,最为人所知的是其斥马士英的“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二句。后竟绝食而死。
周作人引《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乙巳七月二十二日条下关于谑庵一节——王弘撰在《甲申之变论》中责难谑庵于顺治初寄书解允樾,“其词悖慢”,追咎神宗、熹宗,“继之以崇祯克剥自雄”——认为王季重论明亡原由是极正当的,但“中国政治照例腐败,人民无力抵抗,也不能非难”,明非亡不可,却不幸亡于满清,使得骂明似乎亲清,“明之遗民皆不愿为”,谑庵却有此魄力说出口,因此他的这种“刻责忤俗”是“另一可佩服之点”(《风雨谈》,84-86页)。
八
1992年11月4日
午后访梵澄先生。提到贺麟先生谢世,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沉吟半饷,然后摇摇头。……又道:“要我心里流出来,欲罢不能的时候,写下的才是好文字,若是外来的压力,就一定写不好。”……
“贺麟是有风云之气的。”“那么先生也是有的了?”“我可没有,我只有浩然之气。”“那鲁迅先生有。”“对,那是大大的风云之气。”
随便聊了一会,聊到王湘绮,说起他的那一回“齐河夜雪”,我说:“王湘绮是有风云之气的。”“对,但‘齐河夜雪’一事,可见他的‘风云守道’。”……
“要我心里流出来,欲罢不能的时候,写下的才是好文字”,此为经验之谈,非如此不能接近东坡所言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遵命应时之作,非发自肺腑语,不表见性情,势必斧凿痕太重。扬之水写“辛丰年”,是“写得顺手,改得辛苦”,写“杂拌儿”,则是“写得极顺手,几乎是文不加点,读来也觉流畅”。一大原因在于后者是写自家事,由内而发。
此处的“风云之气”“浩然之气”,不好理解。前者大概是一种“英雄气”,吞天吐地,能造时势,趋向于经世、权变,后者似乎更多强调一种内在力量,近乎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徐梵澄说王湘绮“风云守道”,贺麟去世后,他写的一副挽联中也有这四个字。1987年11月2日,扬之水曾在徐家录下一首《王湘绮齐河夜雪》,可解释徐梵澄此说。王湘绮还有玩世不恭的一面。《花随人圣庵摭忆》载:“又民国元年湘绮生日,忽著朝珠、补褂、红帽,延宴宾客。谭祖庵方为都督,诣之,庄语谓之曰:‘清既亡矣,先生何事服此?’时祖庵适衣西装,湘绮执袂曰:‘我与汝穿的都是外国衣服。’相与哄堂一笑。”(《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19年,20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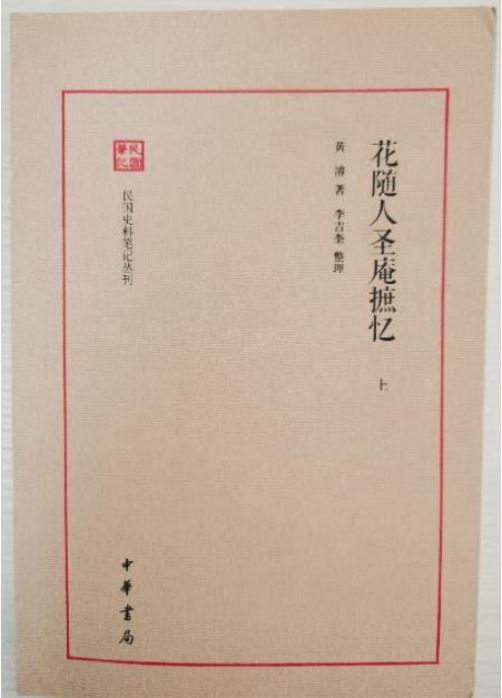
至于鲁迅先生的“大大的风云之气”,不敢妄言,暂且以其致许广平参考的“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为例: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绝不会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5-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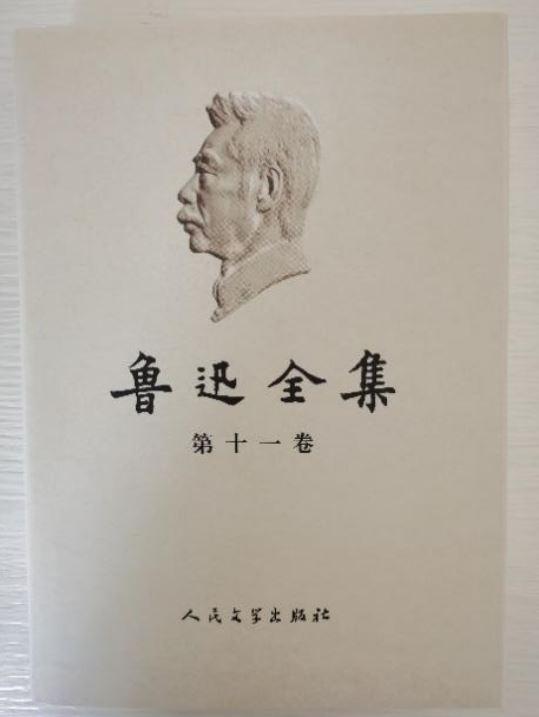
九
1993年2月16日
纷纷扬扬一日雪,落地化,落在树上却不化。忆及梁鼎芬致吴庆坻书简中的几句话:“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似可自况。只是父母在不得言翁;旧书一二种,喜鹊三两只,却是即目。于是将此数语抄与何兆武、周黎庵、周一良、朱维铮诸先生,就便约稿。
此景此人,合一俱化。《花随人圣庵摭忆》内有一则,与之相类,可见梁鼎芬处世态度:“又节庵知武昌府时,其夫人曾来视之,节庵衣冠迎于舟次,住署中三日而去,世所传‘零落雨中花,旧梦难寻栖凤宅;绸缪天下事,壮心销尽食鱼斋’一联,即是时所作也。”(《花随人圣庵摭忆》,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