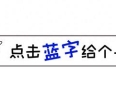【中国故事】
作者:刘荣书(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
收徒弟这件事,父亲回家,自然会跟家人提起,我们却都没有在意。徒弟是一种什么身份呢?一位通事理的长辈如此解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爸爸,以后就多了个儿子。论年纪,这徒弟比你们姐弟几个都要年长,你们应该称呼他“哥哥”。以后,他就是你们的义兄。
哦,义兄。我初次听到了这雅致的称谓。

插图:郭红松
1
当年,在我们贫寒而朴素的乡下,“拜年”是一种很重要的礼俗。
大年初三,我家的篱笆院门会早早地敞开。我那年近花甲的父亲,将院门口清扫一番。若是下着雪,他会将门前的积雪清除干净,瞧他那认真的态度,恨不能将大路上的积雪也一并清除。上午十点钟左右,他会去村口张望,披一身碎雪回来,不无失落地对我母亲说,小袁或许不来了吧?母亲说,雪这么大,恐怕不能来了。
即便下着雪,即便下得“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只待临近晌午,便会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村外的一条土路上赶过来。积雪使他不能顺利地骑行,他便迈开长腿,一跐一滑,推着自行车,步行抵近了我们的村子。拐过两条街巷,绕过几户人家,推开我家的柴门。这时,我父亲正在隔窗观望,对我母亲低语一声:小袁来了。二人便忙不迭迎出门去。
他见了他们,也不纳头叩拜,只是憨厚地笑着,瓮声瓮气地叫一声:叔、婶,过年好哇!我父母嘴里应着:好,好!母亲抬手,为他掸去肩头的落雪。父亲站在一旁,一脸欣慰,嘴里却会埋怨: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是来了!
这个来我家拜年的人,每年初三这天必到。他并非我家的亲戚,而是当年,我父亲收下的一个徒弟。
2
话说当年,在一个叫作“古冶”的地方,有一座煤矿,我父亲委身在那里工作。黑金般的煤炭,帮人苦度荒寒的煤炭,一度为我父亲赢得了尊重。他能帮村里人买到质量上好的煤,不掺一块矸石;那些去煤矿拉煤的人,不管本村人还是邻村人,都曾得到过我父亲的关照——不是留宿在那矿上,便是吃过我父亲从食堂打来的热乎饭菜。我父亲每次回家,总是一副体面的样子。他瘦高个儿,衣衫整洁,不见半点矿工的落魄与邋遢。实际上,他虽说是在煤矿工作,却没有下过一次矿井。之所以会如此幸运,完全仰仗他是一个铁匠。
在那小小的煤矿里,除了矿工,还有铁匠和木匠这两种身份的人存在。结成班组,称作钳工组和木工组。矿井每往前掘进一寸,便要搭建长长的巷道,巷道用木质结构支撑,便会用到木匠;有些地方,要用铁质的“拔锔子”固定,想必我父亲这样的铁匠,就能派上用场。
钳工组里,最初只有我父亲一个人。随着煤矿的规模日益扩大,我父亲要求矿上为他增派一名人手。领导先是举荐了一人,那个油嘴滑舌的年轻人,虽和领导同乡,却没能入了我父亲的法眼。把小袁调过来吧,我看这孩子老实,个儿也高,给我打下手,挺合适的。我父亲说。
相较于井下作业,在地面上从事任何一项工作,无疑都是幸运的。这个姓袁的年轻人,就这样得到我父亲的照护。他长相憨厚,高个子,应该是我父亲能够相中他的原因。我父亲便是一个高个子。烧铁的炉灶,锻铁的工作台,都是他白手起家,按照自己的身高量身定制的。
父亲在世时,偶尔会说起他在煤矿上的那段生活,对于收徒弟这件事,却讲得很少。如今想来,他收下这个徒弟,大概不会有一场“拜师宴”,亦不会有什么相关的礼仪,不会像江湖中流行的那样——我父亲坐在上首,接受着徒弟的敬拜,一拜:日月北斗天长地久;二拜:师徒携手明月九州;三拜:永记师恩功德千秋。行过大礼,还要敬茶,最后,还要递上拜师的帖子……没有,没有这些烦冗的礼仪。这庄严的礼仪,也注定不会出现在一个简陋的、安全事故频发的煤矿里。说起铁匠这一行当,其实并不被很多人看重,它不过是穷苦人讨生活的一种手段。在我们乡下,除了铁匠、木匠、泥瓦匠,还曾诞生过各种门类的匠人,他们传承着粗疏或精湛的技艺,从未举办过任何仪式。只不过师徒间,因一种关系的确立,感情上会更近一层。
自此,身量颀长的师徒二人,便每天委身在低矮的铁匠铺里。
我父亲打上捶,他的徒弟抡下锤。上锤是一把小锤,握在父亲的右手,他的左手,操一把铁钳,钳头夹住一枚通红的铁器。随着一下一下锻打,铁器渐渐改换了模样。师傅的敲打,是引领;徒弟的夯砸,是追随。小锤敲过,大锤落下,溅起的火星,仿如微小焰火。
父亲那时候说起他的徒弟,总是赞叹不已。他说:你小袁哥啊,有眼力见儿。
即使不能亲眼见到,我也能够想象,父亲当年收下的这个徒弟,会怎样履行一个徒弟的义务——上工时间未到,他便会早早来到铁匠铺,生起炉火,将杂物和铁屑清扫干净。他将一把铝制水壶,吊在炉火上,烧一壶开水,先将一只写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搪瓷缸子注满。而后将剩余的开水,灌进一只竹壳暖水瓶中,以备师傅一天的饮用。即便是夏天,我父亲也习惯喝开水,他一人微薄的工资,养活他的五个孩子,常常食不果腹,半夜饿醒,怕伤及肠胃,不敢喝凉水,只能灌一肚子滚烫的热水。到了午饭时间,如果师傅累得不想动,徒弟便会拿着两只铝制饭盒,一只搪瓷盆子,从食堂打来饭菜。两只饭盒里,各自盛着师徒二人的午饭,搪瓷盆里的菜,合二为一。他端着筷子,吃相斯文,等着师傅先把饭吃完,然后才会狼吞虎咽,将剩下的饭菜一扫而光。吃完了饭,他会将菜汤兑了开水,上面浮一层油花,端给师傅,算是孝敬师傅的一碗饭后“高汤”。
我想象不出做师傅的,会用怎样的行动,来关爱他的徒弟。却知道父亲脾气好,注定会成为一位慈祥的师傅。
3
天下苍生,为师者众,为徒者众。如今想来,若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父亲和他的徒弟,注定只会保持一种师徒间的泛泛交往,不会结下一段如父如子的情谊。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父亲所在的东风煤矿,距离唐山市区三十公里,震感强烈。据我父亲说,他半夜饿醒,从床上起来,想去暖瓶里倒些热水,觉得天旋地转。起初,他还能沉得住气。悬在房梁上的灯泡激烈摆荡,整个屋子随之摇晃起来。停电了。这才发现,窗外夜色诡异,西边的天际被一道蓝光照亮。有人在屋外嘶喊。我父亲受了惊吓,摸黑去开屋门,门扇变形,推拉不开。他慌不择路,从窗子翻了出去。刚跑出外间的大门,只听身后传来一声巨响,一根水泥横梁,险些砸中他的脚跟。
天蒙蒙亮。矿区内一片狼藉,宿舍和食堂倒塌,风井架子东斜西歪。空中飘着小雨,雨水让遭劫的人们迅速清醒。哭喊声、呻吟声此起彼伏。蓬头跣足的工友,在废墟间鬼魅般游荡,嘴里喊着某个人的名字。矿上工作的人,大都沾亲带故,一旦自己死里逃生,自然会想起亲人。正是他们的呼喊,让我父亲想起他的徒弟。
他赤脚,朝徒弟所在的宿舍赶去。左脚被一枚钉子扎伤,也丝毫未察觉。面对被夷为平地的宿舍,我父亲嘶声呼叫,无人应答。他在废墟中翻掘,直接找到大炕的位置。檩木堆叠,横七竖八,搬开一块块砖石,掀开一根根檩木,最先找到一只千层底布鞋,足有45码。看到这只鞋子,我父亲心里更加紧张。雨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蒙住了眼睛。他的双手沾满鲜血,不知是被檩木扎伤,还是被砖石划破。又掘出一件褂子,褂子上密布着被铁屑烫开的破洞,找到一只黄色旅行包,那是徒弟每次回家,必带的一件物品……他终于扒出一只脚。脚弓微弯,脚跟朝上。我父亲吓了一跳,伸手抻拽,纹丝不动。此时,他已精疲力竭,险些哭号起来,所幸手心感到一丝温热,发现徒弟的脚掌和腿肚,都是热的。不知从哪儿生出一股力气,他搬开一根粗大的檩木,将徒弟的身子从瓦砾中扒出来。徒弟俯身趴着。我父亲抱起他,拍打他的脸颊,喊着他的名字。大概因空气流通,又有雨水醒脑,徒弟慢慢醒来,叫了一声:叔……刚才咋回事?迷迷瞪瞪,我头上挨了一家伙,就啥都记不住了。
我父亲喜极而泣:傻小子,刚才地震了。
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父亲在他徒弟的心目中,应该有着身份上的双重寓意——他是他的师傅,因了一句古训,相当于他的父亲。他收他为徒,不使他去黑暗的井下劳作,免于经受死亡的恐惧;他传给他手艺,等于赠予他安身立命的衣钵;地震时救了他的命,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况且这个徒弟,被他的家人极为看重,对于他们那个三代单传的家庭来说,我父亲便显得非常重要。至于后来,他同徒弟以及他的家庭有过什么交往,我便不太清楚了。只恍惚记得,徒弟结婚,我父亲作为证婚人,专程去过他的老家。其后这师徒二人,又在矿上工作厮守了几年。大概是陷入传宗接代的恶循环,徒弟的媳妇,接连生下两个闺女,不能完成传宗接代的大业,便要不管不顾地继续生下去。再生,终于得偿所愿。按照当时的规定,难逃责罚。这个徒弟,只能卷了铺盖卷,黯然回乡,被打回农民的原形。
那段时间,这一对师徒,似乎中断了来往。
好在又过了几年,我父亲从矿上退休,回乡继续为生活苦熬。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他的徒弟便欣然前来了。不知有过什么约定,以后每年的正月初三,他都会骑一辆自行车,赶来我家拜年。
初见这位“义兄”,果然如传说中那样高大。长条脸,阔嘴巴。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双细长的眼睛,裹在肿眼泡里,每每看人,低眉垂目。说话瓮声瓮气,在我父母面前,时刻保持一种谦恭的姿态,仿佛一个从旧时代活过来的人,战战兢兢地,面对他的高堂。
最初几年,他一个人来。后来,带他儿子来过几次。那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长相机灵。先是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后来,自己跨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路途遥远,不免乏味,这孩子便会从车子上跳下来,跟在他骑车的父亲后面,跑上一气。见了我父母,乖乖叫一声:爷爷、奶奶,过年好!纳头便拜。我父母喜不自禁,忙不迭塞压岁钱给他。我在一旁观察,发现这孩子磕头时,义兄会看我父亲一眼,一脸庄重。让人恍惚觉得,那跪在地上的孩子,成了他的替身。他是让他的儿子,代替他行那叩拜的大礼。
自此,我家便多了这样一门特殊的亲戚。
不是血脉相通的亲人,胜似亲人。除了拜年,乡里人家的诸多礼俗,也在我们两家人之间延续。我记得我们兄弟三人结婚,生小孩摆满月宴,我的义兄都会赶到,随了礼,夹杂在我的真正的亲戚们中间,脸上露出由衷的微笑。除此之外,偶尔他来这边办事,也会抽空,专程来探望我的父母。
5
我的父母终究是老了。
我母亲于2000年7月离世。按照乡俗,家中有人过世,会派人给亲戚送达“奔丧”的消息。或因悲恸,我父亲显得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就忘了他的这位徒弟,没有将我母亲过世的消息通知到他。
这一年秋天,义兄不知何事前来。得知我母亲离世,潸然落泪。执意要我带他,去我母亲的坟上祭拜。
我带着他,从村里的小卖部买了烧纸,我们兄弟二人,走过一条泥泞的机耕路,蹚开疯长的茅草。母亲的新坟如此低矮,经不住雨水啃噬,待到添坟,还要等满三年的守孝时间。只见他在坟前画个十字,用火柴将纸钱点燃。跪倒在地,动作迟缓,连磕三个响头。他的哭泣,以及他的哀容,令我羞愧。想起母亲下葬时,我竟然没有哭过一声,只待将母亲的骨灰送入坟墓,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到此生再也没了母亲,这才大放悲声。他是我的义兄,却如同我一奶同胞的兄长,面对我母亲的坟茔,如此虔诚地叩拜,如此悲切地痛哭,我便在心里,与他更多了一层亲近。
那一年,他仍来给师傅拜年,却没有留在家里吃饭,怎么留也留不住。想一个没了母亲操持的家庭,毕竟残缺,温馨与和睦的感受,即便在我们亲姐弟之间,似乎也很难找回了。
又隔了一年,我父亲仓促离世。
作为留守家中的老儿子,那一年,我34岁,虽为人父,却仍旧懵懂。不仅要忍住悲恸,还要照应整个葬礼。依旧是,我没有想起这位义兄,没有将他师傅去世的消息,及时通知给他。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从失去亲人的哀恸中渐渐走出来,我也没有想起过他——真是罪过!
到了这一年的12月,一个朔风呼号的冬夜,家里的座机忽然响了。由于父母患病期间所受的惊吓,那些日子,我最怕夜半响起的电话铃声。我从梦中惊醒,心惊肉跳,光着身子,接听了电话。
喂,谁呀?
是我……
我听出对方的声音,正是我的义兄。是袁哥呀?我说。他应一声,陡然问道:听说我叔过世了?我“嗯”一声,有些不知所措。刚想说点什么,却听他说话的语气变得愤懑起来,质问我道:我叔过世,为啥没通知我。他说话的尾音,有些嘶哑,让我感受到隔空而来的悲恸。我握着话筒,身子在寒凉里瑟瑟发抖,愧疚得说不出话来。又听他说了几句什么,电话随即挂断。
此后,我就再也没了这位义兄的消息。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想起过这位义兄。直到近年,往事纷至沓来,梦境也一径朝着流逝的岁月沉落,这才不合时宜地想起了他。
我的这位义兄,长我大姐几岁,也该是步入花甲的年纪。我没有记住他的大名,不知他家住何处。只知道他姓“袁”,是我父亲早年收下的一个徒弟,与我家,有过一段至深的交往。除此,一切随风,都将流散在陈年岁月里。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4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