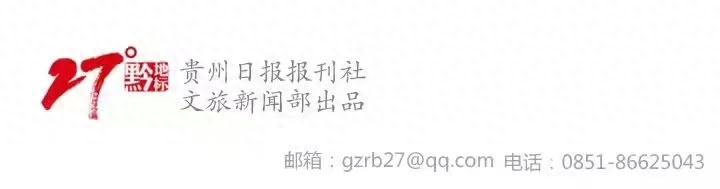
我的家坐落在盘州市与普安县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一条蜿蜒的小河成为盘州和普安两地的分界线,因此家乡得名“隔界河”。
20世纪70年代初,4岁左右的我当时刚记事,现在还依稀记得村里没有学校,为解决山里娃的上学问题,父亲作为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主动带领村民自力更生,建成了我们村的第一所“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只是具备了可供学习上学的基本功能。学校的外墙是村民就地取材用青石砌的,房顶的瓦是村民自行烧制,檩条椽子、毛坯门框和窗框是父亲从广西请木工师傅在我家院坝改制而成。父亲在经济负担特别重的情况下,请木工师傅在家吃住近一个月辛苦改制。后因实在没钱,没有制作课桌和凳子,就用毫不规则的木板搭在胡乱用青石块堆砌而成的石墩上,也没有水泥黏合,石墩摇摇晃晃,上课时“桌凳”倒塌是家常便饭。通常学生们聚精会神听课时“咣当”一声,大家匆忙从地上爬起来有条不紊地垒石墩、捡书本、搭“课桌”“板凳”,门和窗户均没有安装,夏天漏雨冬天漏风,这些都丝毫不影响上课秩序。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学校五个年级俱全,当时共五位老师,一人负责一个班,每个班就是一个年级。老师们都是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的民办老师,尽管自身文化不高,但都很“全能”,同时教授语文和数学,而父亲便是学校的负责人。
儿时的我特别讨厌这个地方,木板拼接的黑板总能扬起大量的粉笔灰,相当刺鼻和眯眼,加之教室是泥巴地面,又无门窗遮挡,坑洼不平的地面刮风下雨时,雨水总裹挟着泥土夹杂着粉笔灰肆无忌惮地拍打在父亲瘦弱的脸上,父亲时常咳得喘不过气来,背上背着的我也跟着咳嗽不止。父亲就在这种“风来风扫地,雨来雨洒水”的简陋环境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守,一晃就是近40年,就这样一批又一批,一拨又一拨把大山里的孩子送出山沟沟……
那些年感觉冬天格外的冷,早上屋檐下总有些长短不一的凝钩,看上去晶莹剔透,漂亮而冻人,父亲用那件已有几个破洞的蓝色大衣把我裹得严严实实,走上熟悉的教学路上,生怕弄脏了母亲纳的白毛底鞋。一路上,同龄的小朋友们提着用坏了的铁锅、铝盆简易制作的“神器”,物尽其用来取暖。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手中也多了一个“豪华”物件“灰笼”,外面是竹丝编织,里面安放一个泥土烧制成的灰钵,灰钵里放些未完全燃烧的木柴块。到学校后,父亲把我“安顿”在座位上,把我穿着母亲纳的白毛底鞋那双小脚放在“灰笼”上,然后是查看班上的小朋友有没有冻伤。
我喜欢读书,但我痛恨开学,因为开学的头一天凌晨,父亲指定会撇下我独自到12公里外的镇上背课本,沉重的大背篓会“侵占”父亲的肩膀和后背整整一天。直至傍晚,见到父亲时父亲脚上的解放鞋早已被汗水浸透,肩上有两个补巴的灰色衬衫粘贴着后背,花白的头发滚落出豆大的汗珠,浸湿着父亲脸上的皱纹、脖颈、前胸顺流而下,母亲心疼地叫我端来一盆热水给父亲泡脚。父亲汗干后,残留的汗渍在那件灰色的衬衫上弯弯扭扭画出大大小小的版块,好像只有粉笔才能将其归纳。
1988年,大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们的小山村沸腾了,大伯伯、三叔、幺叔与父亲一起送大姐去贵阳读书。我童言无忌地问大伯伯:贵阳远很嘞,你们有钱不得嘛!惹得众人哄堂大笑。后来,四个老者东凑西凑,一起送家族的“骄傲”去了贵阳,这趟贵阳之行也成了叔伯们在村民中最为荣耀的谈资。每次我都能听到父亲讲“大十字”,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要默写的生字却由20个、25个、30个一直在递增,要求也越来越严,不明所以“大十字”到底有什么魔力,神奇的“大十字”已悄然成为我儿时最神往的地方……
长大后我终于明白,父亲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大十字”看到了城市繁华、城乡反差巨大,切身感受教育对山乡孩子的重要。父亲在“大十字”的人生路口果断抉择,日复一日继续着他的使命……
去年6月,父亲病倒住院,我一直在他身旁陪护。带着万般不舍,父亲终究还是走了,他的坚守和执着却永远刻在了我心里。
文/ 杨顶
视觉/赵珊珊
编辑/邱奕
二审/曹雯
三审/黄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