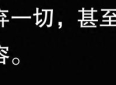齐鲁医院附近有家外贸店,我常去,要经过一条无名的短马路,在济南市区交通图上找不到它。马路左侧,一幢幢高楼比肩耸立,右侧,几乎完全被围墙占据。在围墙沿河畔转角处,有一间只能算作是房子的建筑。房盖是油毡纸的,窗上无玻璃,木条十字交叉钉着蓝塑料布。每次经过这里我都要捂住鼻子,污染的河水散着浓浓的臭味。
那“房子”里住着一对儿外地来的乡下夫妻,他们在那里为济南人弹棉花,已在那儿住了6年了。夏天的蚊子就不用说了,刚过去的暴雨让我想起他们,还好,他们正在收拾残局,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局。这个城市总是繁华和破败同生。
我第一次坐下来,和女主人聊天。他们有—个女儿,两岁。在乡下由他们的父母轮流抚养着。女人问我的衣服从哪里买的,我告诉她从贵和,她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目光,什么也没能阻碍女人之间的交流,就像我感触的泪水。回到家我开始敲下面的文字——他们的一次春节。我的表达比女人的语言生动,但剧情终究赶不上现实。
春节前,他们原本打算回乡下去与亲人们团圆的。活儿积压得多,就日夜突击地弹。最后一件被人满意地取走了,这一忙完,才想起今天是除夕。
女人说:“你什么也别管了,该收拾的我收拾,你快去买晚上的火车票,咱们得争取初一这时候到家是不?”男人带着一头一脸一身的棉絮,匆匆地出了门。
他回来时,女人什么也没收拾,在床上酣睡着。那是张旧单人床,加宽了一块板,用些砖垫着。这几天,女人感冒没有好,她的睡状,像个困极了的孩子。她的一只手臂垂在床下,一条腿也垂在床下,而且脚蹬着地,仿佛那只脚在酣睡的情况下还使着劲儿似的。显然,男人刚一走,她就那样子扑在床上了……酣睡着的女人,两颊绯红,口水从她半张着的嘴角流到枕上。男人俯下头去,用自己的脸颊去贴女人的脸颊。女人还在发着低烧,并没被她男人的脸颊贴醒。她也和他一样,满头发满脸都是棉尘。这使她的头发和眉毛看上去像是灰白的。然而女人毕竟才26岁,又是少妇,女人味儿是棉尘所无法消减的……
终于,他忍不住双手捧着她的脸颊,用自己厚实的双唇严密地封闭住了他女人的嘴。女人一时喘不过气儿来,便醒了。她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你真烦人,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呢?怎么什么也没收拾就睡过去了呢……”
男人说:“今天,咱们……走不成了……”说得吞吞吐吐。
女人这才将目光望向男人的脸,自己脸上的表情顿时起了变化。
“你哭过?”
“没……没有……”男人掩饰地将头扭向一旁。
“你明明哭过!咱们今晚怎么走不成了?你把买票的钱丢了是不是?你倒说话呀!”女人急了。
“没丢没丢!今天的票卖光了。”
“你骗我!”女人的眼里也出现泪光了。三百多元对于他们是一笔大钱,女人没法儿不急。
“没丢就是没丢嘛!哎,自打咱俩结婚,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男人赶紧掏出钱给女人看。
女人放心了,但有家难回的失望使这年轻的乡下女人一时怔住了。
“有明天的票……”可我没买,明天都初一了,春节主要过的不就是三十和初一嘛。初二下午才到家,咱俩还不如不回去了……就在济南过春节吧!咱俩还没在济南过次春节呢……
女人忽然双手捂脸哭了。一年12个月,天天弹棉花,就盼着回家过春节。男人走到她跟前,将她的头搂在怀里,以哄孩子那种语调说:“听话别哭,再哭我可不高兴了。”
女人不哭了以后,男人用半截铅笔在一页纸上写着什么。他将那页纸递给女人看,女人走到桌前,拿起铅笔划去几个姓名,添上几个姓名,更改了一些姓名后的数字……
再以后,他们点了些钱,揣了那页纸,都顾不上换身衣服,双双赶往邮局。那时已经4点多了,他们怕邮局提前下班,很快地走。汇完了款,女人还想往家乡打长途电话,邮局工作人员此时已经往外拎邮包了。男人看了一眼电话,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来。邮局人员说:“打吧打吧,有多少话只管说,我们等。”很少被这么和气这么友好地理解过,这话使夫妻俩心里暖烘烘的。
再回到“家”里,夫妻俩就开始收拾。乡下人也保持着干干净净过春节的习惯。她说:“无论如何也得洗个澡。”
他说:“对,咱们也享受一次,去桑拿。”
于是妻子接着水管子里的凉水绞了把毛巾,马马虎虎地擦了擦自己的脸,也替丈夫擦了擦脸,就赶紧和丈夫出门了。
当男人换上带去的一身崭新衣服走到外边时,他几乎不敢认自己的女人了—坐在长椅上望着自己的那个女人,真的是自己的妻子吗?她头发湿漉漉的,脸红扑扑的,仿佛眼睛也用香皂洗过了。
其实谁都知道除夕的车票比较好买……
第二天,我将一包衣服放在他们家门口。其实生活的悲喜都由自己导演,每个人心里都渴望真诚的一句话:你就是我一辈子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