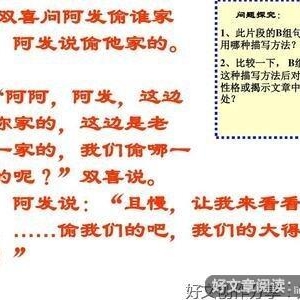郭晓琦一九七三年生于甘肃镇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有诗歌、散文随笔及小说作品在多家文学刊物发表,并入选多个年度选本。曾获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等奖项。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四届“青春诗会”。
这么说吧,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宅男,平时除了上下班出门走几步外,从来不去参加任何应酬活动。倒不是懒,也不是装什么深沉。我是怕见人,从小就怕。为此,刘欢喜没少训斥我。说我就一个没出息的货,太把自己当回事。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我就是改变不了。

那晚,我之所以趁着昏垂下来的夜色去了趟公园,是因为去看望刘欢喜。刘欢喜死了。一个月之前的一个礼拜天,刘欢喜死在了公园里。说是和几个半老徐娘玩牌,接了把“豪华”绝牌欢喜死的。刘欢喜的死,对我打击太大。他是我唯一的哥们,能掏心扯肺,甚至舍命的那种。刘欢喜活着的时候,怼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出去玩玩,能死人”?没想到,他还真是出去玩死的,有点儿一语成谶的意思。刘欢喜死后,他怼过我的每一句话,都活了过来,乐此不疲地缠绕着我。仿佛刘欢喜还活着,趴在耳边不停地叨叨,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突然想明白了,我得去公园看看刘欢喜,顺便给他送点“钱”。
公园的名字有点儿诗意,叫雁儿鸣。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公园周边的黄河大滩曾经水草丰茂,瓜果飘香。滩里常有大雁栖息觅食、鸣叫嬉戏,因此而得名。另一说是公园中心湖里有无数泉眼,泉水涌出时,会发出近似雁鸣一样的声音。其实这名字的由来,于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园里人来人往,处处热闹喧腾。我怀里揣着“东西”,像个贼一样,窥探了大半圈,愣是没找见一个能给刘欢喜顺顺当当送到手的僻静地方。我怕火一点着,会被戴红袖章的管理人员抓个正着。后来,我发现环绕着中心湖密密扎扎的树丛里,隐藏着一条深褐色的跑道,相对要隐秘些。
我猫着腰,沿跑道往前走。有跑步的人超过我,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散开在足足有五六米宽的环湖跑道上,就显得稀稀拉拉。到了弯道处,我探头探脑正寻找“办事”的地方,身后突然有个声音追上来,带着一股青春的热气。我下意识向道边躲了躲,还未来得及回头,就被结结实实地撞上。
我们倒在一起。
我吼了声,应该是“眼瞎啊”什么的。反正,我感觉身体的某个部位被顶出了一个大豁口,心里瞬间也升起一团怒火。青年人敏捷,已经爬了起来,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听声音,我才明白是个女孩。女孩踩着白色的轮滑鞋,穿超短毛边牛仔裤,白色长袖运动衣,白色鸭舌帽,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直溜溜地杵在我面前。我仰头瞅了瞅,女孩细高细高,仿佛是从树阴间直戳下来的一束月光,白晃晃的。
对不起,大爷。
女孩的声音还算柔和,但冷,像一滴滴渗饱了月光的夜露,从高处坠落下来,落在我的额头上、耳廓上,然后破碎。
大爷!谁是大爷?
好,大叔。对不起啊,大叔。
说完,女孩嘿嘿地笑。她竟然能笑得出来。
疯子!我一直认为踩着轮滑在大街上飞驰,或蹬着滑板在车流间横冲直撞的年轻人,基本都是疯子,拿生命开玩笑。没想到,我第一晚出门,就鬼使神差地遇上了,真够倒霉的。我心里那团滚动的火焰,被女孩轻蔑的笑声又吹旺了些。这是你玩轮滑的地方吗?我一边责问,一边悄悄把右手伸进怀里捏把了下。香折碎了,紙糊的手机压瘪了,冥币和蜡烛还好,没散开。
哦?那请你告诉我,哪儿才可以玩轮滑呢?女孩反问。
我被问哑了。很显然,我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公共场地,你能随意溜达,别人就玩不成轮滑?我努力压压火气,没再说话,顺势挪下屁股,坐在道牙上。
喏。女孩伸过一只手,要拉我起来。
那应该是一只经常在钢琴的黑白键盘上恣意跳跃的手,皮肤白皙、五指修长。我愣了下,没有回应。从七岁开始,跌跌绊绊活到了五十岁的坎上,四十多年,我轻易是不会向别人伸手的。
怎么?碰瓷吗?
女孩的声音依然柔软,也还是那种渗饱了月光的露水一样圆润,但口气却十分冲,绝对是愤青们的莽撞味道,听起来不怎么顺耳。
碰瓷我也不怕。女孩补充一句。
啊?我又吼了声。你从哪儿看出我是那种人?
不是吗?依我看,你的行为至少符合碰瓷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笨拙了些。新手吧?肯定是,一看就不熟悉业务。你得去马路上找豪车,那样才有效益。
话说到这份上,剩下的就只有吵架了。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嗡嗡作响,要质问的、要争辩的、要训诫的,话茬子涌到嘴边,很快又咽了下去。凡俗生活中,我只是一颗蔫巴巴的土豆,再光亮点,顶多算一只老番瓜,要和浑身长满尖刺的榴莲较劲,能扯出个子丑寅卯来?再说了,我只是偶尔在这走一遭,划不来争高论低。这样想的时候,我用多半生的经验,把身体里的那团火往下压了压,口气平和地说,我缓一会儿,没你的事了,你走吧。当然,说话的档口,我确实狠狠地剜了女孩一眼。
女孩并没在乎我那个饱满愤懑的白眼,她弯腰揪膝盖上蹭起的白皮,那儿显出一片青紫,有血丝渗出来。听我没事,女孩大咧咧地哼一声,说,好勒,大爷。哦,不对不对,大叔,是大叔。干脆利落的大叔,我喜欢。女孩又嘿嘿笑,然后转身,起步,轮滑哧噜哧噜响起来。也就是女孩的身子摆动起来,就要滑进朦胧光影深处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女孩的动作不怎么对劲,至少看起来是相当的不协调。
空的———
我心里真真切切地颤了下。女孩的一只袖筒随晚风轻轻地飘动,那里面是空的?
我决定去公园跑步。
决心一下,我为那条称心如意的跑道准备了简单的行头。为什么称心如意,我自己也说不明白。跑步鞋我挑了品牌的,白底黑面,轻便防滑,顺畅缓震。运动衣备了春秋服,还选了宽松的大裤头。我当然不会选半袖的,自从我七岁那年弄丢了一只手,从此就与半袖儿无缘。
七点三十分钟,我准时从标有“0”的起点出发。穿过树阴和绿地的跑道果真让人感觉舒坦,灯光朦胧,月光也朦胧……灯光和月光交融着,从树叶间泄漏下来,斑斑点点地洒在身上,铺在脚下。空气湿漉漉的,带着青草味儿、花香味儿。湖畔的古建被彩灯勾勒出骨感的身姿,在一湖波光粼粼的水里晃动……
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毫无例外地在那条跑道上遇见轮滑女孩。其实,是女孩一圈又一圈地超越我。
女孩的穿着没有变化,依然是白色的轮滑鞋,牛仔毛边短裤,白色长袖薄纱衣,白色鸭舌帽。一身白,看上去,她像一片干净又明亮的月光,一圈又一圈地超越我。那些天,月亮一直挂在头顶,格外明亮。因为月光,我看得真切,女孩左边的袖筒会随着身体的滑行有节奏的摆动,那里面是实的,是一条有血有肉有活力的胳膊。而右边的那只袖筒瘪瘪的,任意地垂挂在身体一侧,不时会随风飘起,那里面是黑的、是空的、是冷的,什么也没有……
我有些自责。女孩和我一样,都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我们有过相似的经历和命运。那天晚上,我不该对她吹胡子瞪眼,冒冒失失地吼叫。
这方面,我有过更多戳心的體会,孤立、嘲讽、欺凌……从小,我家境窘迫,生活拮据。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和大我四岁的哥哥,很小就成为父母得力的帮手。七岁那年夏天,是我生命中一个黑色的夏天。那一晚,父母还没有收工,我和哥哥在昏暗的油灯下给老牛铡草。这本来已经是我们兄弟干得很熟练,配合相当默契的活儿,但那晚却鬼使神差地出了意外。平时我都是用右手打回草,那晚我不知道怎么就伸出了左手。很显然,我的左手太笨拙了,没等我顺利收回来,哥哥执掌的铡刀寒光一闪,锋利的刀刃“噌”一声,就铡掉了我的手,像铡断一根鲜嫩的草茎那么简单。哥哥因为那次无法挽救的过失,一直活在自责中,以至于早早退学,打工吃苦力,供给我读书。他认为我只有读好书,考上学,才能活下去。我也因为缺了一只手,被童年和少年时代应有的欢乐抛弃,才一心一意扎进书本里,最后端上了一碗公家饭。
这一晃,磕磕绊绊的人生已逢中年……我叹了口气。想必缺了右胳膊的轮滑女孩,生活中的障碍和艰难,遭受的冷遇和白眼,肯定比我少不了多少。
我开始猜想女孩丢掉另一只胳膊的种种可能。她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少长了一条胳膊,有这种情况吗?几率大不大?我不懂,也没听说过。她五岁或者七岁的时候,因为贪玩而意外触电。或者是,她十五六岁的时候,出了场车祸。不管是什么原因,女孩肯定和我一样,经历过一个悲惨又痛心的故事。
还好,轮滑女孩并没有计较。自从那晚撞倒在一起后,每次超越我的时候,她都会打个招呼。或者侧目一笑,或者来个“耶”的手势,或者打个响指,嘘声口哨。
有一次,轮滑女孩滑到我身边时有意慢下来,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她响亮地喊了声:奥利给,大爷。我没明白。她却调皮地吐了下舌头,可能是意识到自己老是犯同样的错误,急忙改口说,加油,帅哥。接着嘿嘿地笑。
听她这么喊,我也嘿嘿笑了。
女孩说,叫习惯了,不是故意的。
我说,你随意。
女孩问,你知道我第一次为什么喊你大爷吗?
我说,你肯定觉得我老呗。
女孩说,只是你的影子看上去老。
我问,影子也能看出老少啊?
女孩说,当然,我可是这条道上的老手啦!她的声音冷但甜美,一直都是那种渗透了夜露、月光和花香的味道。我们撞在一起的那晚,你的影子黑乌乌的,像一团摇摆不定的荒草。你是揣着心事的吧?肯定是。这条道上的人,我阅过无数次了。谁是经常锻炼的,谁是新加入的,谁是偷偷摸摸玩暧昧的……反正不管男的女的,胖的瘦的,从背影,我就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
厉害!我向她聚了聚大拇指,心里却有些慌张。在热热闹闹的公园里,唯有我揣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去见一个死去的人。说出来,让谁都觉得瘆。
没想到,在你身上竟然看走眼啦。女孩嘿嘿地笑,她又补充说,这可是我第一次在这条道上的重大失误。
看来,我真需要好好锻炼啦。这些年,我基本把自己宅朽了,在你的眼里,连影子也朽了。
喏,你可别灰心啊。你瞧,你才开始半个多月,看上去已经很有型啦!加油啊,大叔。女孩说着猛蹬几下,像一片轻盈的月光划过暗淡的树影巷道,越来越小,最后梦一样消失。
时间进入了伏天,白天总是闷热无比,闷到晚饭时分,头顶就会压上几堆翻腾的乌云。乌云低垂到一定程度,要么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雨,要么刮一阵恶风。去不成公园跑步的夜晚,我像往日一样,翻书、写字,但那颗心不比从前安静,总也安放不稳当。
当然,天气很快就晴好了,大西北的天气,从来都不拖泥带水。每逢这时候,我都会比之前更早一些收拾妥当,来到公园那条属于自己的跑道上。轮滑女孩还是原来的装扮。隔三差五隔三差五,有那么几天,女孩擦肩而过时,并没像以前那样打招呼,只是明亮的月光一样,一闪而过,很快消失在我前方。女孩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又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缘于此,我心里生出一波又一波好奇来。
正是因为一波又一波好奇荡漾着我,使我感觉每一晚的跑步都十分有意思。我甚至一直在注意轮滑摩擦地面的声音,隐隐有哧噜哧噜的震颤,我会有意放慢脚步,慢悠悠地回头。
和以往一样,一截明亮的月光泊在了我面前,亮得几乎使我不能睁大眼睛。
嗨,大叔。女孩喊。
我喘着粗气。
女孩也喘着气,纤细的身体一起一伏。稍稍平稳了下,女孩说,可以借你的手机用一下吗?
手机就捏在我右手里,记步数用。我解开锁密码,屏幕亮了。
女孩拨拉出一串数字,手机嘟嘟响,但那边没人接。女孩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女孩将手机还给我,那条葱白一样的胳膊在我面前一晃,我看见了她白嫩的手腕上方有一朵“梅花”状的印记。那是用烟头烫出来的。看来,女孩对自己也够狠的,并非我想的那样,如一片月光般纯粹明亮。我重新跑起来,跑得很慢。女孩也慢悠悠的,随着我滑行。
女孩说,大叔,你这手机快成古董了。
用过六年了。我说。
女孩说,我猜你是个教师,挺严肃古板的那种。
我嘿嘿笑,说,曾经是。
那现在呢?女孩问。校长,整天黑着脸,背搭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思谋怎么整人的那种类型的校长。
我看了眼女孩。她的鸭舌帽压得很低,看不清她的表情变化。我发现,她的想法总是超乎我的正常思维,稀奇古怪。
我说,我改行了,现在在文化部门编一本内刊,业余写作。
女孩啊了声。说,作家啊,你是作家,怎么拿这样的手机?土爆了,一点也不文艺。
我说,能通话就行。
那哪行?至少得与你的身份和气质匹配。女孩连连感叹。瞧瞧,在这条道上又栽了一次,我看别人挺准的。
我开玩笑说,那是因为你和别人没有撞倒在一起。一旦撞趴下,你和他們搭上话了,就知道你看过的,都不怎么搭边。
女孩嘿嘿地笑。
我见女孩开心,用手指了下她那条空荡荡的袖筒。
女孩明白我的意思,爽快地说,一次干架,被对方砍了一斧头。
啊?我的天!我几乎惊叫。
真的,当时酒劲正旺,我并没有感觉到有多疼痛,只觉得是挨了一棍子,闷闷的。后来,我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已经躺在医院里,多半截胳膊没了。女孩讲得很平静,就像是对方提着一把斧子,随手削掉了一根多余的树枝那么简单。
年轻人,你们这是拿命干架啊?我打了个激灵,后背一阵冰凉。
爱得越深,恨得就越深,伤害就越深。懂吗?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女孩又顺口补充说,说了你也不懂。
我疑惑地看了眼女孩。
女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笑着说,我们本来要开开心心吃顿散伙饭的,好合好散不是。但喝着喝着就喝二了,脑子一烧就干了起来。我掉了一只胳膊,他进去了,大半辈子得在号子里度过,扯平了。
这之间到底是一笔什么账?能让女孩说“扯平了”。我似乎不敢去多想,赶紧换了个话题,问,你热爱轮滑?
女孩说,一般吧。
那你天天踩着轮滑跑?
女孩说,这不快嘛!在这个尘世上,我想多走些路。所以只要有空,我就踩着轮滑跑。在马路上跑,在黄河两岸的风情线上跑,在大桥上跑……晚上要离家近点,我就在这条环湖跑道上一圈又一圈地跑。不是说人生是个圆嘛,从零开始,到零结束。我想努力把我的这个“0”画得更大一些,更圆一点。
什么意思呢?我疑惑地问女孩。
女孩指了下她平坦的胸脯,说,这儿,挖掉了。
挖了?我彻底坠入一团迷雾。
笨大叔,还作家呢。女孩说着,摘下白色的鸭舌帽,又扯下假发,露出一颗光丢丢的脑袋。喏,化疗的结果。
明亮的月光下,我第一次看清楚了女孩的脸。那是一张和她含露带水的声音极其匹配的脸,因为惊讶,我几乎找不准词儿去形容。总之,她的眼睛、鼻子、嘴巴组成的五官,看上去十分的甜,甜到迷人。但又十分的苍白和憔悴。
这么不幸?我心里嘎巴响了一下,像被谁生生扯了把。
当晚,我就趴在电脑上,一遍又一遍地往百度里输入关键词。诸如“男子酒醉,斧斩情侣手臂”什么的,但没有找到任何一点相关的信息。难道这只是女孩随口虚构的一个爱情故事吗?挺悲剧的……我怀疑这一切都是梦境,就像女孩说的那样,我是一团枯萎的蒿草的影子,她自己是一片白晃晃的月亮的影子。
又一个晚上,月光一如既往的明亮和清澈。
荡漾在月光中的女孩从我身边滑过,白色的身子一闪,像是月光中最最耀眼的那一片,照得我眼前一亮。那一刻,我正单腿蹬在道牙子上系鞋带。糟糕透了,这个晚上,我已经是第五次蹲下来系鞋带。我后悔出门的时候,不该换双新鞋子。新鞋子的鞋带质地太光滑,我只有一只手,总也系不紧。
正郁闷,冲出好长一段路的女孩,滑出一个优美的圆弧,轻巧地转身,迎着我滑了回来。又甩一个漂亮的小圆弧后,稳稳地停在了我旁边。
有困难了吧?
女孩说着蹲下来,伸出那只完好的左手。我用我的右手,和女孩完成了一次配合,竟然很默契。明亮而清澈的月光里,我又看见了她手腕上那多黑色的花朵。我觉得那朵用烟头烫出来的“梅花”,开在她葱白一样的皮肤上,实在是有些扎眼。
我没话找话,对女孩说,你看,今夜这月光多美。
女孩抬起头望向星空。
你知道我的手?我忐忑地问。
早知道的。女孩将目光从浩渺的星空抽回来。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这条道上,我可是老手。
我局促地笑。
女孩问,大叔,你这手是怎么弄没的。
我说,小时候帮家里干农活,被铡刀铡的。
啊呀呀!女孩像是得到了什么好消息一样,竟然有些兴奋。我挨了一斧头,你挨了一铡刀,咱俩可是同病相怜的人,对不对?
同病相怜?我心想,我是生活所迫,你是玩冲动,这能一样吗?我叹了口气。
女孩问,你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想,反正像我们这样缺了一部分的人,都过得不容易。在生存中是,在别人的眼光里也是。
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女孩说。你在这方面缺失了,肯定在另一个方面就更加的强大,这应该是生存法则。
生存法则?我陷入了短暂的沉思。“死要面子活受罪。”“独手子,总比长‘三只手’德行吧。”“你不是缺一只手,是缺脑子。”……刘欢喜怼我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我下意识向四周瞅了瞅。
还是女孩打破了稍稍有些沉重的氛围。
女孩说,大叔呀,才一个来月,你就跑出型来了。
我说,啥型?
帅哥型啊!女孩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可是标准的大爷型。
我说,你挺会忽悠人的。
女孩说,我可以忽悠别人,但不忽悠你,真的。照这样跑下去,你迟早会跑成一枚小鲜肉的。
我终于没忍住,噗地笑出声来。
女孩说,以后就叫你帅哥吧。
我说,你随意,不过一个称呼而已。
女孩说,那不一样,我叫帅哥,可是抬举你。
我说,我没那么臭美。
女孩说,看看,我知道你不会理解的。给你讲个真实的小故事:我上中学那阵子很叛逆,跟我爸闹得很僵。我同学和父母闹僵了,相互之间都死憋着气,不愿意说话。我偏不那样,为了气我爸,我一见到他就故意喊他“我的亲爸”。吵架的时候喊,瞪眼的时候喊,怄气的时候喊……有时候我爸打电话,我接通只喊一句“我的亲爸”,然后就挂了,再也不接。那几年,我爸的脸一直是黑的,被我气的。后来,我伤了胳膊,和我爸和好了。和好后,我倒是很少叫他爸爸,而是叫他帅哥。真的,我爸听我叫他帅哥,乐得屁颠屁颠的。你说说,我叫你帅哥,是不是也抬举你了?
那你是不是也叫你妈妈姐呢?我不知道怎么就答非所问地冒出来这么一句。
女孩瞟了我一眼,说,我没妈,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知道我冒失了。时间又有了那么一小会儿停顿,像是凝固了。我装着照自己的嘴巴扇两下,嗫嚅着说,对不起。
女孩打了声哈哈,说,没事的。说了也无妨,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生我的那个女人,跟一个梳大背头的男人跑了……
我忽然就悲伤起来,不是为轮滑女孩,是为我女儿,或许是为了我自己。我没想到,我女儿和轮滑女孩竟然经历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这个世界,简直太小了,太神奇了!我那个心比天高,但命却比纸薄的妻子毫无牵挂地出走后,我女儿还不到一岁。这么多年来,我是既当爸来又当妈,屎一把的尿一把拉扯女儿长大,供给她上大学。毕业那年,我希望我女儿能回到兰州,回到我身边工作。但在亲情和爱情之间,在我这个孤独的西北老宅男和南方小鲜肉之间,女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见我陷入沉默,女孩说,哎,帅哥,想啥呢?和你商量个事行吗?
和我有啥商量的?我有些疑惑。
肯定是好事呀!女孩说。你是大作家,可以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吗?说不定,会畅销的。
我再次瞅了瞅轮滑女孩。她贴在我的一侧,滑得很轻盈,像一片白色的羽毛,跟随着我飘动。我说,你有啥写的。
女孩说,天呐,我的经历谈不上惊天地,泣鬼神。但比选秀节目中那些一讲起个人经历就抽抽搭搭的人悲催多了。
我说,是吗?怎么个悲催法,我倒是可以了解下。
哇,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
我信口问,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女孩说,教钢琴。
教钢琴?
女孩说,是啊,教钢琴,在一家少儿音乐学校教孩子们弹钢琴。
我心里又“咯噔”一下,马上想起女孩白皙而又修长的手指。当时只一眼,我心里就闪念过,那是只在琴键上恣意跳跃,能敲打出狂风、骤雨和流水的手。还真是———但我没敢往下问,女孩只有一只手,一只左手。
女孩可能觉察到我分神,大声说,等哪天精神好些了,我给你讲我的故事,但你得多少准备点眼泪啊。说着,女孩猛蹬几下轮滑,窜出一大截后,回头又喊一句,说定了,不许反悔啊,帅哥。
已经立秋了,早晚的气温明显凉透。
这个晚上,我踏入公园时,所有建筑上的灯光秀次第亮起来,闪闪灼灼。周边的高楼大厦以及家家户户的窗口也都亮了起来。人们和以往一样,陆陆续续来到公园,准确有序地把自己投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我也一样,踩上青石台阶,绕过一片绿地,之后穿过花坛小径,穿过廊桥……期间和一些必须要擦肩而过的人擦肩而过,最后我准确地进入到树阴下的跑道上。
七点三十分,我从标有“0”的起跑线迈开第一步,挺有仪式感的。行进中,我似乎听见了树叶间微弱的蝉鸣,草丛里蛐蛐的歌吟,从某一扇窗口飘飞出叮叮咚咚的琴音……但似乎有没有。跑过大半圈,我总感觉眼前蒙昏昏的,心里也蒙昏昏的。一定是哪儿缺点什么。缺什么呢?我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的顾盼一番,最后仰头望了望天幕。我终于发现,月亮还没有出来。
———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我仔细想了想,从我到这个公园跑步起,月亮弯也罢,圆也罢,多数情况都会准时地挂上头顶,将银子一样的光辉洒遍人间,也洒进人们心里,无比清爽。月亮真是给力!可这个夜晚,月亮迟迟没有出来。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垂得很低,几乎要压着楼顶了,几乎要擦到树梢上了。天空一低,心里就显得窄狭,就觉得压抑。
正闷着,身后有了轮滑摩擦地面的声音,那声音哧噜哧噜地追上来。和往日一样,女孩在超越我的那一瞬间,伸出两根纤细修长的手指,打了個“耶”手势。我很意外地喊了声:加油!这是我第一次以女孩的方式,给女孩喊加油。应该有好几个晚上了,女孩没出现在这条跑道上了。我猜想她可能是身体状况不佳去住医院了,或者是带学生上外地参加比赛了……不管怎样,她应该是最需要别人为她鼓劲加油的时候。
一圈后,女孩追上来。
嗨,帅哥,我想应该到了给你讲讲我的故事的时候了。
这口气,多少有点耐人寻味。我放慢速度,扭头认真瞅了瞅轮滑女孩。她除了牛仔毛边短裤换成了牛仔长裤外,其他穿着还和原来一模一样:白色的轮滑鞋,白色的长袖运动衣,白色鸭舌帽,但看上去没有往常那么透亮。没有月亮的夜晚,一切都有些灰暗。
我说,那好啊,我洗耳恭听。
那你得绅士点是不,主动约下我嘛,作家同志。
好好好。我笑着说,明天你有空吗?小仙女同志。我并没有去考虑明天到底有没有什么安排,随口就约了她。
你终于开窍啦!哈哈哈。那就明天,在……
轮滑女孩话音还未落下,靠我们最近的湖边突然传来女人的惊叫和呼救声。紧接着是很多女人和孩子的惊叫和呼喊声,声音杂乱,人影晃动,场面乱作一团。闲适的公园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有人落水了。之前我注意过,每天晚上,都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湖边玩水。他们提着小水桶,拿着小网兜,一个个撅着屁股,在波光凌凌的湖水里打捞泥鳅、小鱼儿什么的。
我还在愣怔,轮滑女孩长腿一抬,跨上路沿,接着一闪,就顺着水泥斜坡滑向了湖边。反应倒是够灵敏的,这孩子。我想她是去看热闹了。这个年代,最不缺少的就是围观起哄看热闹者。但凡有点事,轰一下就会被围拢得水泄不通。
已经看不见轮滑女孩的影子了,湖边的人继续紧张地喝喊,湖水里有人扑通,光晕一圈一圈漾开……水有那么深吗?应该一伸手就能拉上来的。犹豫了会儿,我感觉不怎么对劲,也顺着水泥斜坡拐向湖边。
湖畔的木栈道上,水泥台阶上,草甸子上,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影。一转瞬就聚集了这么多人,从哪冒出来的?真让人费解。我看见多数人的手里,都举着一部荧光闪闪的手机,仿佛重大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我只好踮起脚尖,努力将目光插进晃动的手臂的空隙,落水的小男孩刚被从水里拉上来。有人一把抢过四肢下垂,光溜溜软沓沓的孩子,倒扛在肩膀上控水,然后放在草坡上,压胸脯……压出一串呛了水的咳嗽声。这么久,跳湖救人的人是被遗忘在水里了吧?我这样怀疑的时候,一截吸足了湖水的,湿漉漉的月光在我眼里晃动。我心里一惊,连忙揉了揉眼睛,没有月亮的夜晚,湖畔昏昏沉沉的,但我还是看清楚了:白色的轮滑鞋,发白的牛仔长裤,白色的长袖运动衣———是她,轮滑女孩。
我突然就激动起来,对着那些晃动的手臂和闪烁的手机大喊:她只有一条胳膊,只有一条胳膊,怎么能让她下去?好像是谁专门派滑轮女孩下水救人的。我一边喊一边往前挤,但腿软得像一滩水,怎么也挤不到跟前。她还有重病在身,刚刚化疗过……我的声音嘶哑、颤栗,被呼啸而来的120急救車警报声和人们的吵嚷声淹没。
很快,湖边恢复了平静,我有些回不过神来,索性一屁股瘫坐在草甸上,盯着幽深的湖面发呆。一瞬间,我眼前又忽闪一亮,看见轮滑女孩仙子般漂在湖水中央,她似乎在对我微笑,最后越漂越小……仿佛一弯从天幕上走失的清瘦的月亮。
(责任编辑:王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