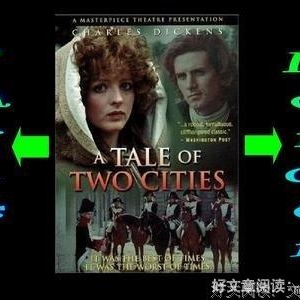《乡里的圣人》是一本由王东杰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21-9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乡里的圣人》读后感(一):颜李学派反智
《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
……因此陆、王的末流和清代的颜、李学派都把知识看作毒药。反智识主义又可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反书本知识、反理论知识,或谓其无用,或谓其造成求“道”的障碍;另一个方面则是由于轻视或敌视知识遂进而反知识分子,所谓“书生无用”“书生不晓事”等等话头即由此而起。陆象山虽有反知识的倾向,但尚不反知识分子,颜习斋则反知识而兼反知识分子。不用说,这两个方面的反智识主义都正在以崭新的现代面貌支配着知识界。
《乡里的圣人》读后感(二):澎湃书单年终策划|澎湃新闻编辑们推荐的2021年度十大好书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816782
推荐语:
盛宣怀是纵横中国近代官场与商界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对他的关注都偏重实业方面的“洋务”而忽略社会救济方面的“赈务”。朱浒教授所著《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利用规模庞大的“盛宣怀档案”,以“赈务”与“洋务”的互动为线索,探讨了如下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盛宣怀这样一个出身于普通士绅的平凡人物,居然能够成为一度掌控国家新经济命脉、尔后又在革命大潮冲击下得以全身而退的角色。”(郑诗亮)
《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王东杰/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乡里的圣人》读后感(三):读后随笔
读到作者在导言部分称自己希望引入精神分析、心理学等知识时,不免心中发怵,因为此前已经见过太多精神分析论史的糟糕案例。所幸王东杰老师的史料敏锐度和解读能力让他在应当止步的地方有所克制,即使偶有发散也不忘强调其中的猜测性质和无法避免的偶然性,几可称得上“恰到好处”。最末一章写乡里民众如何重塑“颜圣人”及其弟子李塨的部分十分精彩——怀特所谓的“历史诗学”不仅仅存在于他笔下那些有足够方法论自觉的史家笔下,也存在于以民间叙事传统理解知识精英的底层。可惜这部分所占篇幅太小,分析仅能点到即止,颜、李的传说形象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对“民间”叙事的理解事实上也依然不出“神怪”、“侠盗”的神话范畴,私以为仍是简化了。
颜元学说的特点极适合此书的研究方法,身体力行、一反理学静思态度的主张本身便足以呼应作者在此书中屡屡引用的王汎森观点,即“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于是,此著的写作形式也成为一条呼应作者理解中的习斋学术的暗线。但说到此处,又不由得回过头来想,那些与此不同,或缺乏具体事件的学者应当如何以此方法研究?以本书为例,上半部分以颜元发觉自己的真实身世为高潮,自此他冲出宋儒藩篱,由于这一事件有颜氏本人的记录,故作者能以此为核心材料步步展开分析。但至下半部分,颜元由“不合时俗”转向“乡里的圣人”这一过程则显得含糊许多。作者提出促使颜氏正视“俗”的三重原因:其一,是他儒家理想自身的价值导向;其二,是出于策略性的“避祸”;其三,是出于功利性的“传道”考虑。但是,第一点,即重视“礼”的同化力量,是许多中下层(甚至高层)儒家学者的共识,第二、三点也并不具有颜元个人的特殊性。和本书前部分相比,此处的解释力度的确显得有些疲弱。
由于此书意在从颜元的个人史出发,以此探索经历、性格和学问的关联,因此作者从几乎未将颜元放入晚明思想史的脉络,仅以寥寥数语点出其交友(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内容的最终旨归在于表现出颜氏的性格特点,而非其接受的文化资源)。然而,如此一来,颜元的许多学说和观点都可能从作者在导论中所批评的、思想史写作中常见的“生活真空”进入另一种“理论真空”,许多有所针对、在特定语境和思想对话中产生的核心观念都可能被一笔带过或扭曲原意。王东杰老师的确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也值得继续下去的研究路径,但它和过去困顿在理论、观念、学说的思想史一样,所能反映的仅仅是思想史的面向之一。
《乡里的圣人》读后感(四):如何在家乡做一个圣人?
乡里的圣人: 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
王东杰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9
老中国基本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时候,互相认识的人之间几无隐私可言,而陌生的外乡人则全为异端(参看《叫魂》)。因此,想在外埠招摇撞骗相对容易(比如清末民国的上海滩“奸僧”本照,参见《元周记》),想在乡里做个圣人,却是很难很难的。
对照《乡里的圣人》主角颜元的生平,三章分别对应“乡里做圣人”的三重难关。
一是破亲情关。颜元在家族并不讨喜,放弃科举更是为父祖所不容。上天给颜元的机遇,就是突然有人告诉他:你是收养的,你爹早就离家出走了,你姓颜,不姓朱。──在茫然惶然的同时,颜元也就释然了。没有了血亲的羁绊,母亲早已改嫁,在伦理范围内,颜元只剩了一个早已离乡不知所终的父亲,这对于颜元打破心理大关,执己成圣,可以说省去了许多的气力。
二是破身体关。颜元显然是践行圣贤礼法的实干派,不是心口不一的道学家,而正是为养祖母服丧的全过程,让颜元体现会到“礼”制下身体的不适与受摧残。当然一心成圣的颜元并未从此走上五四式的反礼教之途,而是转向对“身心”关系的思考,将身体经验纳入到礼的践行中来,从而完成了他全面反对朱子学的理念构建。简单说,就是儒者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三是破世俗关。与朝廷功名加持的儒者不同,颜元要做的是王阳明的“愚夫”式圣人,就如他倾慕的孔子“处乡党”的面目:“大圣人杂于愚人而不惊,不自贤圣,不大声色……恂恂似不能言,俨然昌平乡中一乡人耳。”但“圣人”要获得关注与认同,也不能完全没有表演性,“装腔作势,迹近优伶”正是周边人众对颜元的评价。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坚持一以贯之的颜元也赢得了不少追随者,他的后世声名,亦来自这些人的揄扬与传播,同时,很多士大夫包括康熙皇帝也会把颜元称为“疯子”——足见疯子与圣子,或许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外在环境的变化:明末以来,“圣人”这个称号也跟当今之“大师”“大咖”一样,动辄被人用来称呼一些言行异于常人又让人心生敬(敬重或敬而远之)意的奇人。中国社会最后被称为圣人的,或许是武训,也可以是陶行知——他们二位,也基本上可以被称为“乡里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