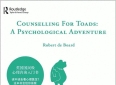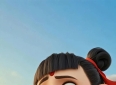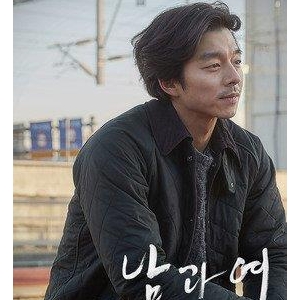作者:刘发开
《感逝集》是山东大学文学院刘晓艺教授新近付梓的一部诗词文集,汇辑了包括旧诗、词、莎翁商籁、尺牍、序跋、散文等在内的各种文体,可视为其2019年出版的旧体诗文集《昔在集》的姊妹篇。与后者相类,《感逝集》也是一部“思怀师友,感逝裁诗”的致敬时光之作。
“感逝”是中国传统诗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其背后往往隐含着古人深刻的时间观念和生命体验。古人寿时不永,短短几十年,如草木荣枯,白驹过隙,倏然而过。睿智精进如夫子,尚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喟叹;一代枭雄曹操,亦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伤婉;潇洒俊逸如王羲之,因感“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遂生“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悲怆;放荡豪逸若太白,亦有“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之悲吟;至于豁达超然如东坡,亦不免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之忧思。
这部《感逝集》中的“感逝”,正如作者所言,蕴含着感念往昔、追忆逝者以及夫子叹川、感喟逝水等多重意蕴,既有语言层面上的低徊吟咏,也有情感层面上的追念感怀,还有哲学层面上的深邃忧思,这种复义性本身即拓展了“感逝”主题的意涵内蕴与阐释空间。
在旧体诗词部分,作者继《昔在集》之后,又一次集中展示了延自章黄学派一脉的深厚诗词创作功力。章黄学派以训诂、辞章而著称于世,辞章学经黄侃先生传至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再传至作者的业师、山东大学教授鲍思陶先生等人。对章黄学派的两种绝学,鲍思陶先生已“骊珠在握”,研深覃精,可惜鲍先生蕙荃蚤摧,盛年早逝,身后只留下一部《得一斋诗抄》和经由其友人倪志云先生补缀的《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论》等为数不多的辞章理论和作品集。
在辞章一脉,刘晓艺深得鲍老真传,积淀了于山大中文系求学时获得的“骨与血”,其旧体诗文可谓“本之情性,协之声音,振之以文采,齐之以法度”。在这部分旧体诗词作品中,既有“体裁之广”,不论是四言、五古、杂言七古、五绝、七绝、七律,还是包含小令、中调、长调在内多达30多种词牌的词作,均可见一个纯熟的诗词作手诸体皆善、驾轻就熟、法度森严的技法和才情;也有“文采之丽”,这是作者的看家本领,如以“离忧莫写,欢好曷叙”写离别,以“风翦烟絮,纷糅流转”写初雪,以“行行若牵裾,总拟后期缀”写春闺,以“浮生唯恨相知晚,老去风情倾玉盏”写伤情等等,其用语之典丽古雅、绮思风韵,几可混同古人;还有“用典之切”,作者长于用典,既有明用、暗用,也有实用、虚用,还有活用、反用,不论熟典、僻典,还是事典、语典,化典入诗,如盐入水,皆能“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语意绵密,笔力遒劲;更有“注释之详”,作者寻绎古今卷帙浩繁的典籍,对每首诗词都附有自作的笺注,将句中用典、古语、掌故逐一标明出处,甚至对部分古音、平仄、韵律等也加以说明,注释总数多达1300余条,极大丰富了文本的底蕴和厚度,也增加了阅读品鉴的审美性和趣味性。
以五言古风翻译莎士比亚商籁体十四行诗,是本书的另一大特色。这一“绝活”,作者业已在《昔在集》中展露,因其文字雅郑、译语精当,已被学界同行引为以诗译诗、会诗的范例。翻译本非易事,考验的是译者对两种及以上语言和文化的熟识程度;译诗尤难,概因诗歌处于文学金字塔的顶端,文学性最强,对节奏、韵律、结构等“形式”的要求也更高,有人戏称“诗乃翻译中失去的东西”,实不为过;而以诗译诗则难上加难,考验的是译者对外语的精通,对母语的熟稔,以及以未泯诗心打通经脉、驾驭两者的深厚功力。
莎翁的商籁体,以五步抑扬格为基本韵律格式,其对格律所持“诗律伤严近寡恩”的要求,与中国旧诗有近似之处。作者以其“深文理”翻译理论为导引,以格律诗人丰富的创作经验为根基,以风格苍凉的五言古风《古诗十九首》为仿体,以归化审美为鹄的,实验性地翻译了19首莎士比亚商籁,彰显出作者打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广博学识和纵横才情,也传递出古今中外不同时空交叠下的情感共鸣与悠远回响。作者不仅以旧体诗歌的形式翻译西诗,也曾在《昔在集》中将自己的诗作不失原味地翻译成英文,可以期许,接下来作者还会如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一样,将更多的中国经典旧体诗词翻译成英文韵文,让诗词之美在中外语言和文化间生生不息地流淌。
这部集子中“文”的部分,包含祭文尺牍、序跋古文、怀人散文等。尺牍、序跋也是章黄学派的当家功夫,刘晓艺显然深得其中三昧,展示了蕴藉古朴的文体风格和从容典雅的社交言语。如在致杜泽逊先生的尺牍中,作者紧扣其先师鲍思陶先生遗稿事,既追叙“公与先师,砚共同窗,谊在第行”的旧谊,又附以“闻先师昔供坊肆,以缀辑生涯,为人嫁作,每不趁意,公恒过往,酒阑辙劝以纂修文献之功”等细节,并历数其先师生平及“朝夕兀兀,穷宵烛之末光,仰屋梁而著书”的勤奋,读之令人动容。这些尺牍,既有文体、称谓上的谨严,也有辞章、句法上的变化,为初学者示所来径。
在《<名家文献版刻书迹辑存>序》中,作者分别对所辑录的杜甫、苏轼、朱熹、王守仁四家作出评点,如谓杜甫“肠热黎元,心忧主上。文悲宋玉,枉许身以稷契;身误儒冠,犹眷怀乎终南”,称杜诗“盖诗之有杜陵,犹文之有六经也”;谓苏轼“以诗为词,别成一宗”,“辞富学厚,天才宏放,洗万古凡马气象,宜与日月争辉也”;谓朱熹“优入圣域,致广大,尽精微”,称其书“御大字如大将,写小诗则明净无滓,味自理窟流出”;谓阳明“提书生三尺之剑,任疆事,制强藩,勋业气节,见诸施行”,称“阳明之学,主致良知;直指心性,揭示本来”,皆为精当独到之见。
在为其先师鲍思陶先生《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论》所作的序中,作者追思鲍公“弱好辞章,长实吟骨;言准玉谿,赋拟相如”,并动情回顾了鲍公故交倪志云先生历时15年,为其续成此遗著之事,称该著“文气赓继,就成省旷;诗心裁采,袭作芊绵”,并引述伍子胥、鲍叔牙、嵇康、老子等先贤的掌故作比类,以彰显其续书之功绩。在序文最后,作者进一步点明序文主旨,即“赞其续志,美其执信”,称“睿音永矣,倪公之德”,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续书之事之人的赞佩。
该书最后一部分是三篇怀人散文,追念与师友们数载承教、因缘交往的点滴,文笔贞丽不艳,意浓情深,且与前面的诗文部分形成“互文”,对照品读,可以相互启发和印证。在对已故先师鲍思陶先生的追思中,作者耙梳了鲍师的家学渊源、求学历程以及章黄学派的师承关系,记叙了很多生动的生活细节。如写鲍师“平生不改誉儿僻”,其子“重铮每年生日,鲍师都会为他写诗”,进而留下了大量亲子诗,在诗人、学者之外,塑造了一个与贾政形象截然相反的当代奶爸形象。
而在对已故友人胡真的追思中,作者则在大量交往细节之外,平添了许多对生死、情缘、命运等的终极哲思。如在讲述了与故交的生死之别后,作者写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我本中拙,或正宜为其所苦。”在该文结尾处,作者进一步升华了所思所感,写道:“我仍存在,我有感知;我欲逝者知道,他的存在,不曾被世界忘记。不仅仅没有被我忘记,也没有被他的亲人、朋友、读者忘记。”并推断道:“在那些常缘之外,世上还有一个与他在师友间的人,我能肯定,他也不会忘记。”这之中,不仅有“浮生如寄,微躯易殇”的无奈怅惘,更有感旧遗情、难以忘怀的无尽追思。
合上这部厚重的书,除了对其典雅文辞中流溢的才情睿思感佩不已之外,也引发了人们对“感逝”主题更多的体味和思考……
“感逝”不仅是对时光的追忆,也能让逝者及逝去的光阴在追思中得以铭刻和定格,进而实现“不朽”。古往今来,如何突破作为“终有一死者”(特拉克尔语)的人的有限性,达到“与天地同流”“与天地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始终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不尽追索。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论,立德需治身修心、涵养品德,立功需赖时势机遇、建立事功,立言则需才情禀赋、学问辞章。司马迁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我相信,这部诗文集中所记述的逝者及生者,也称得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倜傥非常之人”,他们因作者的斐然才情和生花妙笔而见风华,而入册籍,而得永存。(刘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