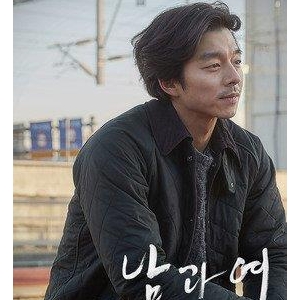一
在与以赛亚·伯林初次会面之后,埃德蒙·威尔逊曾有过这样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夫子自道:
我们整夜都在进行着精彩的谈话,时间不长,却谈了不知多少题目,但都又谈得有内行的知识,有真正的智慧,还有闪耀的机智。他走了以后,我忽然感到,由于过去几乎不认识他,这一次我是把一生里最好的故事,警句,最有刺激性的想法都一股脑儿搬了出来,放在他的头上,而且还装作临时想到的样子;很可能,他对我也是这样的。
我想说的是,读应奇教授的这本《读人话旧录》,也仿佛是在参加一场精彩的精神“夜宴”。在其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最好的故事、最摇曳人心的警句,最富有刺激性的想法,而且还能收获最内行的知识,以及那些闪耀着真正的智慧之光、英气逼人的机智。
与应奇教授此前的几本随笔集相比,《读人话旧录》还是一如既往地好看。而好看的原因之一,也依然是那些匠心独运地经纬其间、并适时地“推门而入”的各种新鲜出炉的学术八卦和解颐妙语。应奇教授自谦是由“段子手”转型而来的“文章家”。而我想强调的是,善于编织和制作各种“段子”,似乎本来就是古今中外的一些文章圣手的不二法门。据说,十八世纪的大哲、经济学“鼻祖”斯密书房里唯一供奉的一尊半身像就是伏尔泰的,而曾就“修辞和美文学”开席授课的斯密之所以对伏尔泰推崇备至、礼遇有加,也正是因为他的“段子手”身份:在斯密看来,正是如满天星斗般点缀在伏尔泰文章中的各种嬉笑怒骂的“段子”,才让当时的欧洲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引车卖浆者流都对他的文章喜闻乐见、爱不释手,并让他们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接纳了真理之光,由此,“伏尔泰对人类福祉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其著作只有少数人阅读的正襟危坐的哲学家。伏尔泰的作品是为所有人而写,也被所有人阅读” 。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在评价狄德罗的文风时,杜尔阁也曾这样写道:“艰深晦涩的学问让人厌倦,形而上学令人厌恶,一句妙语却能被人铭记于心、口口相传,并通过人们的呼吸发挥其效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才富有诗意地指出,唯有优美的警句才能躲过时间利齿的噬咬,以至于在周遭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之际,它依然能成为“不断变化之中的永不消逝之物,一道始终被人赞誉的菜肴,如同盐一样,永远不会失去意义。”
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和趣味,在这本随笔集中,我们看到:作者以“别人是什么都记不住,应奇是什么都忘不了”(童世骏教授语)的天赋异禀,化身为学术江湖的“百晓生”(也即西人所谓的inquisitive man,informative man),从而为我们奉献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段子”。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有:刘小枫教授的大弟子,海南大学的程志敏教授,在听过曾执掌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的汪丁丁先生的讲座之后,就吐槽道:“刚才,汪丁丁教授用二十分钟时间为我们解读了三十几部经典!”而与此异曲同工的则是陈嘉映先生的如下酷评:在评点韩林合教授的《〈逻辑哲学论〉研究》时,他如是说道:“这是专为一本薄薄的哲学书写的一本厚厚的研究性著作,这在汉语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中并不常见,一般都是反过来,中国人写一篇短短的文章就把西方古今全都说了一遍。” 同样辛辣过瘾的还有四川大学的熊林教授的如下精妙之词,“Chinese Social Science要发展,Chinese Social Science 就必须先停办!” 当然,其中当世无双的“段子”,当属应奇教授所引述的一位不具名的高人所发明的一副绝对:“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或许在有些人看来,文中这些信手拈来的段子无非是徒增谈资抑或笑料而已,但在我看来,正由于它对当下中国学术场域和学术生态所做出的细致入微、出神入化的观察和描摹,因而也就具有了某种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就像伍尔芙曾经说过的那样,“一切事物都只有在得到恰当的描述之后才能存在”,故而,我相信,在若干年后,当我们当代的那些所谓的“鸿篇巨制”在时间利齿的啃食下灰飞烟灭之后,《读人话旧录》中的这些学术段子或许会因为其恰当的描摹之功而永垂不朽,并在独具法眼的后世史家那里引发持久的反思和回响。
如果说,在《读人话旧录》中,各色学林掌故和段子是让人大快朵颐的正餐,那么,其中由作者阅尽千帆之后“采撷”而来的各种发人深省、读后满齿生芳的“金句”,则是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的餐后甜点。比如尼布尔的“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民主成为必要。”比如萨托利的“理想主义周游四方,经验主义足不出户,卢梭已燃起上千万人的热情,而洛克只说服一个人。”比如恩斯特·布洛赫(Ernest Bloch)的“只有一个无神论者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只有一个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无神论者。” 比如阿伦特的“真理并非思考的结果,而是一个先验条件和思考的起点;没有真理作为先验条件,任何思考都无法进行。”而在我看来其中最具点石成金、振聋发聩之效的是分析哲学大师彼得·斯特劳森在谈及每个时代的哲学和哲学家的使命时所说的如下箴言:“即使没有新的真理有待发现,至少还有许多旧的真理有待于重新发现”,“哲学的进步是辩证的,其辩证性就在于:我们希望以一些新的、改进了的形式回归到古老的洞见。”“一个哲学家除非用它那个时代的术语去重新思考其先驱者的思想,他就不能理解他的先驱者。康德、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显著特征,正在于他们比其他哲学家更多致力于这种重新思考。”
二
在《读人话旧录》的扉页上,作者还引述了以赛亚·伯林这样一段值得再三玩味的隽永之词:
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喜欢看人们的脸,甚至有时候会盯着别人的脸看,而他们并不喜欢这样。但是,我喜欢他们脑袋的形状,还有脸上的表情……在战时,有人曾问一位居住在新西兰的德国诗人:“你最喜欢的风景是什么?”他答道:“人类就是我的风景。”对我来说情况也完全如此。
精彩的“段子”和灵动的“金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编织段子和锤炼金句的那些人,因为文字固然可以永垂不朽,但惟有人才是天地万物间最瑰伟多姿、美丽动人的景致。同其“智识英雄”以赛亚·伯林一样,应奇教授身上也洋溢着一股浓烈的人文主义情怀,除了纵浪大化,嬉戏山水,对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别有怀抱,他更喜欢阅读和品评的是“人”——这是一部比“大自然”更诡谲、更复杂、更险峻,因而也更值得寻微探幽、揽胜观奇的“大书”。于是,我们看到,在这部以“读人”为主题的随笔集中,作者着墨最多、寄情最深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他最熟悉的当代中西学人:他们的生存样态,他们的言谈容止,他们的气质秉性,他们的兴寄感喟,他们的进退出处,他们的体面抑或不体面。当然,无论中西,“读人”都是一个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传统。仅就中国而言,且不说《世说新语》这种专门以“品评标榜”为己任的独特文类,即便是到了世事丕变的近代,文人间也常以月旦和臧否人物为能事:比如钱基博先生就曾分别用“妩媚”和“武谲”形容梁任公和胡适之的人格形态,而牟宗三先生也曾以阳刚、阳柔、阴刚、阴柔来区分和品藻所有的学术人格类型。而在品评徐复观时,殷海光先生也曾写出如下珠玑之言:“他凶咆起来像狮虎,驯服起来像绵羊;爱热闹起来像马戏班的主人,孤独起来像野鹤闲云;讲起理学来是个道学夫子,斗争起来是个不折不扣的步兵团长;仁慈起来像春天的风,冷酷起来像秋天的霜。……他的冲击力大极了,常常向外冲时,变成了魔王,回到书堆时,又成为圣人。”涵泳浸润于这个悠长博大的传统之中,在面对他所措意的人物时,应奇教授也展现出一种丝毫不输前人的高超的提炼和描摹能力,一种对人心和世相的冷峻清冽而又不失通达圆融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在他的笔下,不论是旧雨新知,还是未曾谋面的“神交”,往往只需寥寥数笔,各色人物便形神兼备,跃然纸上。比如,因为在辩论中得不到支持便叽叽歪歪、骂骂咧咧的著名的韦伯研究专家冯刚教授; 比如总是“预期着反应的反应”的我们著名的以机敏和辩才无碍著称的“网红”导师刘擎教授;以及直接打电话说“我在杭州的金都饭店,你来请我吃饭吧?”的“京中爷”王路;“每每不经意间‘云淡风轻’地就把咱们给领导啦”的“孙绍海”孙周兴教授,以及“你要学会写鸿篇大论,不能只有短序”的法政学家高全喜先生;以及说到紧要处,便“不自觉地严肃起来”的罗义俊先生。虽然应老师所“集萃”的这些学林人物风神各异——或傲诞,或峻急,或倜傥,或雅懿,或俊伟,或轻敏,或矜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个个面目鲜活,个个气韵生动,个个头角峥嵘。于是,在揽读之余,我们不仅对充斥着当今学界的那些大多面目混沌、品性鄙陋的学人心生厌恶之感,也由此情不自禁地对那个曾经争奇斗艳、元气淋漓的士林心生怀旧之情,或许这正是《读人话旧录》这个书名背后的“命意”之所在。
更为难得的是,在这部时有惊艳之笔、堪称学林“写真集”或“新儒林外史”的小册子中,应奇教授不仅善于描摹,而且还勇于论断。就像他在一篇堪称全书之“文眼”,也即专门用来表彰赵园女史和赵越胜先生的“读人与招魂”一文中所昭示的,他写人的最终是为了招魂,是为了提撕士林的风气,是为了接续并激活一种近乎丧失了的宝贵的民族传统,这种以一字定褒贬、用个人的史笔来书写春秋大义的传统,一如梁启超先生在表彰普鲁塔克的《英雄传》时所抉发的那样:“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以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 于是,在《读人话旧录》中,我们见证了应老师身上所表现出的一种汩汩涌动、沛然莫能驭的道德激情,一种“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锦鳞”、“虽千万人,我往矣!”的道德勇气和道德赤诚。在文中,应奇教授并不避讳以“讨人嫌”,甚至“招人恨”的方式去议论活人,去品评同侪,甚至每每以言辞“毒辣”相标榜。当然,应奇教授身上的这种“硬气的”,这种种strong and sharp的东西,并不是其来无由的,因为就像他自己所说,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凡事都要讲究“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之辩的”。但正像麦金太尔所感叹的那样,现代人已经不再把“是”与“应是”合为一体了,那些善写“甜腻”“丝滑”文字的现代学人不仅不愿做道德评鉴——虽然背后的议论和腹诽很流行,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都付之阙如,就像徐友渔先生在一篇序文中所谈到的那样:“在中国做西学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难且不说,‘易’是因为,每一行也就那么些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讲得再荒腔走板,也不至于有人当场戳穿你。” 这或许正是当今中国学术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沐猴而冠的原因。当然,勇于月旦人物或许是应奇教授身上的一种天命,因为“应奇”这个名字中不仅有好奇的“奇”,还有应然的“应”,也就是英文中代表“道德应然”的那个“ought”。所以,这本小册子总是在最为紧要处出现各种非常过瘾的道德品藻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光明俊伟”的孙月才先生,比如始终保持着“清介自守”的书生本色的索介然先生,比如“完美地结合了传统和现代,让人既亲切又敬畏的”吴以义先生,比如惜墨如金,“文字仿佛是从岩石上一个字一个字凿出来”的林毓生先生,比如具有“男子汉气概”和“古典精神”的赵鑫珊先生,比如作为“贫乏时代的思者,幽暗时代的光亮”张祥龙先生。而尤为让人感佩的是,在应奇教授的笔下,不仅有叱咤风云、声名远播的学林俊彦,也有像办公室陈主任、书友钢详、店员小蒋、讲师团的林团长这样的“无名之辈”。不仅如此,在叙述和描摹他们时,其暗藏机锋、凌厉放诞的文风似乎也突然变得温煦起来,甚至还流露出少见的“温情和敬意”,其缘由或许正像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中所指出的那样,“纪念无名之辈要比纪念名人艰难得多。但是,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对那些无名之辈的铭记”。
三
古人云:“文之为用,自喻喻人而已。” 故而,在某种意义上,《读人话旧录》不仅是为了喻人,也是为了自喻;不仅是为了阅人,也是为了观己;不仅是为了淑世,也是为了自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奇教授历年所写的这些“闲散”文字便具有了自我遣兴、自我安顿、自我澄清和自我证成的性质。就此而言,孙向晨教授序文中的如下判断确实别具只眼:应奇的文字具有自我描摹的功能,看似阅人,但最经意处写得却正是“自己”;而那些五彩缤纷、引人入胜的故事,那些错杂纷陈、鱼贯而入的人物,最终都是为了烘托“我”的出场。以此观之,应奇教授的文字颇得蒙田式“随笔”的神髓和真传。正像茨威格所说,蒙田随笔的每一篇文字似乎都是偶然的、率性而为的——要么是谈论某一本书,要么是谈论某种心情,要么是言及某件逸事,要么是忆及某次谈话,它们之间既没有时序上的联系,也缺乏逻辑上的内在关联,但真正将这些形制和主题殊异、散漫无归的文章凝结和熔铸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正是“自我”。可以说,“自我”正是蒙田文学宇宙的尽头,是其所有随笔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无论是写山川风物,还是写人情世态、嘉言懿行,蒙田最终都是为了观察自己、研究自己、培育自己和证成自己,都是为了“从对象中找到自己”(黑格尔语),都是为了书写自我的精神自传和心灵史。同样,在《读人话旧录》等多部随笔集中,在这些“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文字背后,我们最终所看到的也正是一个多面的、“丰腴”的应奇:一个时而法相庄严、金刚怒目的应奇,一个时而摇曳多姿、顾盼自雄的应奇,一个时而身段妖娆、杨柳摆风的应奇,一个颇具行动力且不乏“政治”潜质的“狡黠”的应奇。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面向的背后,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深藏不露”应奇,一个“忧心不遂,斯言谁告”的应奇,一个“道思作颂,聊以自救”的应奇,一个满怀内在紧张和郁勃之气的应奇,一个亟需实现自我和解和重建自我认同的应奇。而其历年间随笔“篇目”文字的取舍,似乎也透露了其心境的变化和某种精神困顿的症候:如果说其2014年的随笔集《生活并不在别处》,满篇都是“美”“大”“颂”,“真生命”,“主人翁”,“再出发”以及“一阳复来”这些慷慨激昂的文字,如果说2017年的随笔集《理智并非干燥的光》延续了这种积极进取的格调,那么,到了2020年的随笔集《听歌放酒狂》中,其文风就陡然为之一变,题目遂转变为“春如梦”“雨如烟”和“总断肠”,而到了2023年的《读人话旧录》,其篇目就更是演变为满眼皆是“冷”“暮”“清”“穷”“寂”“独”“断”“萧”“哀”“孤”。那么,这种心境的变化和精神困顿到底该如何解释呢?我想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或许源自其作为职业哲学家的认同危机,也即到底该如何安顿和定位这些随笔的性质?也就是说,在其他人都在学术疆场上攻城略地,争发各种顶刊文章,争戴各种江河湖海“帽子”的时候,应奇教授虽然以五卷“知人论世”的应式随笔“昂立哲坛”,但也招致了很多人的叹惋和质疑:诸如钱永祥先生就曾质疑,“你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而孙向晨老师也曾直言,以应奇的这般才情和阅人的历练,最终没有落实在大文章上,殊为可惜!即便李景林先生的夸赞之语——“你是做哲学的人中散文写得最好的,也是写散文的人当中哲学做得最好的”,也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了“哲学”和“随笔”之间的某种乖离。
于是,面对这些叹惋和质疑,应奇教授不得不郑重地审视自己的文体实验,并开始思考如何在哲学的框架下安顿和定位其随笔写作的性质。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应奇教授的许多文字所具有的那种自辩和自证的性质:他仿佛是在说,恰似以赛亚·伯林之转向观念史研究,他之转向随笔写作,并不是哲学事业的终结,更不是哲学事业的失败,而只是以别样手段在继续从事哲学事业。于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他在《理智并非干燥的光》的“自序”中所引证的阿伦特论本雅明文字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指出,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所从事的体系化的哲学建构不同,本雅明所从事的是一种“潜水采珠员”工作,一种深入海底采撷和打捞“思想碎片”的工作:
他不是去开掘海底,把它带进光明,而是尽力摘取奇珍异宝,尽力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然后把它们带到水面之上……带到富有生气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它们将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些富丽而奇异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型现象而存在。
故而,借助于阿伦特的区分,应奇教授似乎可以说,他的随笔写作,也是一种哲学化的工作,只是这种哲学化工作所采用的进路不同:不是那种竭泽而渔、沿波讨源的分析式的、体系化的进路,而是一种寻章择句、兴会式的,因而也更加“随笔化”的进路。在这个意义上,与体系化、逻辑化的“大部头”著作相比,“小品文”或“随笔”即便不是更好,也至少是同样好的从事和推进哲学化工作的有效载体和工具。
对于应奇教授的这种辩护,我不能不怀有深切的同情。如果说,就其本质而言,哲学只不过是人们感知、理解和改造世界的工具,那么,随着哲学术语越来越专业化,随着哲学的论证技术越来越繁复精密,各种“哲学建筑术”抑或理论,不仅越来越远离真实的人类生活,甚至反而成为窒息人类感知、扭曲人类理解,阻碍人类实践的最大障碍。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褪去了理论“紧身衣”的束缚,那种非体系化、非逻辑化的随笔写作反而凸显了一种真正的哲学的精神,体现了一种值得称赞的面向真实生活、面向现象本身的一种问学态度。因为恰如应奇教授所频频征引的歌德所说的那样,“人们总是谈论研究古人;但这实际上只是在说:将你的目光转向真实世界,并试着表达这个世界——因为古人正是这样做的。”“过久地停留在抽象事情上头是不好的……生活最好是通过活生生的东西来启发。” 诚如应奇教授所强调的那样,一种健全的哲学观的一个不可或缺,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一个维度,就是它与日常生活和普通读者的关系,因为说到底,哲学最终还是要通过对普通读者的影响而影响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奇教授看到了随笔写作所蕴藏着的巨大的哲学潜力,因为“未加规整的印象自有其价值,通向人生真谛之路似乎在于谦恭地记录下由际遇和嬗变强加于我们的对于生活现象的各种解释。”
应奇教授对于随笔写作所作的另一个辩护,似乎与情感有关。在《读人话旧录》中,应奇教授一再申说人类不仅有“事功的历史”,而且还有“有情的历史”,“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并在一篇纪念叶秀山先生的文章中特意指出,叶先生虽然重视他的论文,但更喜欢他的学术小品。因为正是后者凸显了作者的“性情”,故而更加具有个别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又言及贺麟先生在晚年坐在轮椅上巡视其书房时,“威严得像个将军,深情得又像个恋人”。 如果说,正如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所区分的那样,理性有“理性”(Reason)和“理智”(reason)之分——后者是一种冷的理智,干燥的理智,一种在纯粹的程序性论证中所运用的那种理智,而前者就是在与别人谈话和交往中所运用的那种理智,这是一种爱的理智,暖的理智,有情的理智,那么,显而易见,应奇教授所推崇的正是这种有情的理智、暖的理智、谈话的理智,而随笔正是这种理智的有效载体。因为在这个以科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相标榜的时代,情感似乎正在被放逐出“哲学王国”的领地,而理智也正日渐成为“一束干燥的光”,甚至成为“一束寒冷的北极光”,于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随笔写作反而成为“情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和庇佑之地,并为那些在量化指标的催逼之下心灵日渐干涸和枯寂的学者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情感滋养和慰藉,因为正像应奇教授所说,“作为竞技‘生产力’几近‘枯寂’的学者,或许正是承所谓‘抒情传统’之余绪,在改变世界和解释世界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寄情’于从其功能而言既非改变世界亦非解释世界的随笔类文字。”确实,正像休谟在《人性论》第一卷“论知性”的结尾和约翰·密尔的《自传》所揭示的那样,一颗失去了情感驱动和情感温暖的“分析的心灵”或“机械的心灵”,必将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搁浅, 甚至沉没,而一切人类最伟大的作品,永远都是最辽远的情操的表现,因为恰如狄德罗所言,“唯有感情,唯有伟大的感情,才能提升心灵,完成伟业……没有感情,便没有崇高。没有感情,艺术就回到孩提时代,道德就变得小气”。
殷海光先生曾经指出,一切伟大的人物,都只有一个主词,那就是如何重建自己。而哲学著述——无论其形制和样态如何,也都只不过是重建自我的不同手段而已,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哲人最终的工作不在于制作书籍,而在于制作人格,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种合宜的生活方式。故而,在文章的结尾,我想转引应奇教授曾一再征引的《摩诃婆罗多》中克里希纳德的一句话,并转赠给他:“不是道别,而是前进,航海的人们!”